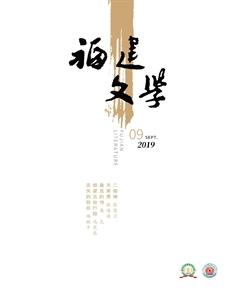人心的一点灵明
许陈颖
散文易写难工。余光中说:“在一切文体中,散文是最亲切、最平实、最透明的言谈,不像诗可以破空而来,不像小说可以戴上人物的假面具,事件的隐身衣。”这意味着散文创作入门的门槛并不高。但是,如何在那些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中写出独特的美感与感受,这对散文作者的文学修养及心灵趣味却是一种考验。王阳明说:“盖天地万物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微处,是人心的一点灵明。”正因为人心的一点灵明,人与天地万物之间才能建立起互相的感应关系,个体生命才能循着心灵的出口,到达别具一格的艺术世界。在福建的当代散文写作中,刘翠婵的乡土散文虽然数量不多,但她真诚地感受着土地上的众生相,在克制的书写中摆脱了一己悲欢的小情绪,看到时代变迁背后那个更为广大的艺术世界,从而打通了“小我”经验与“广大”经验之间的精神通道,成为众多读者的阅读期待。
一
真诚,是个体与自然万物建立感知对应的心灵起点,也是所有艺术创新的前提条件。没有了一颗真诚的心灵,身体的细微感受就无法被真实传达,更不可能有新鲜的发现。虽然社会公共文化给作家的成长提供了必要的训练和基础,但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把文化中的陈规强加给作家,常常使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因为无法突破固有的文化想象而忽略心灵的真实感受,渐渐失去柯罗所说的“不带偏见地去观察自然”的心灵审美感知力。
乡村是刘翠婵的心灵来处,也是她的心灵归途。当她以最原始的眼光与自然万物真诚交流时,故乡所回馈的独特的乡土经验使她从人们所熟悉的日常经验中解放出来,使公共文化所遮蔽的自然万物还原到最本真的状态。这些记忆储备给予刘翠婵的散文写作以巨大的文学滋养,在主体浓烈的情绪与沉默的世界万物之间,她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文学表达通道。
《庄稼开花》描写各式各样的庄稼花。它们或繁盛或衰落,接通的却是庄稼人生生不息的日常生活。稻花是庄稼人一辈子的追逐,它在庄稼人心中的分量最重,是“最贵重最沉静的花朵”;豆花的地位次之,则被庄稼人放置到“犄角旮旯”;菜籽油是陪嫁之物,谁家姑娘出嫁,“谁家地里就长出油菜花”;向日葵则是非必需品,“在土地上孤单而倔强”。丰饶的土地长出了庄稼人生活的期待与向往,并用最朴素的生命姿态告诉他们,人可以幸福、简单地栖居在这片土地上。刘翠婵越是贴近大地,越能守住内心的那份平静,也就越能傾听到土地的声音。在她笔下,庄稼地里的每一种花开,都自带着生命精神与生活的趣味。“耳豆花”的两个花瓣像“两只虚掩着的耳朵”,倾听着大地上生长的信息。到时候了——“豆秧爬得比谁都快,豆花噼里啪啦炸开,一串串挂满秧藤”。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系统在与自然外物相感知的过程中彼此关联、彼此呼应,刘翠婵以别具一格的想象打通了各个感官之间的界限,最终汇入心灵形成作家新鲜活泼的感受,刷新了读者的阅读感受。
以真诚之心反观自我,对自己的起心动念才能有精微而独到的把握,对细节的描摹才能真正接通了自我感官的血脉,使知觉的触角更加精细、独到。“看到嵛山岛天湖和草场的刹那,我想到了一个词:羽化成仙。所有的草都是羽毛,成千上万的绿色羽毛,在风中舞动,辽阔地绵展到远方。”这些奇警的比喻、曼妙的通感、生动的拟人在刘翠婵的作品中比比皆是,她把文字引到诗意、梦想、远方等事物的身旁。于是,“美好的时光”宛如“瓷器”一般莹洁,“翠郊的古民居”化身为“茶株上最金贵的嫩芽”,初春变成了“凉薄之人”。即使只是一叶枫、一片草地、一段时光等这些掩埋在日常中习见的事物,作者也能贴着心灵体验,不浮夸,不做作,让语言到达事物的同时又能摇曳着作家主体的情感力量,从而使笔下的乡土世界焕发出盎然的生机。
二
“过度抒情,不知节制,容易流于伤感主义。我觉得感伤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小姑娘的话,何必呢。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克制的讲述方式会掩饰情感的锋芒,但凸显出来的场景与细节反而构筑了作品内容的坚实,撑起内在的情感张力。刘翠婵的散文极少在情感层面做过度的渲染,她往往借用事实和经验的细节化处理,消解了传统抒情的滥觞。
在《我哥刘伟雄》里,兄妹们作为“黑五类”的孩子,背井离乡无人靠近,贫穷困苦以及被驱逐的阴影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他们的少年时光。没有尊严的生活铸就了他们生命里难以愈合的伤痛,这些悲怆与孤独的情感,作者并不是靠强烈的情感字眼进行宣泄,而是在平静和舒缓的语气中通过细节的呈现流淌出来的。“我们流落乡间,我们需要亲人。小人书,成了这个时节最温柔的手,就着村庄豆大的灯光,不停地抚摩着我们受伤的额头,和流泪的眼睛。”她写哥哥,但同时也在感怀少年岁月中无尽的悲伤,那些痛楚的情绪在隐忍的文字下涌动,诗人哥哥生命中的孤独有了清晰的方向和来由,忧伤而动人,但在更深层次上交织着的,是兄妹之间心息相通的深情厚谊。
《木菊》写祖母。“木菊又名木槿,是野生植物,亦可家养。它的花香有奇效,强烈的催眠作用会使人瞬间晕倒,有的甚至会连睡好几天,然后自然醒来,所以又有‘醉花之称。”木菊是一种野生植物,但“陈木菊”却是刘翠婵笔下的祖母:祖母以年迈之躯被遣离乡,领着全家七口在牛圈里度过春节;祖母声嘶力竭地,以“骂”驱走偷竹人;祖母听说女儿病逝“无动于衷”,闲时却喃喃自语……作者并没有声嘶力竭地呐喊,也没有故意把场面写得惊心动魄,相反,她只是个冷静、客观的记叙者。在一次又一次与艰难世事的对抗中,“硬气”成为祖母对抗生活苦难唯一的武器。“从没把她与花联系起来,故去十多年后,想起天上的祖母,始知木菊就是花,虽寻常,却有异质,如她风雨一生。”作者以花喻人,从个人回忆的角度来叙述曾经荒唐的岁月,并通过小人物命运在历史洪流中的跌宕来呈现大历史的沉重背影,无数个“木菊”纷纷从祖母身后的时代中走出。这种对于特殊年代里人们生存状态的解读,使刘翠婵的写作从私人的狭小视野中走出,呈现出宽阔的精神视界。
三
刘翠婵在乡间长大,她的眼光抚过乡间草木砖瓦、牛羊猪狗、人事沉浮,它们都是写作所依凭的材料和精神载体。在《故乡草》中,这些渺小又熟见的生命,不仅是物质的,同时也是精神的,它们经由心灵的转化聚焦到作者的笔下。作品表面上写的是草木,但指向的却是时代大变迁之后所面临的共同社会问题。
她从“草”的生死,写到村庄的兴衰,再写到生命的轮回,最后再回到草,天地万物被连接到“生死循环”这个永恒母题上,同时又向多维度撑开。包括对社会现象的思考、与大自然生命的对话、对死亡的叹问等,精妙的构思潜藏着作者对时代的反思与追问,打开了文章的内部空间,为曾经繁荣生息的乡村献上了一曲挽歌。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空心化是城镇化进程中所衍生的一种社会现象。村庄建筑由此衰败,曾经的乡村伦理,无以赋形,走向消亡。对于离乡的游子而言,“村庄与他们除了一息尚存的老爹娘外,已没有任何瓜葛。有一天,当爹娘死去,成了坟头上的草时,他们才会回来,然后,更彻底地离开。”那么,他们曾有的精神记忆将如何安放?他们身后是否还有真正的故乡?“草是有来生的,无论死得多么难看,春风一点染,它就又是芳草了。村庄和村庄上的人们没有来生,一旦离去,永不回头。”作为乡村之子,她的追问建立在对乡土、人生的透通观察之上,她的悲伤来自对生命的深切关怀,并通过乡村熟见的事物——“草”写出了时代精神气息的流转,并以文字的轻盈抵达了主题的深邃。中国散文协会副会长红孩老师说:“写草的散文很多,能从以往的关于草的文字中,写出自己笔下的草,本文具有标杆的作用。”
四
对于离乡的游子而言,乡村的存在,是曾经的悲伤也是未来的希望。在风中摆摊的孤苦阿婆、背着一只鲳鱼去台湾探亲的妈妈、因为丢羊而偷哭的老实表舅、摔一跤再也无法爬起的太婆等,娓娓道来的平常人生里不仅有悲伤,还有无奈与坚忍,它们都不是生活以外的事,它们就是乡土生活本身,构成了触手可及的真实人生。但是,“只要还有庄稼在开花,日渐苍凉的土地就还会有欢乐,日渐落寞的村庄就不会太贫瘠。只要还有庄稼在开花,庄稼人的手再粗糙,也还是拈香的手,他们粗糙而贴心地抚摩过后,很多庄稼开始盛开和茁壮。”(《庄稼开花》)不管经历过多少苦难,故乡的村庄都是刘翠婵的精神基座,是她内心“那一点灵明”的源头。她用真实的“小”去探寻人生的“大”,并在精神的挣扎中实现自我的超越,使她的乡土散文在独特个人经验的讲述上达到一定的深度,呈现出诗意的澄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