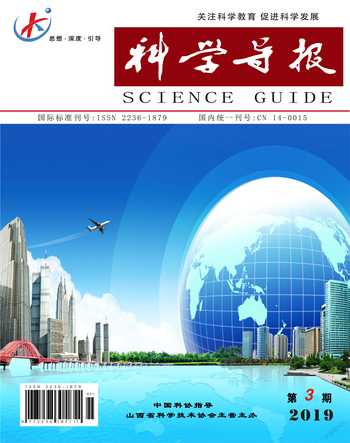浅析《小鲍庄》的“寻根”艺术
摘 要:王安忆的《小鲍庄》是寻根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她用一种神话色彩奠基了小说奇特的风格和笔调。尽管寻根文学之热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作者通过《小鲍庄》所传达出来的对仁义的思考与批判不仅不过时,反而熠熠生辉。本文将通过《小鲍庄》中的神话起源进一步窥探民族文化之“根”。
关键词:《小鲍庄》;神话;寻根;仁义
王安忆的《小鲍庄》自问世以来就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作为流淌在寻根大河中的分支,它承载了时代的愿景。在小说中,作者从神话式宏伟叙事中构筑民族文化之根;从浩荡历史车轮中追寻仁义的脚印;从时间的交错中洞悉发展中的小鲍庄。一幅幅乡村的图景缓缓展开,一张张仁义的面具渐被撕开,隐藏在小鲍庄中的,到底是怎样的寻“根”艺术?正如陈思和所说,在王安忆的作品中多以细腻感情叙事为主,《小鲍庄》则实在“土气十足”。这股土气写出了人间非凡的烟火气,这种土气正是当下的中国所逐渐丧失的。
一、传奇性
“七天七夜的雨,天都下黑了。洪水從鲍山顶上轰轰然地直泻下来,孩子不哭了,娘们儿不叫了。鸡不飞,狗不跳,天不黑,地不白。”这些描述让人想到盘古开天辟地、人类刚刚诞生的场景,上古神话中也有对洪水大爆发的描写,像沧海桑田等。这种宏大的开篇暗示了即将出场的小鲍庄的不凡。
小鲍庄所处的位置是鲍家坝下最洼的地点,这是由于小鲍庄治水的先人不得大禹的精神,在筑坝的同时生了三子一女,而大禹却在娶妻三天便出门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先人未能治水成功,致使鲍家坝里的水形成一个大湖,三年才干,先人觉得对不住百姓,带着妻儿住在此地,并由此繁衍开来,形成了一个十几口子的小鲍庄。鲧自古就是仁义和善良的象征,王安忆以鲧禹治水的故事给小鲍庄安排了一个极具神话色彩的起源,同时也将仁义之根置于小鲍庄中。如果说小鲍庄是微缩的华夏文明的话,那么这仁义就是中华传统文明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儒家文化的思想内核。王安忆恰好为她的文化寻根之旅安上了一个合理的精神内涵。
这场大雨给小鲍庄埋下了仁义的种子,但同时也将原罪说推上了舞台。由于先人有罪,所以小鲍庄的人们在出生的那一刹那起,一生都在赎罪。充满仁义感的捞渣在一次洪水中死去;小翠从小被收养当童养妻,与文化子想爱却不敢爱等等。王安忆将宗教的原罪说纳入小说创作,不仅是对故步自封的传统仁义观的讽刺,更是对人类自身行为的反省。
二、人物的象征意义
王安忆将捞渣的出生安排在第一节中,是具有深层含义的。他就像拯救苍生的英雄,和洪水同时诞生,是集结着仁义礼智信的综合体,但这位英雄却不受父母重视,甚至被生下也是个意外。村民们都说捞渣笑起来的模样好,眼睛弯弯的,小嘴弯弯的,亲热人,恬静人,看起来“仁义”。捞渣是德智体美劳全发展的好孩子,是小鲍庄里核心价值观的象征。捞渣为救鲍五爷而死,省报和县里的记者们蜂拥而至,给捞渣写了一篇又一篇报道,将其称为英雄式人物,他的死把这个平静的村庄推向了风口浪尖处,各地的学生纷纷来小鲍庄悼念他,甚至还有领导提出应该学习捞渣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精神。事实上,捞渣的死预示着小鲍庄与仁义精神的远离。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以仁义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渐行渐远,这里渗透着王安忆对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消逝的隐隐担忧。
捞渣的死带走了传统文化中的仁义,开启了现代化的大门,而文疯子的存在则是带领着村庄走向了现代化,捞渣的事迹开始只是在几个村子之间相互传颂,后来由于文疯子的一篇报告文学,事迹开始在县里、省里传播,最终被评为小英雄。如果没有文疯子,或许小鲍庄只是死去了一个人两个人而已,并不会引起什么轰动。
作者把传播和弘扬传统文化的重任交于文疯子手中,希望他带领村民重塑民族之根。在捞渣的墓前,总会有新人来祭奠,但也总有旧人去清扫痕迹,捞渣的母亲、拾来、鲍彦山等人用扫帚清去一天的烟尘,扫去的不仅是尘埃,还有现代文化的侵袭,他们也是传统文化优秀因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反讽与反思技巧的运用
王安忆称,“《小鲍庄》恰恰是写了最后一个仁义之子的死,我的基调是反讽的,这小孩的死,真实宣告了仁义的死亡!”捞渣死后,被省团委评为英雄小少年,一年后还被迁坟,作者所反讽的,并不是像捞渣这样集结着民族全部美德的真仁义,而是打着仁义牌去毁灭美德的人。大姑收养拾来是一种“仁义”,然而文中则多次暗示拾来为大姑的私生子,拾来对大姑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鲍彦山养着小翠是一种“仁义”,但他是为了大儿子建设子而将小翠当作童养媳;鲍秉德不和疯媳妇离婚是一种“仁义”,但实际上,他不敢突破自己所打造的舆论压力,十分关注世人的眼光。这些看似是仁义的行为实则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和利益,总是有太多人打着光明的理由去做黑暗的事情。
王安忆将表层的仁义与深层的欲望碰撞成一种悖论,进而形成对假仁假义的讽刺。鲍秉德、拾来,鲍二婶、鲍彦山等这些人不能说是不仁不义,只能用假仁假义形容,他们的仁义与捞渣的仁义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小鲍庄》具有超越空间和时间的双重内涵,表现了“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的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王安忆的寻根笔触并未伸向不规范,而是寻找到具有神秘色彩的神话用来表现传统文化中的仁义因子。寻根文学寻的便是民族文化之根,在追寻的过程中,作者发现了千疮百孔的“根”,由此透露出的精神危机和文化焦虑值得每一个人思考。
参考文献
[1] 王安忆:小鲍庄[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2] 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 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4] 洪子诚:当代文学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注释:
①陈思和:双重迭影,深层象征——从《小鲍庄》谈王安忆小说的一种叙事技巧[J]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1月
②王安忆:小鲍庄[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84页
③王安忆:小鲍庄[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97页
④王安忆:我写小鲍庄[J]光明日报1985年8月15日
⑤韩少功:进步的回退[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页
作者简介:董若楠,1995.3,女,汉族,河南永城人,黑龙江大学,研究生院 2018级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