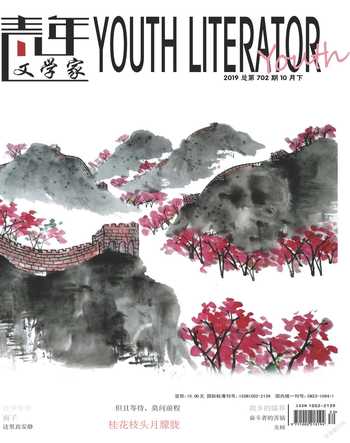“好色”的遥响
摘 要:《金瓶梅》是我国小说史上一部出格的奇葩,它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后世小说的发展。而在一条狭长海峡相隔的日本,数十年后的江户时代,出现了同样以生活情色为主题的伟大小说家。两个民族性格都较为内敛的国家在彼此几近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创作出了类似的“好色”作品,甚至有了世之介、西门庆这样外在类似的形象。兰陵笑笑生与井原西鹤的“好色”之观,似乎正彼此呼应。
关键词:井原西鹤;好色一代男;“好色”;金瓶梅;西门庆;世之介;兰陵笑笑生
作者简介:丁洁,女,出生于1998年2月,汉族,新疆伊犁人,扬州大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30-0-03
在隆庆至万历朝之间,中国的土地上诞生了许多出格之作。明朝中期出现的这些作家,在严厉的文字狱搜查下已没了署名的自信和余裕,却在书本中放荡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一边,华阳洞天主人的《西游记》正动摇着上层统治者的耐心;而另一边,在民间,一本惊世骇俗、也是中国头一本家庭市井题材的长篇小说《金瓶梅词话》也摇曳着文人的神思,其作者兰陵笑笑生神龙见首不见尾。不同于“四大奇书”其他三本,《金瓶梅词话》所选的时代、所选的人物、所选的题材都极为怪异,这也为后世道统家们不齿,它的文学性和地位也常常受到质疑。在中国,奇书《金瓶梅》是孤独的。而在稍后的时代,稍远的地方,江户时代的日本也出现了一批以世情、情色为主题的小说作品。其中以江户文学小说大家井原西鹤的作品最有特色,他创作了一系列以“好色”为名的情恋小说:《好色一代男》、《好色一代女》、《好色五人女》流传于世。《金瓶梅词话》与西鹤“好色”之作,时间上十分接近的时代之中,竖长海峡隔着的两岸之间,诞生了它们这样写作方向相似,观念也十分相似的文学作品,却鲜少见到有相关研究。《金瓶梅》若生在江户时代,定是“好色”之中的一字辈,而《好色一代男》若在明朝诞生,也一定不同于普通的情色小说。“情色”太贬,应将它们一齐归入这“好色”文学之中。
“好色”一词,在中文与日语中同文而并非完全同义。在中文语境中多有贬义的“好色”,是形容男女因对方的姿色而动心,进而产生追求行为。在儒家的文化氛围熏陶下,“好色”常常被认知为一种属于男性的缺陷品质。这或许与传统观念中的“凤求凰”——即男性追求女性相关,相对而言女性是甚少追求男性的。故而我们在《诗经》之后的中国古典文学乃至现代语境之中都甚少见到女子“好色”。若是追求了,则必定是个“淫妇”,连“好色”的评价也难得到。而另一面,“好色”的男性也几乎从未得到正面的审视,耽溺于情色之事的男性无法成就儒家赋予的功业大事,史家所写伟大人物往往都是去性化的,家国为大,儿女情长为小,微不足道。可以说,不论男女,“好色”与“淫”在中文集体无意识的大环境中已潜在地画上了颇富贬义的等号。
在日本小说翻译为中文时,原本为汉字的篇名往往得到了保留:这便出现了一定的歧义。井原西鹤所作的《好色一代男》、《好色一代女》、《好色五人女》等作品在译介为中文时都保留了原本的作品名,在中文读者看来,不免有一种贬义色彩。但在日文的语境中,“好色”这两个汉字之意义与同写法的汉语有着一定偏差,虽然也解释为“異性に対してともすればみだらな気持ちを抱くこと”(对异性抱有淫色的想法),在情感上却更接近“风雅”、“风流”这一类中性的意义。且在江户时代,“好色”一词还有“美しい容色。また、美女。「女御·更衣、又は遊女·-·美男/風姿花伝」”,即是“美丽的男女”的意思。不少日本研究者认为井原西鹤在命名《好色一代男》、《好色一代女》、《好色五人女》等“好色”之作时运用了这个双关的意义。可以说西鹤对于笔下“好色”的人物本身是毫无贬损之意的,反是带有一丝宠溺的调侃味道。因此与一些学者不同,私以为本就不能以贬损的目光,去看待“好色”的世之介等人物,这是典型的不同文化语境下简化翻译造成的误读。西鹤的“好色”,是写男女之間理应有的爱意,并将其淋漓尽致地表达。
在不同的文化语境和社会环境下,井原西鹤与兰陵笑笑生却一同靠近了“好色”。《金瓶梅词话》的好色是公认的,不光是西门庆好色,也不光是潘金莲好色,连他那些娶进来的女眷人等,也疯了似的好色,为西门大官人而倾倒;西鹤之“好色”则直白地写在标题里,《好色一代男》与《好色一代女》之主人公,都自称与数千人发生了性关系,《好色五人女》之中的男男女女,也似为一个色字而疯狂。创作在前亦生于前的兰陵笑笑生自然不知晓遥远的日本将要有一位伟大的江户大文学家诞生,而井原西鹤也未听过彼时虽已对外传播至日本,却因“淫秽”被束之高阁的《金瓶梅词话》。两位作家在对各自封闭了的创作环境下,选择了类似的创作题材,并最终产生了外在存在相似,内核却有深浅差别的文学作品,缘何如此,无疑是值得考察的。
追查一部文学作品的渊源,往往要根植在作者的时代之中去思考。西鹤所生活的江户时代,随着简单资本阶级的兴盛和日本本国传统,对“好色”其实具有相当宽容的态度。王向远先生在《浮世之草,好色有道》一文中罗列了一些观点及例子证明这点:
据中村光夫在《“好色”的构造》一书的看法,在平安王朝时代初期,由空海大师从中国传到日本的佛教 真言密宗及其经典《理趣经》,将男女交合视为神圣之事,带有印度思想的强烈印记。当时的宫廷贵族受真言密宗的很大影响,“按当时的真言密宗及其经典《理趣经》的看法,男女性欲本来是‘清净’的东西,男女交媾时进入恍惚之境,使人获得了在人世中的最高的自由,达到了菩萨的境地,在性欲高潮的瞬间,便进入了控制这个世界的超越的心理状态,也就是达到了解脱的境地。”(中村光夫,1985:108—109)同时,根据从中国传人的汉译学而汇集编纂的《医心方》等性学书,在王朝贵族中也流传甚广,使得当时的 日本人更多地从自然与养生 的角度看待男女与好色问题。例如紫式部在《源氏物语》的《夕雾》卷中,借源氏的口议论说:“多么大好的年华啊!真是人生中最光辉的时候,干出那种风流好色之事,别人也不该说什么,鬼神也会原谅他。”(本居宣长,2010:81)中世纪僧侣作家吉 田兼好在《徒然草》中认为,不好色的男人,就像一个没有底的玉杯子,是好看而又不中用的东西。一些本来是禁欲修行的和尚,也以“好色”为荣,花和尚的风流破戒,成为日本文学作品津津乐道的话题。……到了江户时代,在町人享乐风气的带动下,人们对于“好色”持更为宽容开放的态度。
西鹤在是一位情恋小说大家的同时,其更有标志性的身份是:他也是一个町人。在创作了许多“好色物”的同时,他也创作了如《日本永代藏》这样的町人经济小说。在江户时代兴盛的町人阶级主导和把握着江户日本的发展,和风气的变化。在这样相对宽松的社会风气下,他的“好色物”创作不但不受到拘束,反而获得了张扬,甚至有着大量可接触、了解的现实素材。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西鹤以其毒辣的观察之眼进行着“好色物”的创作。因着这份独到的毒辣,使得西鹤的“好色”创作又不同于一般的情色小说。不论身份高贵与否,“好色”的男女们的确抱有对彼此的真情,但他们最终或多或少地都被金钱社会或道德社会而抹杀,贬损。从这里可以依稀窥见西鹤对着自己所处的时代社会也含蓄地夹杂着否定之意。
而地理上远在中国,时间上远在百年之前的兰陵笑笑生则与西鹤面对着不同的状况。兰陵笑笑生其人身份依旧不明了,但哪怕在这里不过多赋予他任何一种存在的推测身份,他所面对的明中叶的社会环境依旧不容被过于乐观地被估计。明中叶的商贸经济活动同样兴旺,同样有着“好色”“好货”之社会心理,艳情小说的创作不在少数。如此富饶丰富的社会也成为了《金瓶梅词话》所描写的一个侧重点。但与江户时期日本显然不同的社会结构和传统思维并没能使纯粹的“好色”之情完全成为《金瓶梅词话》的创作中心和实际内核,以西门庆为中心的脱俗男女真情是《金瓶梅词话》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和西鹤所处的江户日本不同,仅是这部分就已极大地践踏了当时社会较为公认的道德与秩序,及对正邪的判断。这无关乎兰陵笑笑生具体是谁,而与作为文人的他有关。作为一个文人的兰陵笑笑生一方面和世俗社会相连,一方面熟知社会上层的构造,亦清楚上下之间的勾结,这种处于夹缝之间的位置使得他所写的“好色”之中掺杂了大量含蓄而激烈的讽刺,掺杂了强烈于西鹤的对社会公共道德的反抗和大声驳辩。
西鹤与兰陵笑笑生二人所创作出的“好色”,即便因着时代和文化因素而在观念上有一定深浅的差异,但在对“好色”真情的推崇上却趋于一致。西门庆与世之介此前也被人浅显地比较论说一二,但显然仍不足够。西门庆作为原出自《水浒传》的邪恶形象,被选取为《金瓶梅词话》之主角,一方面是基于《金瓶梅词话》的讽刺效果需求——兰陵笑笑生并不是要讽刺作为恶人的西门庆,而是要借用因《水浒传》基础而在世人眼中足够丑和恶的西门庆形象去讽刺西门庆广博人脉所涉及到的万千事象,西门庆的恶与之相对显得渺小而纯真。我们必须要理解,兰陵笑笑生是相对正面、并带着怜爱之情看待西门庆的。正如张竹坡所言:“为月忧云,为书忧蠹,为才子佳人忧命薄,真是菩萨心肠”,这评价给兰陵笑笑生是恰当的。另一方面,便是着眼于《水浒传》西门庆之多情温柔。一百回《水浒传》里,他是头个对被大户挤兑而被惩罚性倒赔嫁给武大郎的潘金莲感到实在同情的人物,而先前被金莲迷恋的武松实际是缺乏对她境遇的同情的,一语点破金莲境遇的西门庆由此拥有了被她爱上的资本,也有了被兰陵笑笑生选择的资本。那么经过改编的、兰陵笑笑生笔下的西门庆如何?可以看到他确乎如水浒中那般好财好色,欲求无尽,无赖混账,黑白通吃。但多了更多描写的他又纯真得可爱,好兄弟应伯爵借他大笔钱财,他不要对方打“符儿”作证明;妻眷女子嘱咐他的,要他去打首饰,置办事物,西门庆也一向娇宠得很,一概答应,惠莲和玉楼病了,他更是关怀备至,亲力亲为;李瓶儿去世了,他“口口声声只叫:‘我的没救的姐姐,有仁义好性儿的姐姐!你怎的闪了我去了?宁可教我西门庆死了罢!我也不久 活于世了,平白活着做甚么!’”;西门庆要死了,也放不下他爱着的女子们,天真地要求她们为他发愿心,也来爱他。凡是爱他的,亲近他的,他便也以极大的热情丝毫不保留地回馈爱护回去。通读全书下来,便能明白那些貌美的女子绝非是单因钱财而倒向西门庆。《金瓶梅词话》中西门庆之外的男人,无非是一些庸俗可憎的面孔,他们没有柔情,也没有温暖,徒然拥有的也是不如西门庆精明而甚于他卑鄙的心机与算计。本来拥有李瓶儿的花子虚是个纯粹的无能废物,只会仗着钱财享乐度日,自以为能;应伯爵口口声声与西门庆称兄道弟,受了西门庆许多照顾,西门庆死后他却立刻谋算着如何剥削西门家的钱财;西门家的男女死去,前来吊唁的男男女女大都落的是些极其虚假的眼泪。以这有情有义的恶人西门庆为镜子,兰陵笑笑生描画出了一个充满了财色欲望、毫无真情的世界。男子向财向禄,女子向往穿戴饰品和地位,孟玉樓决定再嫁西门庆时,她的家人为了侵吞她的财产如苍蝇般叮扰个不停,出嫁之后,她的耳边清静了——西门家现实的权势和西门庆强势体贴的个性摆平了聒噪的家人。西门家像是这个世界上的小小乐园,隔绝了这些比西门庆本人肮脏得多的事物,随着西门庆死去,乐园垮塌消失后的众多女子也就再度落入不堪的视奸。西门庆的“好色”乃是不存于此世的一种“好情”,在普世存在的污浊之中显得清白,使人同情也使人哀叹。
而纵览西鹤的作品,也有类似的倾向。本身情恋小说这一题材,就涉及了对外部世界的描写与刻画。而西鹤的“好色”之作连携起来观看,便不得不说西鹤在他所有的“好色”之作中力图整体地展现了江户时代整个好色社会的完整姿态。《好色一代男》是世之介作为男子去遍览世间风流:“这个世界上的各式各样的男妓、妓女和风流女我都无一遗漏地见识过了”;《好色一代女》则是“我”作为女子品尽这世间的色事:“出卖色相的行当我全都干过了”;而《好色五人女》这五个故事看似没有直接的联系,却也是好色社会的分部展现。值得拿出来一说西鹤之“好色”的是《好色一人男》的男主人公世之介。他本身季即是“好色”的产物,从七岁到六十岁也一直在追求色道,即是“好色”。《好色一人男》由数个碎片化且充斥着巧合色彩的故事构成,是世之介与各色男女相遇相会相爱最终爬上床榻的故事。世之介在色事上启蒙极早,在七岁这本该懵懂的年纪就已懂得许多,并直白地表露了兴趣。他也爱一切女子,一切以肉体回馈他的人,他也以这极强的性欲去回应。世之介和西门庆不同,他作为浪荡的富家町人没有固定的家庭,于是他所见到的状况形形色色,更为多种多样——亦见到了许许多多的惨事。加藤周一先生在《日本文学史序说》中把《好色一代女》称为“一部反《好色一代男》的作品”,亦有学者支持他的观点。在两部小说的结尾,世之介与“我”看似确实走向了近似于相反的道路,一个全然不信佛业,坐了“好色丸”消失了踪影,一个脱离红尘,皈依佛身。但单单以角色的行为去揣摩西鹤的思维未免失了水准。世之介无疑是一个“好色”之徒,但他也是个西鹤借妓女小金之口指出“您是日本这片土地上不曾有的人。”的角色。世之介何是“不曾有”?在《好色一代男》第二卷之陋室的被褥一节,世之介与一名男妓相处,男妓即使知道男妓是要骗他钱财,说的可能全是谎言,他仍会问男妓:“那么,你夜间接待了令你讨厌的客人,你的心情怎么样呢?”——“即使他说的全是谎言,世之介也不认为他完全是为了骗钱才说的。”世之介不但是以肉体爱着他们,还以柔情去同情、爱怜他们。而世之介所处的社会是町人的社会,是个纵使放荡也受着日本道德、公共秩序约束的世界。町人们享乐,却无情。卖淫者受到的轻贱是各个社会共通的,情欲受到的道德压制也是共通的。《好色一代女》的“我”也是此类,一路从大夫堕落为最低贱的街娼的过程中,她几乎没有体会过感情的美好,而全是肉体之乐,这是世人给她的,是众多世人在使用她。而世之介之所以“不曾有”,显然是因为他天生的同情心和多情温情的本能。悲悯他人的他在精神上并不属于给一代女们带来悲运的这世界上的人。这样的他像是投射着好色社会众生相的摄像头,本身显得极其虚幻。西鹤显然不否认世之介的虚幻性,没有家庭的他没有落得西门庆这样极为现实的悲惨下场,而是乘着“好色丸”如泡影般消失在了海上。
在不同的时代与文化环境之中,兰陵笑笑生与井原西鹤不约而同地追逐着相似的“好色”——一种独立于暴力污浊世界的悲悯与多情,也是一种试图粉碎和攻击常理道德伦理秩序、金钱规则的软性声讨。西门庆营造的小乐园乃至他自己都被更污浊的世界毁坏殆尽,世之介也如幻影般消失在了海上,更多的一代女被社会生产了出来,层出不穷。然而从文学里看去,我们却有幸目睹了“好色”文化的遥相呼应和精神共鸣。关于此类研究之少实在是令人汗颜,这本应是要更加受我们关注的过去和未来的有力之鉴。
参考文献:
[1]《好色一代男·好色一代女·好色五人女》 [日]井原西鹤 九州出版社2000年出版
[2]《金瓶梅词话》[中]兰陵笑笑生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3]王向远.浮世之草 好色有道——井原西鹤“好色物”的审美构造[J].东北亚外语研究,2016,4(03):67-73.
[4]李云.论西门庆的悲剧形象和命运[J].泰山学院学报,2016,38(01):69-73.
[5]李云.论西门庆的有情形象及其对贾宝玉的影响[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6(04):493-496.
[6]窦苗.《金瓶梅》讽刺笔法中的冷热对书——透视李瓶儿、西门庆、潘金莲的死亡悲剧[J].黑河学刊,2013(12):34-36+39.
[7]张义宏.日本《金瓶梅》译介述评[J].日本研究,2012(04):117-121.
[8]止庵.非凡的“好色”论[J].出版广角,2004(12):56-57.
[9]吕元明.井原西鹤创作简论——日本江户一代历史的伟大描绘者[J].日本研究,1985(02):58-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