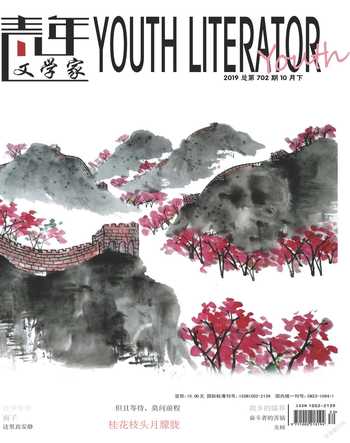从《红豆》看百花文学中的爱情选择
黄娟
摘 要:《红豆》是百花文学时期的典型作品之一,通过女大学生江玫在爱情上的选择,表现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最终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小说发表后适逢反右运动,由于女主人公江玫面对爱情选择的犹疑,围绕小说的思想倾向展开了争论。虽然小说在主观意图和客观效果上产生了分裂,但也流露出女性最真实的情感心理,这种分裂在当时遭到批评无可厚非。在今天看来,《红豆》摆脱了同时代其他文学的公式化倾向,表现了人真实的人性和人情。
关键词:百花文学;《红豆》;爱情;革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30-0-02
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在苏联“解冻文学”的影响下,中国文学思想和创作出现了新的朝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给文学注入了新的生机,出现了一批揭示社会主义内部矛盾的小说,被称为“百花文学”,洪子诚将这一时期称为“百花时代”。百花文学的典型代表一方面是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等,这些作品大胆干预生活,深刻反映人民内部的复杂矛盾,揭露和批判了官僚主义和其他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消极现象。另一方面作为“百花文学”的还有宗璞的《红豆》、陆文夫的《小巷深处》、邓友梅的《在悬崖上》等,这些作品涉及了社会主义文学较少触及的爱情生活题材,揭示了人物丰富的情感世界。
宗璞的《红豆》发表于1975年《人民文学》“革新特大号”上,以知识分子的情感世界为描写对象的《红豆》一经发表就引起了文学界的争论,随后不久,《红豆》和其他“百花作品”一起受到批判。围绕《红豆》的论争主要集中在女主人公江玫对待爱情选择的态度上,宗璞将江玫和齐虹的爱情放置在解放战争胜利前的大背景下,革命事业与爱情在江玫身上无法两全。虽然江玫最终放弃了爱情,成为一名党的工作者,但就文本和读者阅读体验而言,江玫并没有完全放下对齐虹的感情,以至于六年后见到两粒小红豆勾起她对往事的回忆。大多数人认为小说对江玫的愛情描写不妥当,使得作品的思想倾向不健康,一些作家也发表了文章进行批评。批评集中认为宗璞没有表现出知识分子怎样经历着曲折痛苦的道路走向革命事业,没有表现出知识分子彻底的改造思想情感。宗璞坦然接受批评者对《红豆》的种种批评,她想刻画的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成长,但在写作过程中没有比江玫站得更高,以至于带来了主观意图和客观效果之间的差距。换言之,百花时期的爱情题材写作也没能突破十七年的框架,《红豆》的出现只是作者无心之失的结果。
“双百方针”的提出带来了文学的“解冻”,为文学提供了“干预生活”,写人性、人情美的空间。这之前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由于带有所谓的资产阶级情调受到批判,《红豆》中的江玫也带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气息,“白天上课弹琴,晚上坐图书馆看参考书,礼拜六就回家。母亲从摆着夹竹桃的台阶上走下来迎接她,生活就像那粉红色的夹竹桃一样与世隔绝。”[1]她的这些小资产阶级气息正是她和齐虹恋爱的基础,同时她又“嫌弃那些做官的和有钱人”,带有“一种清高的气息”,这又为她后来向事业的转变提供了准备。《红豆》中革命和恋爱的关系不同于左翼时期“革命+恋爱”的模式,江玫面对的是爱情和革命事业的选择。作者把江玫的恋爱心理刻画的十分细腻,她第一次见到齐虹就观察齐虹有“一张清秀的象牙色的脸,轮廓分明,长长的眼睛,有一种迷惘的神气”,并且觉得齐虹一定没有看见她,“不知为什么,这个念头使她觉得很遗憾。”[1]江玫和齐虹在一起时总是觉得时间不够长,“她甚至希望路更长一些,好让她和齐虹无止境地谈着贝多芬和肖邦,谈着苏东坡和李商隐,谈着济慈和勃朗宁。”[1]在他们相爱以后,江玫也觉察到“她和齐虹的看法永远也不会一致”,但她放不下齐虹,她和齐虹争吵、流泪,她可以说“我和齐虹,照我看,有很多地方,是永远也不会一致的。”[1]但她却不允许别人对齐虹的批评,萧素顺着她的话说“齐虹憎恨人,他认为无论什么人彼此都是相互利用。”江玫就激烈的反驳说“你怎么能这样说他!我爱他!我告诉你我爱他!江玫早就忘了她和齐虹之间的分歧,觉得有一团火在胸中烧。”[1]江玫去参加游行,思想却不能集中,“她是惦记着那在西楼窗下徘徊的那个年青人”。处在爱情夹缝中的江玫“一天天地消瘦了,苍白了”,萧素劝江玫忘掉齐虹,江玫迟钝地说:“忘掉他——忘掉他——我死了,就自然会忘掉。”[1]作者大胆深入江玫的内心世界,细致入微地写出了她作为一个知识女性所特有的所谓小资产阶级感情,以及恋爱中纠结复杂的心理变化。
齐虹是个怎样的人呢?作者对齐虹的刻画并不全面,齐虹是资本家出身,他的外貌是从江玫的眼睛看到的,虽然学的是物理,但他热爱钢琴。从外表看,他们很相配,关于他们在一起的描写也非常动人。齐虹说“你甜蜜的爱,就是珍宝,我不屑把处境跟帝王对调”,[1]他用莎士比亚的诗表达自己的真心。得知要迁往美国,齐虹冒着雨跑到江玫家请求她跟自己一起离开,直到离开前一刻他还带着一丝希望,希望江玫能够跟他一起走。从爱情的角度看,齐虹是真的爱江玫,甚至后来“齐虹脸上那种漠不关心神气消失了,换上的是提心吊胆的急躁和忧愁。”[1]也许作者自己也是纠结的,她一方面为江玫和齐虹的爱而感动,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自己的作品主题,最后导致齐虹这个人物形象并不丰满。齐虹说他恨人类,却没有交代齐虹“恨”的缘由,他会突然的暴躁,这和他身上的艺术气息又是多么不相称,他对人生不信任,对爱情也不信任,他要监视一切。作者为什么如此描写齐虹?其实细读文本,齐虹并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甚至他所有活动的中心都是爱江玫,尽管他不喜欢萧素,但也没有过多的批评。反而萧素评价齐虹是一个自私自利和残暴的人,不得不说作者这样安排是为小说的主题服务,也能够理解为何江玫在觉察到齐虹与自己的差异时却仍旧不能放手。
在江玫和齐虹中间还有一个萧素,萧素是象征革命事业的一方,而齐虹是象征爱情的那一方,受萧素的影响包括亲身参加诗歌朗诵、游行等活动,加上与齐虹精神上的差异,江玫与齐虹渐行渐远。批评者认为“一个人的思想和感情是统一的,是和阶级立场不可分割的。对于恋爱的态度,也是表现一个人的立场和观点的。” “批评者一致关心的是小说主人公女大学生江玫在革命和爱情之间应该作何选择,走上革命道路后心中还应不应该保留爱情的位置,而不是爱情本身对一个人——一个女性是不是重要。”[2]爱情本身就是私人性的情感问题,对于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大学生来说,爱情是感性多于理性,尤其像齐虹这样一位才华、相貌出众男生,这些对于一位女性的情感来说无疑加深了痛苦,就像江玫她明明觉察到自己与齐虹在某些方面的看法永远也不会一致,却又留恋着齐虹。江玫最终放弃爱情又是必然的,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她的精神是向着革命事业的,在她的成长中,“她和母亲一样,憎恶权势,憎恶金钱”,加上萧素的影响,萧素为江玫母亲卖血筹钱进一步摧垮了江玫的心理防线,最后得知自己父亲是屈死的,这些必然导致江玫走上同萧素一样的道路,尽管割舍感情是痛苦的,但这是江玫唯一的选择。
齐虹去美国的那天,江玫着急地寻找齐虹,她心里充满了不舍,但还是毅然拒绝了齐虹,“我不后悔”,“齐虹看着她的眼睛,还是那亮得奇怪的火光”。批评者认为江玫的这句“我不后悔”实际上表现出来的是后悔,当她再次回到校园,再次看到那两粒红豆,想起和齐虹在一起的故事,她表现出的细腻的情感似乎都表明了她后悔了。但换个角度来看,齐虹算是江玫的初恋,作为一名女性,江玫对齐虹的投入了太多的情感,而恰巧小说的作者宗璞也是一位女性,面对这样的感情很难不被感染,宗璞自己也说:“在写这个小说时,自己也被这爱情故事所吸引了。”批判者站在更高的角度,关心的是江玫在爱情上所做的选择,以及选择的态度是否彻底,从而来判断这是否符合当时的主流,但却忽略了作为一个女性对待爱情的态度,是否走上革命事业之后连女性的私人情感也应一并舍弃。有人认为作品宣扬了爱情至上、爱情永恒,革命破坏了个人爱情和幸福,这难道不是放大了江玫和齐虹之间的爱情,忽略小说对江玫革命性一面的描写?对于朱一清提出的如果齐虹回来了,江玫会怎么办?答案还是会像小说结尾所说的“江玫果然没有后悔。这时她已经真的成长为一个好的党的工作者了。”[1]六年前的江玫是不谙世事的大学生,感性多于理性,一头栽进爱情里难以割舍,六年后的江玫已经成长为一位党的工作者,已有足够的理性面对生活,即使有所留恋,也只是停留在对过往感情的回忆。再者,对于齐虹是否有改变,我们也无从分析,毕竟作者对于齐虹的刻画还留有很大的空隙。这么说并不是否定当时批评者对于《红豆》的批评,《红豆》是短命的“百花时代”的最后一批绝唱,随后受到批判,这与五十年代的文学的复杂关系密不可分,批评者大都站在政治的立场上评判《红豆》的价值,连作者本人也承认当时想写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成长,但是不想主观意图和客观效果不一致。洪子诚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里指出是“投身革命与个人情感生活,在小说中没有被处理成一致”。[3]而小说的这种矛盾和分裂在今天看来是有价值的,正像宗璞自己所说的:“有时这种欣赏是下意识的,在作品中自然地流露了出来。”[4]这些在当时文化语境里不被接受的思想、感情恰好就是自然真实的情感的流露,是人类的自由精神和生命本能的表现,表达的也正是人类生活最真实的感受。这也正是《红豆》和同时期其他作品的不同之处,摆脱了公式化的影响,到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重放的鲜花》一书,才得以与广大读者再次见面,人们才能够再次审视《红豆》作为“百花文学”的价值。
当时文艺界对于《红豆》江玫形象的争议主要是她在爱情选择上的犹疑,尽管小说的结局在文章中早已做了大量的铺垫,但是江玫对齐虹的感情没有像《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对余永泽的感情转变一样,这就为《红豆》留下了被讨论和批评的空间。如果换个角度看,《紅豆》表现出的爱情的魅力正在于情的长久与难忘,如果人能够轻易就抛弃一段感情,那这感情也不能给人的精神带来多大的影响,主人公也不能以她丰富复杂的情感世界感染读者。为了江玫的社会理性与主流文化形态保持一致,爱情选择的结局早已注定。宗璞自己也谈到:“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不断地出现十字路口,需要无比慎重,无比勇敢,需要以斩断万路情丝的献身精神,一次次做出抉择。祖国、革命和爱情、家庭的取舍、新我和旧我的决裂,种种搏斗都是在自身的血肉之中进行,当然是十分痛苦。”[5]正是这种在自身血肉之中进行搏斗的痛苦,才表现出知识分子在人生十字路口选择的艰难以及对这选择的不后悔,从而增强作品的感染力。
参考文献:
[1]宗璞.《红豆》[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0:4、6、9、13、24、12、17、35.
[2]毕光明.难以突破的禁区——《红豆》的爱情书写及其阐释的再考察.《中国当代文学论争档案·小说篇(二)》[J].2010(4).
[3]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红豆》的问题在哪里?——一个座谈会记录摘要.《人民文学》[J].1958(9).
[5]宗璞.《中国女作家小说选——<红豆>忆谈》[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