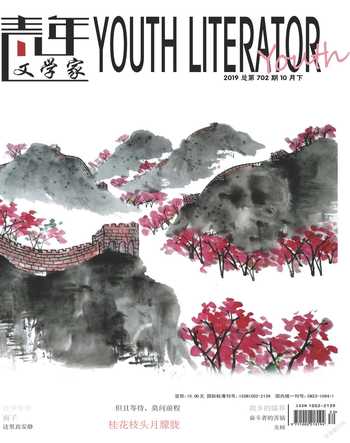这里真安静
朱紫梦
一
我到过一个地方,静谧得像过去,神秘得像未来。
是阿松带我去的。阿松是干妈的翻译,是一个长得挺像安徽人的越南人。那天早晨,他不知怎么摸开了我酒店房间的门,在我吃完早饭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坐在酒店的落地窗前等我了。我不由悚然一惊,因为除了很熟识我的干妈,还从来没有人在这个窗前出现过。
他朝我粲然地一笑,说要带我去一处很少有游客知道的神圣地方。我相信了他,他一定是知道些异国人没听过的地方的,就冲他头一次朝我露了这么多颗牙。
我打开房门,那里还等着两位在旅行社工作的阿姨,阿松的同事,也算我在这里的亲人。她们都没比我大几岁,对于清早出发去看景之类的事,兴趣也很大。于是,一行四人。
阿松是幾个男生里开车最规矩的。该超车的时候超车,该鸣笛的时候鸣笛,有时跟着车里的华语老歌哼上几句,除此之外,一句话都不讲。坐他的车很安稳,也很放心。只是有一点不好,坐他的车总莫名爱叫人发困,这样一来,就省去了很多风景、很多音乐。
这次的路上却不一样。他虽依旧是一句话不说,却被略微锁起的眉头和紧把方向盘的手暴露了心情。阿松的表情控制得越艰难,目的地也就变得越新鲜,越神秘。
二
我们开着借来的敞篷轿跑,从酒店出发,沿着海岸线向西方向,过了我曾以为永远没有尽头的“海滨浴场”,过了我曾以为永远也不会消散的人山人海,开上了一条我印象中开往北京郊区的萧瑟山路。
我呆呆地看着周围的风景。烟火气,浓到无法再浓;清新,又清新到了无法再清新。它们怎么就这样天然地融合在一起了呢?很难想象一座以旅游业闻名的城市会放逐出一块如此原始土地,让它孤零零地待在城市的另一端。我从副驾上站起来,把身子从天窗上探出去,张开双臂——左手是花,右手是海。我想深深地细嗅每一朵小花,直到知觉化为乌有;想在蔚蓝的空气里成为海里的浪,风中的云;想一次又一次地触及那冰冷,甩开鞋子,扥起裤脚,冲进海浪,全身湿透,在所不惜……
我有点希望阿松把车停住告诉我们就是这儿了,因为那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瞬,我情愿在淡泊中终了此生。我又希望他能继续向前开,把山路都走穷。我想知道这片海是不是也没有一个尽头。
他没有停下来。
山路越来越陡,预示着前面应该有大景象。
他停了下来,在快到山顶的时候。
三
我有点紧张地拨开草丛和树杈,朝着山路尽头的方向。今天阳光很好,目的地竟是与我们隔海相望的对面的那座山。
对面是金兰湾。阿松说那里是越南人民反抗压迫的起点,是……
我突然觉得有点不忍去听,情愿只凭自己想象。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反抗压迫”这个词组十分敏感。可惜,我的目光无法跨越一整片蔚蓝到达另一座山丘,我的手也遮挡不住一直向眼中冲刺的阳光。连让我胡乱猜想的由头也十分依稀。
例如,为什么山的左侧明显要比右边荒芜呢,这里一定发生过什么激烈的战役,使这一侧的植被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也许,是一次越南人民的奋勇抵抗?
又如,为什么山腰处竖了好几排石柱呢?是墓碑?那么纪念的又是谁呢?是军队将领,还是民族英雄?
还有,为什么这座山上繁花满树,对面的山上却没有一点彩色呢?有人将它们偷走了,还是有人将它们没收了?
……
这些,都一定有故事,而且是极其跌宕,甚至极其壮烈的故事。
发生在被侵略国家的故事,未必都是可悲的。作为特殊时代的一个特殊参与者,那里会包藏着许多尝试、倔强、顽强乃至牺牲。也许,世界反法西斯战役的某次决定性战役,曾从这里孕育。我盯着海浪从对面涌来一波又一波,深深可惜多少动人的故事全都化作了液泡。
这些故事隐匿于闹市,沉淀成宁静。民族、历史的大课题,既在那里定格,又在那里混沌。酸甜苦辣的滋味,弥漫于树丛,弥漫于海雾。海浪波涛隔开的,是一座历史的纪念碑。
果然,如果这里是目的地,我再也不想在淡泊中终了此生。我现在想的是,我在离别之际才读懂了它。
我在离别之际才读懂了它——除却震撼之外,这句话包含着一份检讨。我们一直享受它、消费它,却又轻视它。它花了很多年的目光、脚力走出了一条路,我们却常常嘲笑它为何不走另外一条。它好不容易在沧海横流中保住了一份家业、一份尊严,我们却嫌它被第三产业占领,手心朝上。这次在烟岚渺渺中看它,终于吃惊,终于惭愧,终于懊恼。
四
曾让人怦然心动的花和海,又化成了万里之下的星星点点。我没有走遍这里的山山水水,却了解了一个国家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