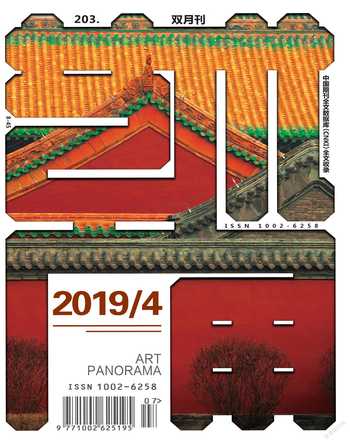独立剧场:新世纪中国先锋戏剧的生存空间
陈吉德
独立剧场的“独立”意味着民间、边缘、底层和自由。进入新世纪,曾经冒险越界、披荆斩棘的中国先锋戏剧开始分化。有的跟商业把酒言欢,拜倒在票房的裙裾之下,如孟京辉;有的急流勇退,投身于新媒体,如牟森;有的漂洋过海,另谋发展,如张广天。大部分先锋戏剧依然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寻觅新的生存空间,独立剧场就是其重要的发展场域。
一
独立剧场并非新世纪才有的新生事物,之前有上海的新光小剧场,北京中戏的黑匣子剧场、广州的水边吧,等等。但是独立剧场的大量出现却是新世纪之后的事,它们成为中国先锋戏剧新的生存空间。从地域上看,独立剧场主要分布于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大城市;从整体定位上看,有的侧重于商业性,有的侧重于艺术性;从生存状态上看,有的如鱼得水,有的如履薄冰。
北京一直是先锋戏剧的重镇,这与独立剧场的出现不无关系。作为首都,北京的独立剧场出现时间早,分布较广。新世纪较早出现的是北剧场。北剧场2002年3月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小剧场的基础上开始筹建,2003年1月开门营业,是当时北京首家民营剧场。起初的投资人是台湾赖声川,后来变为袁鸿。
蓬蒿剧场,又称蓬蒿人剧场,是北京最小的小剧场,可容纳100人观看演出。2008年,牙科医生王翔投资150万元,在寸土寸金的南锣鼓巷中觅得一个民国时期留下的四合院,改造成剧场,属于非盈利性公益性剧场。“蓬蒿”一词取自李白的诗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反其意而用之,希望更多的普通人走进剧场。这恰恰体现出先锋戏剧民间和底层的艺术定位。蓬蒿剧场的剧作注重文学性,推崇剧本的重要性,引领着剧本的创新思潮。剧本不注意商业性,讲究童真和朴拙,尤其关注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呈现出浓浓的人文气息。剧场的梦想是“不是一个种族一个阶层,而是所有人,共同完成由动物性的匮乏性低层需要向人的存在认知性高层需要迈进,走向心灵的丰富和高贵!”[1]如今的蓬蒿剧场已经成为北京先锋戏剧重要的演出场所。
如果说蓬蒿剧场追求的是“大众”,尚剧场追求的则是“小众”。该剧场位于方家胡同46号园区F座,占地面积约700平米,核定坐席282座,隶属于北京尚剧舞台艺术中心,原为上世纪50年代轻工机械厂礼堂旧址,投资人为刘一萌和荣伟杰。剧场外观是醒目的立体“尚”字形红色钢制结构,成为东城区剧场文化的标志。尚剧场重在一个“尚”字。“尚”字有崇尚、推崇之意,拆开来看是“小”“同”二字的变体。“小”“同”意为小范围的认同,不追求大众化的认同。拒绝大众,讲究小众,正是先锋艺术的受众定位。尚剧场拒绝生活的庸碌与烦琐,崇尚生命的质感,特别注重情感深处的灵魂冲动,力求用温暖的阳光照亮心灵的每一个角落。
在北京,不仅有单独的小剧场,还有民间小剧场群,这就是北京天艺同歌国际文化公司董事长的樊星变买所有家产、在2009年创建的繁星戏剧村。戏剧村位于北京市西長安街核心区域,经营面积达5000平方米,以“生产戏剧、创意剧场、倡导文艺生活、传递人文关怀”为理念,以“场制合一”为运营模式。所谓“场制合一”,就是将剧场演出和戏剧制作融为一体,两条腿走路。戏剧村注重不同思想的碰撞,认为剧场应该是让人思考的地方,因此打出一个口号:“人人都是思想家。”戏剧村就是四合院里的百老汇,错落有致,集创作、运营、演出、交易、展览为一体,点亮了民众的文化生活。多年来,戏剧村“通过剧目来吸引观众获取利益的同时,根据商业化的运营机制打造了集合文艺创作、剧场演出、艺术展览、主题餐饮、咖啡图书等综合性的文艺园区。”[2]
上海是新世纪中国先锋戏剧发展的另一个重镇。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的独立剧场并不比北京少,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下河迷仓。剧场位于上海南端龙华港的一幢普通的小楼三层,此处习惯上被称为“下河”。法人代表王景国早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在美国生活多年,回到上海后,于2000年在肇嘉浜路创办了“真汉咖啡剧场”,失败后于2004年创办了下河迷仓(DOWN-STREAM GARAGE)。“迷仓”之名重在“迷”。这是执迷者的“沉迷”之处,也是清醒者的“入迷”所在。柏拉图说,诗人写诗要陷入一种迷狂状态。对,从事艺术的人根本离不开“迷”。有“迷”才有诗意,无“迷”就是匠人。迷仓是梦开始的地方,很多艺术爱好者在这里知“迷”不误,相识相知,共同前行,因此成为上海先锋戏剧的重要力量。剧场的独特之处是完全免费使用,且只对业余剧团开放。当然,所有的演出也无需购票。“草台班”“组合嬲”“测不准”“802”“九维”“聆舞”“越界”等民间戏剧团体都是在下河迷仓的扶持下逐渐“长大成人”,取得各自的成就。
与下河迷仓只专注于戏剧的“单条腿走路”原则不同的是,“可当代艺术中心”坚持“多条腿走路”原则,注重多种艺术形式的综合性和延展性。它建成于2007年,坐落于凯旋路的创邑源里,涵盖当代多个艺术门类。创办者为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教师周可。剧场由上海大明橡胶厂改造而成,内部面积400平米,参照美国外百老汇多个剧场设计建造而成,可同时容纳240人观看演出。中心定位在一个“可”字。“可”者,“可能”也,指创造一切的“可能性”:为多种艺术形式创造结合的“可能性”,为艺术开辟想象空间的“可能性”,为商业注入艺术内涵的“可能性”,为当代艺术提供发布与交流平台的“可能性”,为商业寻找与艺术相结合的“可能性”。这里经常举办演出、朗读会、论坛,成为上海先锋戏剧的重要生长点。
提到上海的独立剧场,不能不提到来自北京的孟京辉。下河迷仓关门后的2014年,孟京辉将位于静安区江宁路466号的艺海剧院5楼小剧场改造并重新命名为“先锋剧场”。这是孟京辉在北京蜂巢剧场之外开设的第二个专属剧场,成为孟氏先锋戏剧在上海演出的大本营。先锋剧场由孟京辉担任艺术总监,经营模式与蜂巢剧场完全相同,集创作、生产、展示、活动于一体,每年实现近200场的演出量。《恋爱的犀牛》《两只狗的生活意见》等孟氏先锋戏剧都在这里演出过。
除北京、上海外,全国其他一些城市也有独立剧场,以实验探索精神著称的广州“水边吧”即是一例。水边吧始建于1995年,因位于天河区沙河涌畔而得名,1999年被拆除。水边吧的主人江南藜果原名黄利国,1990年从广州暨南大学新闻系研究生毕业后从事媒体工作,后辞职专心从事实验戏剧。现在的水边吧位于石牌东陶育路暨南花园15栋。偏僻安静的地理位置注定了水边吧不可能生意兴隆。江南藜果只希望水边吧成为尽情玩耍的欢乐场和实验场,秉承自尊、自强、自觉、自为、自在、自省、自由的独立精神。水边吧的实验戏剧,是它最吸引人的标签。它尤其注意剧场的身体性探索,认为在所有艺术门类中,戏剧最具有身体性特征,离开身体性,戏剧便不复存在。剧场就是展现身体的场所,身体成为剧场开发不尽的艺术资源。
作为六朝古都,南京汇聚了几十所高校,易于接受新鲜前卫事物的莘莘学子是先锋戏剧生存的重要土壤。南京的独立剧场虽然相对较少,但先锋性比较明显。比较有名的是南京大学的黑匣子剧场,面积约200平米,可容纳100余名观众。典型的中央式舞台,三面是可移动的座椅,不设座位号,观众随机而坐,来迟了只好坐在地上。与演员的近距离接触可以让观众获得在常规大剧场无法体验到的代入感和亲切感。多年来,在文学院戏剧影视研究所吕效平教授的带领下,黑匣子的演出非常活跃,尤其是一些前卫性、实验性的戏剧,可以在这里生根发牙。《洛丽塔》《黎明之后看夕阳》《有人将至》等作品均在此演出过。黑匣子虽然远离主城区,但依然成为众多戏剧爱好者的艺术圣殿。南京艺术学院也有一个黑匣子。2018年,学院成立了赖声川戏剧艺术研究中心,带动了黑匣子的发展。除上述两个“黑匣子”外,位于奥体中心的保利剧院(全国连锁)也有一个小剧场,有时免费提供给业余剧团演出使用。
通过上述挂一漏万的描述可以看出,独立剧场已经成为新世纪中国先锋戏剧重要的生存空间。它像一方肥美的水草,为先锋戏剧的成长提供了充足的养料。假如没有这些独立剧场,先锋戏剧注定像无处皈依的游子在大地上流浪。
二
独立剧场对于新世纪中国先锋戏剧的重要意义在于支撑起日常的戏剧演出,积极进行先锋戏剧的艺术实验。繁星戏剧村创建以来推出了《那次奋不顾身的爱情》《那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一触钟情》《一夜一生》《狼》《爱在无爱城》《大话四梦》《第四类情感》等几十部小剧场经典话剧。结合话剧、音乐剧、戏曲、舞蹈剧等现成资源,戏剧村主推“跨界”理念,追求“混搭”风格,所以在进行先锋戏剧实验时,注重与其他艺术的碰撞交融。原创爱情经典喜剧《那次奋不顾身的爱情》采用多维度的视听手段,打造出超常的3D通感戏剧。观众可以在剧场内获得全方位的身临其境的观看体验。戏剧一开场就是别开生面的万圣节化妆舞会,迅速把观众带入剧情。观剧过程中,观众可以和演员亲密接触,共同见证一段铭心刻骨的旷世真爱。改编自法国著名喜剧作家居伊·富瓦锡《心心相印》的实验戏剧《一触钟情》谱写的是两个小人物的恋爱狂想曲,演出百场,场场爆满,口碑极佳。该剧的舞美设计遵循极简主义的美学理念,台词妙语连珠,插科打诨,加入了很多光电设备,将爱情的臆想化境界表现得淋漓尽致。话剧《一夜一生》有意加入许多戏曲元素,这种混搭呈现出别样的神韵,让观众目不暇接,毫无疲惫感。话剧《大话四梦》以梦为视角,重新解读汤显祖的“臨川四梦”。剧中四位人物丽娘、卢生、南柯、紫钗,分别对应着《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紫钗记》。作者汤显祖和卢生由一人饰演,因此,汤显祖创造了梦,也审视了梦。四人寻梦而去,重入轮回……戏剧村还注意观众的参与感,演员经常进入观众区进行表演。在话剧《爱在无爱城》中,当沙法官因妄城的愚昧法律而无法跟年轻貌美的比恩卡在一起时,沙法官就站在观众席中对比恩卡倾诉衷肠。此时,观众几乎可以听到沙法官的呼吸声,闻到他身上散发的气息,切身体验着他对比恩卡的真挚情感。
广州水边吧一直致力于先锋戏剧的实验。早年,他们在酒吧、麦当劳等生活场景中演出环境戏剧,排演过《广州档案》《孔乙己》《麦当劳主义》等作品。2000年,水边吧推出了先锋话剧《孔乙己和三个女人的故事》。该剧取材于鲁迅的《孔乙己》《阿Q正传》《过客》《药》《祝福》《长明灯》《狂人日记》《纪念刘和珍君》《影的告别》等诸多作品,各场次之间插入与剧情无关的鲁迅散文或杂文原著片断,共同演绎出传统文化的“吃人”本质。2001年,演出即兴话剧《今夜不能没有性》,内容大胆前卫。2006年的《手,X手手的手》不但全部即兴,还有观众全程参与。2009年秋至2010年秋举办身体戏剧免费工作坊,但应者寥寥。2011年推出极为前卫的话剧《阴道独白》,主题是唤醒女性身体意识的觉醒和对女性身体的尊重。2012年推出话剧《蹲》第六版。全剧都是蹲着的戏,加入了广州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对抗,基调戏谑、风趣、轻松。
除支撑起日常的戏剧演出外,独立剧场还举办各种戏剧节,从而加强了戏剧同仁之间的联系,扩大了先锋戏剧的影响。最有影响的是蓬蒿剧场举办的“北京·南锣鼓巷戏剧节”。这是北京第一个由民间剧场发起、政府支持举办的具备国际水准和全球视野的戏剧艺术节,也是国内最有活力、最具交流深度的国际戏剧节。从2010年到现在,已经连续举办了九届,出现了很多有探索性、先锋性的作品,如第一届的话剧《锣鼓巷的故事》,第二届的话剧《遗嘱》《都》,第三届的独角戏《百年孤独》、话剧《猫城记》,第四届的小剧场实验京剧《杀子》、肢体剧《战台湾》、实验川剧《情叹》、梦幻剧《蓦然回首》、多媒体互动装置《站立的人》、默剧《无形的桥》,第五届的多媒体独角戏《朱丽小姐》、社会情境剧《〈人民公敌〉事件》,第六届的肢体剧《步行训练》、文献剧《关于美好新世界》,第七届的实验傀儡剧《科利奥兰纳斯》,第八届的默剧《最后的船》,第九届的独角戏集《声音机》、新锐话剧《Z21》。锣鼓巷戏剧节注意戏剧作品的温度、灵性、思想和意义,让更多的人以艺术的方式触摸真实的生命体验。
上海的下河迷仓经常举办“秋收季节——当代表演艺术年度交流展演”。2009年活动中演出的剧目有上海臧宁贝的《江河行》、李震的《皮相》、聆舞团的《明年的这个时候》、友缘剧社的《沃伊采克》、草台班的《小社会》、测不准戏剧机构的《浮游语切切》,北京饭剧团的《我说》、大臀表演研究小组的《晚间新闻报道》、新工人剧场的《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广州直观工作室的《戏游记之“香·体”》,济南凌云肢体游击队的《准备》等先锋性作品。2010年活动中演出的剧目有上海易剧场《词·肉》、草台班的《小社会第二卷》、小珂《病房III清·明》、不乱扭的《一点点就够了》、任明炀工作室的《好好好》、张渊的《形秽》,北京优戏剧工作室的《模棱两可》、薪传实验剧团的《自我控诉》、陶身体剧场的《瞬间》、广州林春园的《住在砖墙里的作家》、济南凌云肢体游击队的《缺席》等先锋性作品。
此外,独立剧场还注意培养编导演等人才,为先锋戏剧的发展储备了后续的力量。比较明显的是一些高校的黑匣子剧场。这些剧场大都为戏剧专业或相关专业而设置,虽然设施相对简陋,但为学生的训练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三
独立剧场重在“独立”,“独立”就意味着自强自立、自给自足、自负盈亏。就目前的实际情况看,独立剧场大都处境艰难,除非是有比较强的票房号召力,比如孟京辉投资的上海艺海剧院小剧场。开业以来,不仅上演孟京辉本人的作品,也上演其他有一定艺术水准的作品,所以盈利是肯定的。
以其他方式的盈利来贴补演出亏损是大多数独立剧场不得已的做法。以戏养戏是南京大学黑匣子剧场的生存之道。剧场原来是一个排练厅,一位学生家长慷慨投资,提供了灯光和座位,将其改造成一个小剧场。演出票价低到十几元,最多几十元,几乎场场亏损,可每场演出都有院系在补贴,而院系补贴的钱就是现象级话剧《蒋公的面子》源源不断的票房收入。迄今为止已经补贴了几十万元。如果没有《蒋公的面子》,不知黑匣子是一种什么样的处境?
广州的水边吧位于居民区深处,其定位是不向任何机构献媚,不与任何势力结盟。水边吧在经营上以销售花雕酒、女儿红系列老酒为主,以销售“三碗不过岗”“自由的天空”等特色酒为辅,另外还有江南香干、水边秘制牛肉、水边吧椒盐鸭排、孔乙己茴香豆等特色小吃。以商养戏成为水边吧的生存之道。
北京蓬蒿剧场的生存之道是以医养戏。主人王翔是一位著名牙医,在京城开了三个牙科诊所,成为剧场生活的重要“血源”。十多年来总计补贴1000余万元。在此情况下,剧场尚能守住艺术的纯洁,秉持探索性和实验性。孰料,2016年,剧场租用的四合院由租转售,王翔使出浑身解数,完成首付过户,尚负债4000余万元。雪上加霜的是王翔经营的两个诊所因搬迁,遭遇房租暴涨,无法正常为剧场“输血”。危难之际,剧场尝试开发戏剧衍生产品,微信小店上线。拒绝堕落,捍卫尊严,剧场一直在努力。
以戏养戏,以商养戏,以医养戏,尚能维持运转,坚守梦想,这已属幸运。不幸的是有些独立剧场无法维持生计,慨然断腕,轰然倒地。最具悲剧性的是上海下河迷仓。迷仓在2013年底,终因财力不支,无法交纳房租而关门歇业。同样悲剧收场的还有北京的北剧场。从2003年1月开门营业至2005年9月倒闭,仅仅生存了两年多时间。其间上演过孟京辉的《恋爱的犀牛》、赖声川的《千禧夜,我们说相声》等先锋性戏剧,在关门前还举办了2005年大学生戏剧节。
在大众商业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今天,作为非主流、民间化的独立剧场必然处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要抗拒媚俗,追求艺术的品位;另一方面又要谋求生存之道,无法避免商业性,如果过于追求艺术性,可能无法维持生计;如果过于追求商业性,又可能伤及艺术性,甚至不自覺走向庸俗和堕落,因此,二者的平衡点很难把握。但不管怎样,独立剧场无疑为新世纪中国先锋戏剧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生存空间,功不可没!
注释:
[1]孙晓星:《再剧场——独立戏剧的城市地图》,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2]鲁昕:《近十年民营小剧场戏剧的特点研究——以“繁星戏剧村”为中心》,山西师范大学2017届硕士学位论文,第17页。
(责任编辑 胡海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