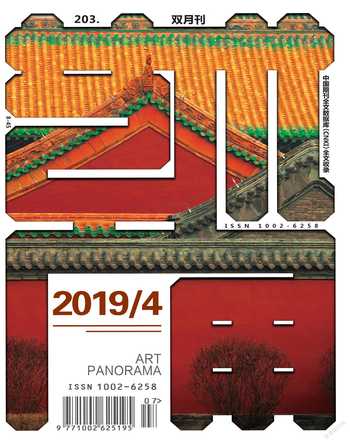中国当代美术创作环境刍议
冯利源
美术创作的根本是通过审美的方式表达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理解,也体现对所处时代社会变化发展中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其中美术创作的环境又对作品产生直接的影响。当代美术创作取决于艺术家对时代精神的把握,是从传统语言的再创造中寻求一种“自由”,但这种再创造并不是没有规律可循,也绝对不是一个与自为存在的主体相对峙的现象。[1]
从近代美术创作的历史发展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当时中国所处的环境和所面临的困境是一次有意义的变革,为中国文化与国际文化的接轨取得了不可磨没的功绩。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开始,1979年的“星星画展”以及1985年的美术思潮又把中国当代艺术推向了风口浪尖,是坚持以苏联的契斯哈柯夫为代表的“苏派”素描教学方法,还是打破固态、以欧美的时尚前卫艺术为榜样,成为困境中的中国当代艺术未来发展方向的争论焦点。黄永砯、王广义、高名潞、徐冰、舒群、张晓刚、毛旭辉、朱澄等人,以新生的锐气和巨大的活力猛烈地冲击着旧传统、旧观念、旧格局、旧方法,《美术思潮》1985年第1期上的《中央美院师生关于全国美展座谈会纪要》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据作者费大为介绍,出席座谈会的师生不仅尖锐批评了六届美展重题材、轻艺术的倾向,还大胆批评了美术与社会交流渠道单一化的问题,即“完全由政府部门组织展览会,负责出版物”的问题。有发言者尖锐地指出“流通渠道的唯一性是不利于美术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的。”[2]
纵观历史,当代美术创作的现状并不令人乐观,正如陈绶祥先生所说:“市场意识形态统治了一切,利益之轴磨损了一切我们可以称之为精神的意识——包括宗教意识都成为浮夸的标签。”[3]中国当代美术创作在徘徊与艰难的环境中生存与探索,美术作品的创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在中国当下的艺术环境中凸显了与艺术家本质创作精神相互背离的种种现象,本文以“指摘”的方式,从笔者所遇见的现象中分析中国当代美术创作环境中所存在的相关问题,虽言辞直截了当,但实属肺腑之言。
指摘之一:中国当代美术创作动机的不明确性。
当我们面对一种艺术形式或者一种艺术创造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对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进行深入的思考,从全球范围看,对于不同领域的文化现象来说,如何交织如何碰撞是引发个体文化思辨的决定因素。不管我们面对什么样的艺术形式,其所存在的艺术本体和艺术语境对于社会的思考是不能忽略的。不管是本土艺术还是外来艺术,我们都要用正确的方式去解读去领会,扬长避短,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保持对于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生命力,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中国当下某些美术创作缺少为社会生活服务的动机,缺少对于时代精神和时代主旋律的深入挖掘和真切表现。从绘画历史发展过程看,每一时期的经典美术创作作品都是所处时代真实社会生活的写照,比如秦汉时期,疆域辽阔,国势强盛,丝绸之路建立了中外艺术交流的纽带,艺术作品的风格特点是气魄宏大,笔势流动,既粗犷豪放,又细密瑰丽。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事频繁,民不聊生,佛教成为大众精神寄托的载体,文人崇尚飘逸通脱、与世无争,因此艺术注重人心内在精神世界的表达,强大画面的意蕴之美。再如,宋代的绘画崇尚自然与理性,既有平淡至简的追求,又有“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责任感。即使近代中国虽有内忧外患,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尚存,一批艺术家如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吴昌硕、傅抱石、潘天寿、刘海粟、任颐、林风眠、潘振镛、何香凝、石鲁、陆俨少、黄胄、丰子恺、叶恭绰等依然把中国艺术推向了世界的高峰,从近年来海外竞拍的作品价格和艺术作品的创作年代不难看出,全球拍卖行对于这一时期中国艺术作品的关注度明显增加。
纵观当下中国艺术作品的现状,不难看出,85美术思潮中黄永砯、王广义、徐冰、舒群、毛旭辉等艺术家的作品,和之后的张晓刚《天安门系列》、刘晓东《三峡移民系列》、方力钧的《光头人物系列》、岳敏君的《我爱大笑》等中国当代艺术黄金一代的代表,以及移居海外的艺术家如蔡国强《烟花系列》、谷文达《碑林—唐诗后著》、陈丹青的《西藏组画》、艾未未的《行为艺术》等作品,充分表现了美术创作所体现的时代精神,他们的作品能够被标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代表性作品,不仅仅取决于画面的完整和表现方法的独特,最关键是成功地把握了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语境,能够在特定的时间点充分表現中华民族即将崛起和焕发新生机的思想观念。画面语言既具有现实主义的情感,同时又掷地有声地凸显了社会矛盾和问题,因此在那个特定的时期,这些作品就像一针强心剂让正处于徘徊和观望的人们仿佛听到了一种来自于艺术家内心深处的告白。随后当代艺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开始以融入和创新的方式呈现出异彩纷呈的时代特征。中国艺术家王广义、张培力、耿建翌、徐冰、张晓刚、蔡国强、艾未未、马六明、方力钧、萧昱、徐震、高氏兄弟等相继参与了威尼斯双年展(1993年45届到2001年49届),比如,45届展览中,方力钧的具有标志性、符号化的“光头”系列首次亮相,传达了独立艺术家追求思想解放的热情,体现了80年代后期新启蒙思想的感召下塑造更加具有时代感、文化感的形象,是后来中国“顽世现实主义”的标志作品。再如46届展览中张晓刚的“血缘:大家庭”系列,虽然从创作手法上看具有模式化的“装饰感”,但确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团圆”和“合一”的文化精神所在。正如张晓刚所说,这些旧照片有种特殊的视觉沉淀,从中我们能捕捉到那个时代中国家庭对于社会的感受与情怀,这些作品纪念那个时代的关于家庭的记忆。这些优秀作品让来自中国本土的“中国艺术”在国际舞台绽放新姿,也充分展示了具有中国情怀的艺术魅力,这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创新的方式,更主要的是一种良好艺术精神品质的体现。
但当下,受市场经济和物质利益等因素影响,美术创作的功利化倾向日趋明显,从近几届美展和优秀的代表作品看,很多作品的创作更趋向于材料、效果的制作,甚至一味求大、求精细而介入喷墨、打印以及数码特效,把作品的二次复制当成追求的方向,画面缺少能够传达时代气息和弘扬时代精神的文化意蕴。不少美展的后续反馈,对作品的整体评价质疑颇多。总的来说,是没有全面反映出中国当下绘画主流精神和创作技巧的时代性。过于强调围绕画面形式性的处理,缺少对于中国当代社会所产生的社会性因素和民众问题的持续关注。艺术家个体没有形成有利于艺术精神的创作动机,要么频繁流于商业炒作,创作满足市场的低级行画,要么为了参展而刻意迎合主办方的创作主题,忽略了美术创作的本质精神以及对人类共同理想的追求。因此,有效提升中国当代艺术的精神性,用“文化自信”凸显具有中国特征的文化价值和艺术精神,是增强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的前提和保障。
指摘之二:中国当代美术创作的功利性性倾向。
中国美术家协会从1949年建立开始,为推动美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美术精品的诞生、美术人才的培养、美术活动的开展,全国各级美术家协会功不可没。其体制化的设定与管理方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积极推进中国艺术群体的职业化发展的同时,难免会出现一些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应的现象,一些问题的凸显,也成为中国美协各级领导极力进行改革和改良的关键所在。比如,对于部分美术创作环境渗透的行政化管理成为艺术家过分追求功利的手段,严重制约了中国艺术家精进自我提升艺术水准的能力,令艺术作品缺少独特深刻的内涵,令艺术家缺失艺术探索的时代精神。再如,有些地方把衡量艺术家优秀与否的标准赋予具有行政化干预的评价标准上。从代表艺术专业的行政群体划分模式上不难看出,这是层级制的管理体系,从上一级美协到下属各级美协的建立成为管理艺术工作的专门机构,一些艺术协会的领导成为了当代优秀艺术家的代表,专业赛制的评比、专家组成员的机构建立习惯以协会中特定官职、官员为中心,形成了固态化模式。一些地方美协的主席团成员数量与年俱增,部分省市的主席、副主席人员设置庞大,少则十几人,多则二十几人,建立了既密集又具有垄断性的关系网络。
部分美协机构中一些任职的官员以及美协会员作品润格从每平尺三五万到近百万不等,成为炙手可热的“抢手货”,因此能否进入协会甚至成为官员是很多艺术家毕生孜孜不倦、经营自我的目标。追求艺术后面的功利成为艺术家创作的主流思想,试想当年梵高、高更、徐渭、唐伯虎、郑板桥、黄秋园都是生前落魄的艺术家,但对于艺术的追求一生不变。我们不能说艺术家就一定要活得穷困潦倒,但是不尊重美术创作本质的艺术家,把艺术当作生财之道,流于形式的行为是一种带有“矛盾”式的创作动机,当社会舆论在声讨范增作品如印刷机一样高效复制的生产行为的时候,我们必须分析,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当代优秀作品是什么。
多年来,行业协会会员评定的宗旨是对优秀艺术家成就的肯定,而绝非敲开财富之门的金钥匙,从现在的一些社会现象看,国内很多展览对于指定级别的协会会员提供了特权待遇,比如相关会员免初审、比如只有相关会员可以进入某某拍卖行列,比如相关会员拥有优先参与相应等级展览的特权行为。有部分展览以商业为目的,仅限相应等级的会员参与,虽然没有明确注明非会员不得参加,但实际操作过程中这种倾向比较明显。长此以往,国内艺术品评的标准就默许为以会员资格为代表的评审模式,是会员的作品就是优秀作品,非会员作品很难进入官方展览。在美协会员申请中近年来也新增了必须逐级申报会员的不成文规定,降低了各级协会对于申报会员的透明度,增加了各级美协官员行政干预权力。拼搏多年成为美协会员的艺术家,大多数考虑的是如何进行有效的商业运作、包装自我,提高作品市场价值,以迎合市场需要而进行创作行为,因为奔波于此,使不断提高、精进自我的艺术精神追求缺失,画功停滞、画风单一俗套,难以产生真正的艺术精品。
指摘之三:中国当代美术创作评审机制的局限性。
多年来,国内专业美术赛事均由具有较高学术造诣和专业水准的专家担任评审专家,秉持公平、公正的评审原则,评选出不少达到很高艺术成就的美术佳作。但是,也不能不看到,一些具体评审方面的设置和方式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中国当代美术作品的评选方式,还主要是通过传统的参展入选后获奖来界定,很多赛事的评审过程和方式较为模糊,缺乏评审的细化标准体系,评选标准多从宏观及程式化的角度进行说明和界定,对优秀作品仅仅以名单的形式在网站上公布,缺少较为有效和完善的大众评赏平台,展览的全部参赛作品以及获奖作品不能及时在公众平台上展示,后期也缺乏较全面的关于获奖作品、落选作品的情况说明和较为科学和专业化的评点环节,使很多展览仅仅停留在基础性的传统奖项评审的框架中,缺乏后期深层次跟进式的创作交流和学术探讨,不能较为及时地发现和解决中国当下美术创作中所产生的相关问题,难以持续保证优秀美术作品的产生。
美术展览是美术创作工作者提升自我,发挥其艺术价值的重要途径之一,美术展览也成为评定艺术家作品优秀与否的重要平台,各级美术协会的入会标准也是以参加同等赛事的获奖情况、次数为参照比重,因此参与美术展览对国内艺术家来说意义非凡。但从国内的展览评审程序和评审原则看,许多展览还是习惯以美协各级官员所组成的评审委员会作为终审机构,甚至出现一票否定、暗箱操作、走人情风、贿评等违反竞赛原则的事实情况。从历届美展看,国画、油画等大画种的选送程序还是实行逐级申报、限额申报的传统方式,很多优秀的作品难以在公众范围内展出,在地区的选拔中就被淘汰,被体制化、人情化的因素所埋没,没有体现竞赛原则上的公平、公正、透明。例如,全国第十二届美术展览,很多专业人士就公然批评作品创作的低劣、手法单一、制作成分过强、老面孔居多等。如中央美院教授薛永年看过展览后建议要下大力气继承古代和近代的优良传统,“多年以来我们并不忽视创新,也不忽视横向比较,但是比较处理不好创新和继承的关系、处理不好横向与纵向与传统的关系,因此作品往往更重視视觉而不是心理,往往重视视觉新颖而不是文化厚度。”[4]
评审方式的局限性之外,其监督机制也有不够完善之处。国内每年举办的各级展览为数众多,以中国美术家协会举办展览为例,2018年具有美协入会资格的大展就有50多次,从一定程度上确实展示和汇集了当代艺术家优秀的创作作品,但从某种程度上看,也不乏带有目的性、投机性的创作行为,从近几年的美协网站公布的投诉事件分析看,很大一部分都集中在作品出现雷同、抄袭、一稿多投、代笔、照片侵权绘画等问题上。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说:“近年来,许多美术院校的年轻学子,手机拍照成了习惯,很多人不会画速写,不会画创作的小构图和变体稿。由于这种浮光掠影的学习态度,不难想象其创作作品在感情上的苍白。”[5]
值得注意的是,常有这样的现象:同时在各级展览中出现同一作者,同一作品又在参加同一年度具有入会资格的展览中分别入选,这不难说明目前国内对于美术作品的创作监督机制不够完善。2016年中国美术家协会启动了排重系统,对类似事件进行了有效遏制,虽然在美协的条例中对于相关人员有一定的约束,但社会影响力不够,很多人依然故伎重演,没有达到真正的惩戒效果。从最近叶永青事件看,不管结果如何,对于艺术作品“抄袭”的认定在国内并没有详细规定,也没有具体的鉴别机构,都充分说明了国内目前对于艺术作品的创作规范和监督机制均存在问题,需要通过更为科学的方式进行有效的完善。
综上所述,在大众审美品位提升的今天,如何有效发挥美术创作对于社会精神层面的积极作用,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就美术创作环境发展来说,常常是涉及到多个侧面、层面、环节同步参与、整体联动,以使艺术家在充分的生活体验中形成良好的创作素养,为时代创作优秀的作品。中国当代美术创作的未来发展,可以说机会颇多,但也任重道远,只有把握住美术作品创作中所体现的丰富性、典型性和真实性的基本原则,完善评审机制,建立良好的创作环境,才能有效提升艺术家创作作品内在精神与社会价值。
注释:
[1][英]伯恩斯·皮卡德:《历史哲学:从启蒙到后现代性》,张羽佳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4页。
[2]费大为:《中央美院师生关于全国美展座谈会纪要》,《美术思潮》,1985年第1期。
[3]陈绶祥:《新文人画艺术——文心万象》,吉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4]冯智军:《全国美展,不仅是一场美术盛会》,《中国文化报》,2014年12月22日。
[5]蒋跃:《有必要再强调一下生活——对第十二届全国美展的冷思考》,《美术》,2015年第3期。
(责任编辑 胡海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