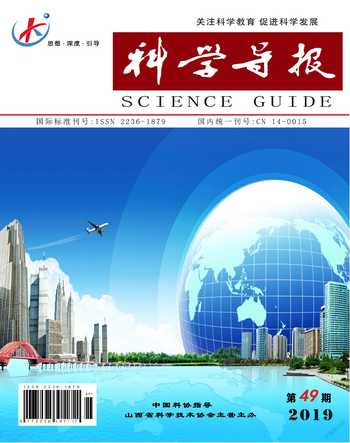抵抗到接纳:以“恨”为主导的情感抗争下的“黑粉文化”
杨蕊青
在当前互联网时代的媒介生态中,粉丝文化以其声势浩大的“线上线下”群体互动与千姿百态的消费行为,成为了大众文化研究中一个备受关注的议题。而与之相对应的“黑粉”文化近几年伴随着粉丝文化的发展,也逐渐走向公众视野。两个情感完全对立的群体,在以恨为主导的情感抗争中,也在不断发生改变:从抗争走向接纳。
关键词:粉丝文化;情感抗争;怨恨
一、“黑粉”及国内“黑粉”文化的发展
西方关于粉丝文化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关于“粉丝”一词的定义国内外尚未有明确的概念界定,一般指热衷于某个人物或某件事情,并为此愿意付出大量时间或金钱的人。“黑粉”则是与“粉丝”相对立,指厌恶、憎恨某位明星或者公众人物,會在网络上开展一系列言语攻击行为、编撰且散播明星负面信息、制造明星负面表情等一系列图文生产的粉丝群体,“黑粉”又称“ANTI”粉,最早由娱乐产品输出大国韩国制造传播开来,意思是反对某些特定艺人、公众人物的群体,“Anti 粉”不仅对特定的对象存在情感上的厌恶,他们会对明星进行一系列的言语上的攻击,甚至在线下展开一系列极端的攻击人身行为。
与国外“ANTI”粉不同的是,中国的“黑粉”很少在线下开展极端的人身攻击、威胁等行为,他们多在互联网上开展有规模、有组织的攻击行为,给被攻击者带来很大的精神困扰行为。这种攻击不仅仅针对明星偶像,还针对有影响力的个体粉丝,有时还表现为粉丝群体之间的群攻。几乎每个人气高的明星的微博留言区都能看到黑粉对明星的攻击。这种攻击还常常引发粉丝之间的“战争”。而中国“黑粉文化”的发展史,也是紧跟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进行的,随着媒介娱乐化程度越来越高,“黑粉”文化也逐渐愈演愈烈。
国内最开始是小部分群体在贴吧、论坛等社交平台对厌恶的明星进行恶搞和攻击,在这个阶段,最典型的黑粉群体是李宇春的“黑粉”,他们称李宇春为“春哥”,并衍生出了“信春哥,得永生”、“信春哥、不挂科”等流行语,将李宇春的头像置换在史泰龙身上,制造了一系列恶搞的表情包,当粉丝群体与其在互联网上产生对抗时,他们会开展“爆吧”等群体性行为。此时,由于互联网发展的有限性,“黑粉”仅存在粉丝圈层的对抗面,并未真正走向大众。
伴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黑粉”群体也进入快速发展期,其中最著名的代表是蔡依林的黑粉以及他们创造的“淋文化”。2003年蔡依林发布新专辑《看我72变》,其中造型及曲风涉及抄袭日本艺人滨崎步,因此认定蔡依林抄袭的日本流行音乐爱好者成为了蔡依林的第一批黑粉,到2009年,蔡依林发布新专辑《花蝴蝶》,其封面造型让黑粉对其的反感愈深,也是从这时候起,蔡依林不被称为蔡依林,而是“淋淋”,黑粉也拥有了自己的称呼——“本质骑士”,随之以后他们创造了一系列恶搞表情到讽刺文本,他们称之为“淋语”,百度贴吧也有了一大批专门用来恶搞蔡依林的主题贴吧,除了原有的日音粉丝以外,一大批欧美粉丝也加入到这个群体进行传播,关于蔡依林的恶搞全面爆发,从粉丝圈层走向了大众,淋语中的“惹”、“噜”、“厚”和表情包在网络上被大量运用,成为了一种文化奇观。
2015年,黄子韬宣布退出韩国男团EXO,由于他曾在微博上发表长篇文章指责其前队友吴亦凡退团,他这一行为引起大量粉丝的不满,这群粉丝快速通过新媒体技术在微博等平台集合起来,他们称自己为“法骑”,名称的来源为黄子韬在退团时将微博头像改为一支香烟上面写着fuck来表示对部分粉丝指责他的行为的不满,法骑自我定位为一个有爱的团体,坚持只搬运黄子韬的黑历史,绝不信口造谣,主要发布与黄子韬相关的图文。正是由于法骑对黄子韬坚持不懈旷日持久的攻击和抹黑,许多并不认识和关注黄子韬的路人网友开始认识黄子韬,并加入到抹黑黄子韬的行列里,让黑黄子韬成为当时最流行的网络文化,甚至连黄子韬本人也开始使用自己的“黑称”,并宣告自己不会轻易的“狗带”,此时,“黑粉”文化作为粉丝文化中的一个独特分支正式被公众和明星本人接受,这种文化且越演越烈,每位流量明星都有其“黑粉”群体,并有之具体的相对应的语言体系,甚至在这个阶段“黑粉”之于明星,从最开始的完全对立面,发展到如今的推手,帮助他们获取流量,吸引公众的注意力。
二、以“恨”为主导的两类情感抗争
乔纳森·H·特纳强调“情感在所有层面上,从面对面的人际交往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特纳、戴维斯,2007)。情感区分了粉丝与“黑粉”,这两类人在关注明星文本的情感数量上是不相上下的,但在能量的意愿上却是完全相背离的,“黑粉”在抗争中,形成了以“怨恨”为主导的情感构成。
在“黑粉”的情感抗争行动中,“恨”成为了主导情感,而这种“恨”主要分成三种类型:一种是互联网空间中,部落群与部落群之间的碰撞,碰撞让各个群体间不断摸索彼此的底线,二者之间不平等的对抗关系使得极端情况极易出现;二是粉丝本人与明星自身的认知落差以及造成的意义情感断裂;第三种则是明星及其团队塑造的形象与其本人本质上形成巨大的认知反差,这种反差让怨恨者自身产生不平等的失落与无能感。
(一)对抗形式下的“恨”
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媒介文化娱乐功能也越发突出。粉丝可以通过互联网技术快速集结,形成声势浩大的规模,开展一系列的群体性行为。而在一定的互联网空间中,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对抗,一方的过分强势造成关系的不平等,开始出现差异化情感,两者之间的身份关系开始划分界限,当互动不断进行时,这种差异化情感愈演愈烈,不平等感越来越强,进而开始变成“恨”。其中最著名的事件是“虎扑直男大战吴亦凡粉丝”。事情的导火线是有虎扑网友放出吴亦凡消音的rap视频,这一举动引发吴亦凡粉丝的不满,在粉群的意见领袖号召之下,召集了大批粉丝去虎扑举报黑帖,并试图在虎扑开展“反黑”行动。这一强势的粉丝行为瞬间引发了大量虎扑用户的不满,@虎扑步行街 在微博称反黑召集「真是牛逼坏了」。下午,吴亦凡直接在微博宣称我的音乐不用给你们这帮人听,吴亦凡工作室发表声明称视频是恶意处理,要追究法律责任,此时反感情绪瞬间走向高潮,虎扑用户群体感受到自身的利益及领地被侵犯,一时间他们创造了大量的表情包、黑话,并将吴亦凡的表演视频进行二次创作,带有戏谑的内容一时间迅速传播开来。
(二)情感意义的断裂
第二种类型的“恨”主要是指一种反转型的粉丝行为,即“脱饭回踩”。脱饭回踩是在特定事件的刺激下,粉丝从情感到行为产生 180 度转变的反转型行为。劳伦斯·克罗斯伯格曾指出:“粉丝对于某些实践与文本的投入使得他们能够对自己的情感生活获得某种程度的支配权,这又进一步使他们对新的意义形式、快感及身份进行情感投入以应对新的痛苦、悲观主义、挫败感、异化、恐惧及厌倦。”他还认为是情感指引着粉丝们构建出属于自己的要义地图(Mattering Maps),它构建了对粉丝们而言具有重要意義的事物。而“爱”与“恨”仿佛硬币的两面,具有想对立性,当粉丝的情感链断裂,一旦偶像出现与粉丝心中形象稍有出入的行为,特别是当偶像行为触犯粉丝利益时,粉丝就会产生强烈的被欺骗感和背叛感,从而由“爱”转向“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2017年鹿晗在微博宣布公开恋情,一时间该微博发布两小时后即获得46万多的转发量,浏览热度一度导致新浪微博服务器崩溃,其后,实时大批鹿晗粉丝在微博宣布“脱粉”,#鹿晗掉粉# 话题占据微博热搜。接着,社交网站上开始出现以“前粉丝”身份,内容涉及鹿晗人品、私生活等多方面的攻击言论。造成这种“脱饭回踩”的原因是在过去粉丝与偶像本人的关系构建中,由“爱”这种情感连接的从属关系让粉丝形成了自我的身份构建,一旦象征意义因为媒介事件发生断裂,过去的自我身份构建发生改变,情感关系破裂,心理迅速形成一种落差,凝结成满腔的埋怨和愤恨。
(三)认知反差造成的不满
明星及其公关团队为了打造明星都会为明星塑造一定的“人设”,即明星形象。但往往在一些事件中会造成形象的崩塌。“黑粉”通过自身的认知和经验进行价值判断,发现与其营造的大相径庭之后,会因为被欺骗的“不公平”造成失落进而引发“恨”这种情绪。例如蔡依林的“黑粉”多为日本流行音乐爱好者和欧美音乐流行爱好者,因为蔡依林塑造的“努力”人设与其大量抄袭的现实相违背,因此表现出厌恶的情绪。
三、从抵抗到认同,“黑粉”文化同时走向大众化
技术的发展赋予了每个使用者传播和创造文化的机会,原本仅属于两个对立层面的对抗行为被媒介技术迅速带入到大众的视野中去,移动互联的是即时性和交互性让大众同时有机会随时生产出大量的文化成果,随时都有机会成为下一个热点,公众表达欲不断提升,大量文化成果不断涌现导致原有的意义被稀释,原本的文本意义内涵再一次被丰富,“黑粉”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不仅仅只是一味的贬低和虚无发愤慨,增添了很多温和的意义,“恨”的情感抗争被冲淡,当粉丝群体开始接受被丰富的文化内涵意义时,他们会减少抗争行为,处在相对立的情感面的另一边的“黑粉”群体当不平等感减弱时,自然会减少、消除其“恨”的情感意义,双方也就会从抗争走向接纳。典型的例子是最开始被认作是带有侮辱性、讽刺性的“淋语”被蔡依林本人所使用,同时一大批明星本人开始使用自己的所谓的“黑粉”表情包,代表着明星本人在享受着粉丝众星捧月的态度的同时,也开始接纳“黑粉”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林东东.新媒介时代粉丝的文本盗猎与生产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8,25(04):73-77.
[2] 傅琳雅.观看—参与—表演:数字媒介技术驱动下粉丝文化权力的结构性演变[J].广告大观(理论版),2018(05):41-47.
[3] 李建伟,王怡冉.脱饭回踩:一种反转型粉丝行为研究[J].新闻爱好者,2018(09):13-17.
[4] 李博文,经晓彤.媒介构建下粉丝文化的新变化[J].视听,2018(09):14-15.
[5] 郑钦云.被忽视的“Anti粉”文化现象解读——以微博平台中的“Anti粉”为例[J].新闻研究导刊,2018,9(12):62-63.
[6] 张樾.我国粉丝文化现状探究[J].新闻研究导刊,2018,9(11):93.
[7] 胡岑岑.网络社区、狂热消费与免费劳动——近期粉丝文化研究的趋势[J].中国青年研究,2018(06):5-12+77.
[8] 毛天怡. 从群众到粉丝[D].上海师范大学,2018.
[9] 杨晓庆. 网络行动中的情感化抗争研究[D].安徽大学,2018.
[10] 洪培琳.冲突视角下的粉丝文化现象分析——浅谈粉丝微博骂战频发症候[J].现代营销(下旬刊),2018(01):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