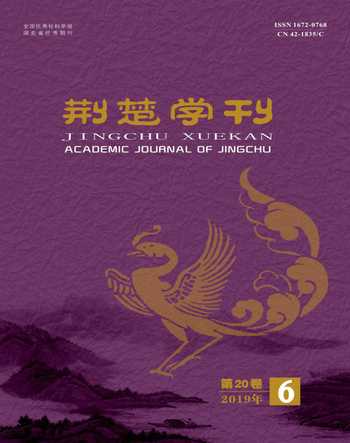试论清华简《系年》的书写背景及其特点
罗姝鸥
摘要:清华简《系年》以粗线条式的书写,兼顾了叙事的完整性与时间的顺承性。它于历史关节处着额外之墨,既表现出楚国乃《系年》叙事之主线,又反映出作者敏锐的历史洞察力。它的存在,表明了先秦历史书写的多样性,丰富了我们对先秦史籍面貌的认识。
关键词:清华简;《系年》;先秦;书写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768(2019)06-0005-05
清华简《系年》全篇138支简,包括合文与重文一共3875字。“原篇无题,因篇中多有纪年,文字体例与若干内容又近似西晋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故拟题为《系年》”[1]135。全篇分为23章,记录了从武王克殷一直到战国早期三晋伐楚的历史。《系年》的出现,对先秦史学、文学、文献学等相关领域及其研究来说,无疑是具有重大价值的。本文将结合学界相关研究成果,讨论《系年》的性质、写作特点等相关问题。
一、多样的先秦历史书写
对于《系年》的体例,学界已有了一些看法,大略有三种:一部分学者认为其为编年体,如清华简《系年》整理者认为《系年》的“文字体例与若干内容又近似西晋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1]135,另外李学勤先生也认为《系年》“是一种编年体的史书”[2],但“《系年》完全不是《春秋》那样的编年史”(不是“标准的编年史”)[3]。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其为纪事本末体,如许兆昌、齐丹丹认为《系年》“已经具备了纪事本末体的基本特征”[4]。还有一部分学者则试图在这两种体例之外寻求一些新的思路,如刘全志认为《系年》既不是编年体,也不是纪事本末体,更不是《左传》的摘编,他推测其性质可能与失传的汲冢竹书中的三篇“国语”相近[5];而李守奎则以为《系年》“全篇既不是单纯的纪事本末体,更不是编年体,而是有整体布局,通过叙事和剪裁,表达著者的历史观[6]。
为何会产生这样的分歧呢?这就与《系年》的书写特点有关。《系年》全篇囊括了从武王克殷到战国早期三晋伐楚这一段历史,大略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而就具体事件而言,其发生、经过及结果也都得到了或简或详的叙写。所以,学界才出现了“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的争论。支持“纪事本末体”观点的学者,往往会以《系年》并未“编年相次”等特点为由而否定其具有“编年体”的性质;而反对“纪事本末体”观点的学者,又往往会以《系年》记事未能“详叙其始终”为由而否定其具有“纪事本末体”的性质(1)。试图跳出这两种体例的学者,或者证据不足,或者未能展开说明,也未能有个定论。可以看出,关于《系年》的性质问题,还有大家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其实,在判断《系年》属于哪种体例之前,是否该先辨析清楚写作特点与体例、概念之间的区别呢?就拿“编年体”来说,逐年记事是其写作特点,但除此之外,作为一种成熟了的体例,它还具备一些其他的特点。而当体例成熟进而形成规范性的体例概念以后,包括逐年记事在内的所有的特点综合起来,才能称之为“编年体”,而脱离其他而只具备其中某一写作特点的史作,并不能称之为“编年体”。同理可知,“纪事本末体”亦然。这也是上文所提到的支持“编年体”观点或“纪事本末体”观点的学者遭人质疑的原因所在。
就一般规律而言,体例的固定及体例的概念是后于写作方式的出现而出现的。所以,要谈《系年》的性质,就不能拿后来的体例概念去框套,而应回到《系年》所产生的先秦背景中去理解其性质。然而,秦一统之后,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至司马迁之时,“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8]606,先秦史书已不多见,传世的则更少。不过,我们仍能从汉代史书记载中找到一些痕迹。我们从《史记》的自述及前人的论述中可以知晓司马迁所见之史籍书目,据班彪《略论》推测,司马迁所据材料有《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及陆贾《楚汉春秋》。而除此之外,就《史记》文中自述所取材者中,史类文献也还有《秦记》(《十二诸侯年表》:“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8]606),及《谍记》(《三代世表》:“余读《谍记》……稽其历谱。”[8]606梁启超及金德建以为《谍记》有可能就是《世本》(2))。筛选一下,可以看出,司马迁参考的先秦史籍主要有《左传》《国语》《世本》(《谍记》)、《战国策》《秦记》等。其中,《世本》(《谍记》)、《秦记》已失传。但从《史记》的自述中,大略可知两书形式,前者为谱谍体式,后者为不标年月略叙史实的记事体。虽然传世的《左传》《国语》《战国策》经过刘向、刘歆父子的编辑及后人的整理,其原貌已不好判断,但就已知的《史记》所参考的五部先秦史书而言,其体式已经相当丰富。有编年的,有不编年的,有记言为主的,有记事为主的,也有略记史实的,还有谱谍式的……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秦火及岁月长流的阻隔,先秦史书的面貌应当是相当丰富而精彩的。
《系年》的出现,其实就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先秦历史书写的多样性。所以,我们与其用后世固定化、单一化了的概念去框套《系年》的性质,不如就《系年》的实际情况去丰富我们对先秦史记书写的认识。
二、兼顾叙事的完整与时序的顺承
清华简《系年》全篇138支简,简背皆有排序编号(“有一处误记,后又加以纠正,计编号至137號,最末一支简无编号”),排序不成问题。全篇分为23个段落(整理者依此分章),每个段落完结之后,该简就此留白,新的段落都是重新由另一简开始书写,不存在两章文字同在一简的情况;而且,每个段落结束之处,几乎都有清晰的墨勾或墨横(3)。这些特别之处正可以说明,《系年》23个段落的顺序编排是有意为之。
从《系年》全篇布局来看,23个章节,前四章“所说的重点也是在于周王室何以衰落,若干诸侯国怎样代兴,这表明《系年》的作者志在为读者提供了解当前时事的历史背景,也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7];后面五到二十三章,为《系年》内容之主体,以楚、晋两国记事为主,涵盖秦、齐、吴、越、郑、宋、蔡、息、陈、卫等国,叙述了春秋至战国早期诸侯征战、分合的全过程。从这样的布局可见,《系年》的作者是有统一谋篇的意识的,关于这方面已有学者进行了论述(4)。我们认为,《系年》的作者不仅有统一谋篇的意识,还试图在内容的组织与书写中合编年与叙事之两宜。就《系年》的内容而言,的确是偏重于叙事的完整性的。但在叙事的同时,我们又可以看出《系年》作者在叙事时间编排上的匠心独具。这也就是为何我们能在《系年》叙事中看到“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影子的原因。
一方面,在23章内容的组织和具体章节叙事的书写中,《系年》虽然没有逐年相次记事,但从武王克殷到三晋伐齐,基本上是按时间先后顺序安排的。然而,在具体的叙述中,作者又会为了叙述的完整性而进行时间编序上的调整。有的学者指出《系年》第20章开篇纪年跳回“晋景公立十又五年”(5),不合前后章节的时间顺序,其实,这正是《系年》作者在平衡时间与叙事的匠心所在。第20章叙述的是吴、越相继与晋“为好”的过程。内容前后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叙述的是晋与吴“为好”,而以“勾践灭吴”为转折,后半部分叙述的是越继吴与晋“为好”。其前半部分从“晋景公立十又五年”开始记述,显然是为了理清晋、吴“为好”之开端(“申公屈巫自晋适吴,焉始通吴晋之路,二帮为好”)和发展过程。这方面正好体现了《系年》作者叙事方面注重叙事完整性的特点。除去开篇追根溯源,第20章随后写到晋吴伐楚,在时间上就已经承接上了第19章,而后叙及勾践灭吴、晋越为好、晋(赵)越伐齐等事迹,又合上了第21章的时间。另外,第20章吴楚内容的安排,显然是继第19章楚昭王围蔡、蔡归于吴而来,而第19章楚昭王围蔡与第20章开篇之申公巫通晋吴之路显然又与前面第15章相应。其实,若严格地按照时间顺序的话,第15章其实也存在着类似第20章的问题。第15章主要叙述吴人受“申公屈巫”及“五员”影响叛离楚进而伐楚的过程,时间跨度较大。也因此其开篇时间略早于第14章,结尾时间却远远晚于第16章,而合于第19章。而这大时间跨度内的吴楚两国之外的诸侯之事,就按时间顺序被安排在了第16至18章(6)。第15章及第20章的这种安排,显然是为了具体事件的叙事完整性而对整体性时间顺序进行了调整。从这一点来说,《系年》的确也有些后世所谓的“纪事本末体”的影子。
另一方面,进入《系年》具体章节的叙述之中时,文中常用具体纪年或王位、爵位的更迭以提示事件发生的前后顺序。如第2章“(郑)武公即世,庄公即位;庄公即世,昭公即位……”,第7章“晋文公立四年……”,第八章“晋文公立七年……”,第20章“晋景公立十又五年……悼公立十又二年……晋敬公立十又一年……晋幽公立四年……”。这也是为何《系年》会被有些学者认为是“编年体”的原因。但正如我们上文所分析的,具有编年体的某些写作特征并不代表就是编年体,这方面已经有学者具体批驳。但需要注意的是,否认《系年》为编年体性质,并不是否认《系年》含有编年体的某些写作特点。《系年》叙事对时间顺序的重视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系年》虽有纪元,却显得混杂不一。其实,《竹书纪年》也存在混用纪元的情况,但其用纪元的原则却是相对统一的,即平王东迁以前用王的世系纪元,东迁以后用晋国纪元,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元。而《系年》23章中,前四章用的是周之纪元,五章以后则是晋、楚纪元交迭更替。总体上看起来大体是用晋纪元的时候讲的是与晋相关的事(如第6至10章及14、17、20等章节),而用楚纪元的时候講的是与楚相关之事(第13章残损不算的话,有第11、12、15、16、19、21、23等章节)。但也存在例外,如第18章与第22章。
第18章主要讲述了晋楚第二次弭兵之盟至晋内乱七年致诸侯反晋之间的事。在这一章内,同时用了晋、楚两国纪元,也同时用了两国国君之更替以推进叙述时间。而讲述晋楚第一次弭兵之盟事件的第16章,其中用的却只有楚纪元。两相比较,这其中的差异是否为《系年》作者有意为之?亦或是有别的原因?面对单一的例子,我们很难作出判断。然而幸运的是,《系年》第22章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相关联的线索。第22章主要讲述的是战国早期三晋伐齐之事,用的却是楚国纪元。而就其具体内容而言,除了开篇用到楚之纪元之外,全章内容都与楚无关。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存在。第22章的存在,显然排除了《系年》作者有意以某国纪元写某国之事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系年》总体上看起来记某国事即用某国纪年并非作者有意为之,而是由别的原因所致。那到底是何种原因所致呢?当我们将第18章与第22章的特殊情况纳入整个《系年》纪元系统中综合考察后,发现《系年》纪元之混用,很大的可能性是受其所用材料的影响。
在上古时期,整合几个文本形成一个新的文本的情况是非常常见的。有的学者将这种整合过后产生的新文本称为“衍生型文本”(7)。《战国策》便是刘向整合几个文本所形成的新文本(8),《系年》的情况或许与此类似。作为一部历史著作,《系年》的内容不可能凭空捏造。而当《系年》作者面对来源不一的各种材料时,其筛选、整合、再创作都必定遵循一定的规律,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系年》大体以晋纪元写晋事,以楚纪元写楚事。而无论再努力,作者整合编辑前人材料时,或多或少都会留下的一些不协调的痕迹,这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第18章与第22章。《系年》的存在再次让我们看到了早期文本生成的复杂性。
综而观之,在对全文格局的把握上,《系年》作者在平衡叙事的完整与时序的顺承之间作出了有效的努力。而在具体叙述中,则大体上交迭使用晋、楚纪元,晋事用晋时,楚事用楚时。这些都不得不说是《系年》作者谋篇布局之匠心所在。
三、额外着墨于历史转关之处
《系年》的叙述,多以粗线条的记叙为主。正因为这个特点,可能会让人怀疑它是否类似于《铎氏微》等史书,是依据《左传》摘编而成。这样的看法已经有学者予以反驳。正如反驳者所言,《铎氏微》等几种“春秋”微的存在与流传,本身就证明了战国一直承续着依据史书进行再创作的风气,《系年》也是这种社会风气的产物(9)。
需要说明的是,整合编辑前人材料并非单纯的复制,即使不著新言,单纯是材料的重新组合排列,其中也必然蕴含着作者用意,是一种再创造活动。何况《系年》虽说以“大事记”类似的粗线条记叙为主,但也存在不少细化的描写。如第14章所叙“晋驹之克受辱伐齐”事件,其文如下:
晋景公立八年,随会率师,会诸侯于断道,公命驹之克先聘于齐,且召高之固曰:“今春其会诸侯,子其与临之。”齐顷公使其女子自房中观驹之克,驹之克将受齐侯币,女子笑于房中,驹之克降堂而誓曰:“所不复訽于齐,毋能涉白水。”乃先归,须诸侯于断道。高之固至莆池,乃逃归。齐三嬖大夫南郭子、蔡子、晏子率师以会于断道。既会诸侯,驹之克乃执南郭子、蔡子、晏子以归。齐顷公围鲁,鲁臧孙许适晋求援。驹之克率师救鲁,败齐师于靡笄。齐人为成,以甗骼、玉筲与錞于之田。明岁,齐顷公朝于晋景公,驹之克走援齐侯之带,献之景公,曰:“齐侯之来也,老夫之力也。”[1]167
作者以简洁的笔调书写了“晋驹之克受辱伐齐”事件。其中如“驹之克将受齐侯币,女子笑于房中”,几笔便将齐顷公之失礼与驹之克受辱的场景声情并茂地勾勒了出来。驹之克指白水为誓以及结尾处提着齐侯的腰带牵以献之景公的场景,将驹之克士可杀不可辱之气节及有仇必报之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结尾那一句“齐侯之来也,老夫之力也”,驹之克得意之形跃然纸上,清晰可见。类似的书写还有第5章楚文王抢息妫,第9章晋灵公之立,第15章申公屈巫争少孔(10)等几处。这些细化的情节描写尽管相比《左传》来说,还显得太过粗糙,但对比《系年》全文粗线条式的记叙,这几处细化的情节描写已经显得足够特别。
将这几处情节放于历史长河中去看,可以发现:通过息妫之争,楚文王将楚国势力向北扩张;晋灵公继位风波,加剧了晋秦之间的怨恨,巩固了秦与楚联合对晋的态势;驹之克受辱,使得晋、齐关系破裂;申公屈巫争少孔而背楚投晋,通晋吴之路,致使了吴叛楚投晋,甚至导致了此后百年吴越相继与晋为好而抵制楚的态势。可以看出,《系年》作者所着墨重点描写的几件事,都发生于楚国霸业道路的几个关键节点之上,很难说这几处描写不是作者有意为之。于历史事件发展中所加入的这些细节、场景以及语言描写,与其说是塑造人物的需要,不如说是《系年》作者叙述历史的需要。这几处着墨点的选择,不仅反映出《系年》作者对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深刻认识及对历史走向的清晰判断,还反映出《系年》作者的叙事是有所偏重的——几处浓墨重彩的描写,都与楚国相关,都处于楚国争霸的关键之处。似乎可以说,楚国才是《系年》作者叙事的重点。
再结合前文中所提到的《系年》纪元问题来看。晋楚两次弭兵之盟,相比第18章的晋楚纪元混用,第16章独以楚纪元记事;而第22章三晋伐齐,与楚无关却依旧独以楚纪元记事。我们是否可以揣测,在众多资料之中,楚国的记事材料在《系年》作者面前更具优先性?在没有更多材料支持的情况下,这或许只是一个大胆的推测。但综合上文所提及的《系年》作者每每于楚国争霸关键之处着浓重之墨的情况来看,这种推测也并非全无道理。
总而言之,《系年》以粗线条式的书写,兼顾了叙事的完整性与时间的顺承性。虽然这样的写作方式在其书写中还不够成熟与完善,但其意义却是重大的。它于历史关节处着额外之墨,既表现出楚国乃《系年》叙事之主线,又反映出作者敏锐的历史洞察力。它的存在,表明了先秦历史书写的多样性,丰富了我们对先秦史籍面貌的认识。
注释:
(1) 前者如许兆昌、齐丹丹等学者,后者如刘全志等学者。
(2) 梁启超在论及《史记》“所据之原料”时提及“(三)《谍记》(或即《世本》)”,详见《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19页;金德建从此说,其考察司马迁所见典籍时,于《谍记》下按语云:“《谍记》乃总名,包括五帝三代历谱……《谍记》即《世本》。”详见其专著《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9页。
(3) 23段中有20個段落结尾有墨勾。
(4) 许兆昌、齐丹丹详细分析了《系年》的“统一谋篇之布局”,但他们将《系年》章节划分为1、2至5、6至23三部分,与我们的观点略有出入。
(5) 许兆昌、齐丹丹《试论清华简〈系年〉的编纂特点》:“而《系年》中,却出现了并不按照时代顺序排列章序的现象。如第14 章标明为晋景公八年,第17、18 章为晋平公元年及十二年,第20 章又转回晋景公十一年。由于《系年》各简均在简背标明简号,因此,这种年代错序应是简文的本来现象,不应是整理者的误断。显然,这种时间顺序上的错乱,也不是编年体史著所应有的。于此亦可知《系年》虽记有年代,但绝无编年叙事的意图。”这种观点显然没有理解《系年》作者布局之用心。另外,许文中说“第20 章又转回晋景公十一年”误,应为晋景公十五年。
(6) 换算成公元年来说的话,第20章时间跨度大约为:前585年(申公巫通晋吴)-前472年左右(赵越伐齐);而第15章大约为(前599-前505),第19章大约为(前507-前478左右),第21章大约为(前422-前421)。
(7) 关于“衍生型文本”的说法,由程苏东提出,其在《激活“衍生型文本”的文学性》(《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7月25日,第5版),《时空的文本与失语的文学批评——以〈史记〉及其研究史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等论文中对此有所界定及运用。
(8) 刘向《战国策·叙录》曰:“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
(9) 刘全志《论清华简〈系年〉的性质》细致比较了《系年》与《左传》记述的内容,从《系年》比《左传》多的部分、两者不合部分、及《系年》记载错误部分等几方面证明了《系年》非《左传》之摘编。但值得注意的是,刘全志虽然排除了《系年》摘编《左传》的可能,但并不代表它不可能摘编自其它史书。不过,笔者也并不认为《系年》为某类史书的摘编,但参考某类史书,或者说在某类史书基础上进行再创作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10) “少孔”之“孔”当写为“上孔下皿”。
参考文献:
[1] 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二)[M].上海:中西书局,2011.
[2] 李学勤.初识清华简 [N].光明日报,2008-12-01(12).
[3] 李学勤.由清华简《系年》论《纪年》的体例 [J].深圳大学学报,2012(2):42-43.
[4] 许兆昌,齐丹丹.试论清华简《系年》的编纂特点[J].古代文明,2012(2):60-66.
[5] 刘全志.论清华简《系年》的性质[J].中原文物,2013(6):43-50.
[6] 李守奎.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N].光明日报,2015-12-10(16).
[7] 李学勤.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J].文物,2011(3):70-74.
[8] 司马迁.史记[M].裴马因,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荣,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11.
[责任编辑:黄康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