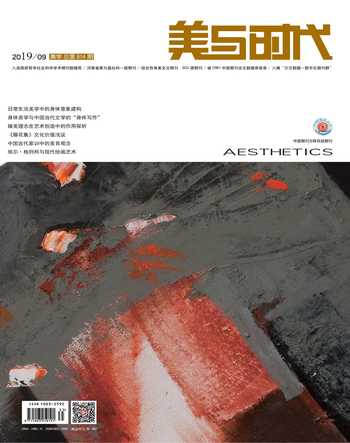粤音与葡韵迭影的美学交融:再现澳门土生葡人女作家江道莲小说《长衫》
摘 要:话剧《长衫词》尝试揉合广府传统曲艺南音与葡萄牙怨曲法朵(Fado),将澳门土生葡人女作家江道莲的小说《长衫》以说唱为技艺,并用现代戏剧的方式演绎而成。《长衫词》重新还原20世纪40年代澳门妇女对命运使然、无奈的生存形态,并展示了澳门本地多元文化共融、共生的社会特性。
关键词:江道莲;土生葡人;澳门;小说;戏剧
澳门本地表演团体——足迹Step Out与区均祥粤剧曲艺社合作“演书节”的小剧场《长衫词》,改编自土生葡人女作家江道莲的短篇小说集《长衫》(又译作《旗袍》)。《長衫词》揉合广东传统音乐南音、葡萄牙法朵(Fado),并运用剧场艺术进行重新演绎,超出了文学作品背后的隐喻、语意和讯息。制作单位跟“演书节”的初衷一致:“每一个作品的背后、每一个作品的创作过程,甚至起点,事实上都有一些参与文本在当中起着启发性的、蓝本的角色,以至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中没有绝对的‘原创’,一切都源自‘改写’此一事实。”[1]《长衫词》创作蓝本来自于小说集《长衫》,剧中女主角的原型及故事情节取自《长衫》里众多独立故事,如《长衫》〈《告别》《内心的冲突》《阿慧的绣花鞋》《翡翠戒指》,其中以《长衫》作为主轴。
一、江道莲及其小说集《长衫》
短篇小说集《长衫》于1956年在葡萄牙里斯本出版,作者江道莲是中葡混血,从小接受葡萄牙式教育。“二战”期间,她于香港担任葡文报纸《澳门之声》翻译BBC电台电讯稿的工作。回澳后,她加入《澳门新闻报》当记者,并从事编辑工作,成为澳门第一位女记者。
首篇小说《长衫》以战争前后作为背景,讲述年轻中国女子张玉的悲惨命运。张玉的父亲经营酒铺,她自幼在不愁衣食的家庭里成长;十五岁那年,父亲安排她与邻近米铺东主的长子阿春订婚。订婚后,张玉决定到欧洲求学两年,短暂的求学生涯使得她由以往胆怯害羞、缺乏主见的少女变成气质优雅、自信独立的新时代女性。相比之下,阿春的学识只局限于读报,迂腐懦弱,传统男尊女卑的观念根深柢固,这就为后续的悲惨结局埋下了伏笔。
婚后,张玉极力塑造自己成为一个贤妻良母的角色,甘于成为阿春背后的女人,生儿育女,过着所谓幸福美满的日子。随着战事的爆发,阿春不得不变卖家产,带着张玉和儿女逃到南方避难。处身战争年代,夫妻俩的钱财已花光耗尽,一家之主的阿春从未有出外打工以赚取微薄工资的念头。可此时张玉的内心却经历多番挣扎,认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与命运抗争。她决定为了家庭进行自我牺牲,取出当年结婚时所穿着的百花图案的黑色丝绸长衫到舞厅陪阔佬跳舞,以娇柔的身躯来换取全家的三餐温饱。而失去男性尊严的阿春,终日无所事事,情绪变得暴躁,经常发脾气甚至拿孩子们出气。一次偶然机会,张玉在舞厅里结识了一位西洋阔佬,为了摆脱舞女的屈辱生涯和孩子们日后的安稳生活,毅然答应阔佬到外地旅游。出发前,她向阿春保证三日后会回来,出发后却沉醉于轻松愉悦之中,不觉已离家一星期。某日清晨她起来看到报纸上阿春的寻人启事,敦促她火速回家。张玉心急如焚,忘记带钱,忘记带上送给孩子们的礼物,跑到码头乘搭最早的一趟船赶回家。到家之后才发现阿春欺骗了她,从而使她原本想多陪客人几天,挣一大笔钱摆脱贫穷的计划功亏一篑,于是夫妻俩激烈争吵起来。阿春恼羞成怒,手拿厨刀,狠狠地向妻子砍下去,美丽的张玉倒毙于血泊之中……
二、话剧《长衫词》的符号隐喻
话剧《长衫词》如何对原著小说进行改编的呢?该剧由说唱演员何志峰、黎若岚及戏剧演员梁建婷演绎。开场序幕,戏剧演员梁建婷饰演的“她”软瘫在白色的长枱上,仿如说唱演员黎若岚手中的扯线木偶,举手投足都被机械式地牵扯着。就连说简短的话语,都故意拖拉成两三节,而当“她”学习Português(葡萄牙语“雇主”)一词时,重复了三次才读出正确的发音,仿佛在质疑自己的身份,究竟自己是葡萄牙人还是中国人?牵涉到身份认同的问题在过去的土生文学作品乃至戏剧演出都会受到诸多关注。
说唱演员黎若岚形容女主角拥有一双大眼睛、高挺的鼻子,正是因为她是一位土生混血儿。改编后的《长衫词》将原著里的张玉设定为中葡混血儿,并从头到尾没有交待过“她”的名字。小说中的张玉是父母的掌上明珠,而剧中的“她”自小与父亲隔离,跟母亲住在小屋,而父亲却住在山上的大宅,缺乏正常家庭本应有的父爱关怀。可见她母亲与父亲之间是不受任何合法婚姻的保护,只因母亲的低下华籍身份,被排挤在家族之外,而她则被视为是玷污了家族血源、让族群传统蒙羞的罪恶,“她”的身份亦不会受到土生葡人族群中父权社会的认可。
贾渊、陆凌梭在《起源问题:澳门土生的家庭与族群性》一文里指出了当时葡人家庭对中葡混血儿的接受情况:“认同华人族群的人论调一般都是谴责性的。这归咎于六十年代华人备受歧视期间所遗下来的耻辱印记。持这种论调的人坚持说只有社会的最低阶层女性(如妓女)才会与葡人结合产下土生葡人。据相反论调的是土生葡人中最有地位的那一群,所谓古老的名门望族。与这些家庭有密切关系的葡裔人士亦抱相同论调。”[2]
回到话剧《长衫词》里的“她”,由于身份未得到父亲的认可,从来没有人会为她庆祝生日。直至她十七岁生日时,父亲送她一件长衫作为生日礼物,这件黑底碎花图案长衫让她爱不释手,珍而重之。为了配合这身长衫的打扮,她穿上黑色高跟鞋,对自己美丽的容貌与姣好的身材打量一番。长衫的设计符合女性的身段,剪裁把腰身和袖口收窄,凸现东方女性娇柔的曲线身型,长衫标志着她的女性身体发育成熟,开始从少女迈入女人。她脚下的那双黑色高跟鞋,则是她苦难之路的开端。黑色高跟鞋不仅是她成为女人的象征,也预示着她不自觉地被命运操纵,逃不出当时传统女性的悲惨宿命。跟剧场“序幕”的安排一样,女性的生命从出生到死亡都不由自己掌握,如同扯线木偶般任意随父权主导下的家庭、社会所操控,后续的剧情发展不出意料地如想象般的悲剧被演绎出来。
正值青春年华的“她”,对爱情的美好产生无限憧憬,愉悦地享受着情郎为她折取的一枝桂花,把它戴在头上。转眼间却得了重病,口里不断念着《金缕衣》诗句:“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技。”表面上是慨叹青春短暂,及时抓住时机。实际却远不止如此,她为何会生病呢?“折桂”原有夺冠登科之意,得了重病的“她”,是否预示着这段姻缘是错配呢?似乎命运不会让她配上一个如意郎君,偏故意安排她终身误托。
三、从女性主义看戏剧《长衫词》里的“她”
“她”不顾父亲的反对,毅然嫁给了自己深爱的男人。结婚后,“她”才惊觉自己遇人不淑,拆穿了丈夫的虚伪面具,经历怀孕生育的痛苦,直到丈夫经营生意失败、染上酗酒赌博毒瘾,变卖所有值钱的家当,也无法改变全家人生活遁入困窘的状况,唯一“最值钱”的只有结婚时所穿着的长衫。最难以启齿的是,丈夫强迫“她”卖淫为娼,穿上那件丁点残旧看起来还算体面的长衫接待不同的嫖客。这时,长衫被悬挂在白色长枱上方,而饰演“她”的戏剧演员梁建婷仅透过双臂穿过长衫袖口,运用双手在身体上下交叉移动,暗示“她”与众多客人身体接触,脸容虽被长衫遮盖,却遮掩不住长衫底下“她”内心的痛苦和绝望。
需要厘清的是,小说《长衫》中张玉与阿春的缔结是“父母之命”包办的“门当户对”的婚姻,后来因战祸导致家财散尽。阿春无所事事,为了养家糊口,张玉只得承担起家庭重任,委身于舞厅陪客人跳舞。此处可看到她为了孩子,“为母则强”的女性原始本能,抛弃父权社会里世俗眼光对女性不公平的评价,勇敢地和命运对抗。而话剧《长衫词》中的“她”和丈夫的结合是建立在恋爱的基础上,“她”对丈夫的爱是盲目的,丈夫染上毒瘾,仍然对他不离不弃。甚至丈夫强迫“她”卖身为娼,亦不见“她”反抗,默默地接受丈夫的无理、粗暴的要求,最终失去人应有的尊严。而且丈夫只要伸张手,“她”便自动奉上金钱,一味地纵容、妥协、让步,最终导致夫妻关系失衡的恶果。
直到生命将要结束之时,“她”才鼓起勇气对丈夫做出最后的控诉,原来温柔、服从的贤妻形象不见了,亦是因“她”对爱情彻底绝望了!“她”痛恨丈夫,恨他亲手摧毁了自己期待建立美好家庭的愿望。原本丈夫应该是家庭的经济支柱,主掌家里的决策大权,支配整个家庭的规矩,体现出传统父权制度下男性应有的话语权,妻子和儿女必须顺从他的指示和吩咐:“社会历史文化由话语构成,人们处于话语与权力相互交织的网络中,一方面受权力的支配,另一方面又执行权力……因此,谁拥有话语权力,其主体的建构就越明显、越具有优势,在权力关系中越占据有的地位,而这也会反过来巩固权力。”[3]这就是“话语即权力”,谁能掌握话语的力量就意味着拥有权力。
传统妇女被排斥在社会参与领域之外,受制于封建规条,压制她们的生存空间,最主要原因是她们“没有说话的能力”。而一旦妻子成为家庭的经济来源,丈夫沦为成家庭的附属成员,“性别角色意识形态决定了谁在家中工作、谁在家中照顾孩子与家庭”[4],陷入经济上依赖女性的处境,传统的夫妻性别角色出现倒置,这就为最后的悲剧结局埋下隐患。
四、法朵与南音演绎悲怆命运
上天曾过给“她”机会,好让“她”能够从不幸的命运中挣脱出来。客人邀请她到香港旅游,而且可以轻易挣到一笔钱,解决家里现时的苦境,“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虽然“她”也知道这趟旅程只能是暂时填补心灵上的缺位,但在“她”亲手为自己戴上红色小礼帽登船时,想要离开丈夫与儿女的冲动还是从心底油然而生。“她”决然地离开丈夫,到了陌生的城市,看似是脱胎换骨般变得从容、愉快,此时剧场播放着法朵(Fado)哀怨色调的“Medo”(译作“恐惧”),伴随着“她”的轻型舞姿,露出久未展现的笑靥:Quem dorme à noite comigo(晚上谁与我共眠)/? meu segredo(那是我的秘密)/Mas se insistirem, lhes digo(如果你坚持追问,我会告诉你的)/O medo mora comigo(恐惧与我一起生活)/Mas só o medo, mas só o medo(惟有恐惧,惟有恐惧)
这首怨曲不正切合“她”此时内心真实的写照吗?欢场上形形色色的男女在情欲里纠缠不清,笑面迎人待客,又有几人会真心地爱“她”呢?而“她”一直以为跟丈夫的婚姻建立在真爱的基础上,但事实上,每当“她”只身孤影深夜归家,面对的只有粗暴无情的丈夫,恐惧俨然是“她”日常生活的写照。睡在身边的人是丈夫还是客人,似乎早已不再重要。
说唱演员何志峰、黎若岚就座于剧场东、西两端,由于黎若岚的土生葡人身份,很自然就能联想到她是原著小说的作者江道莲的化身,她的角色不止于说唱,还介入剧场与另一戏剧演员梁建婷进行互动。说唱演员何志峰以第三者身份演绎,从旁观者的角度交待剧情的来龙去脉,引领观众感受到女主角身上所表达的无法挣脱的宿命观。他以凄切呢喃的声线说唱《长衫词》哀哀戚戚的曲词:“花露凝点恨水长东,想起缪莲往事,理屈词穷。”唱词中的“缪莲”者是谁?南音经典名曲《客途秋恨》提道:“小生缪姓莲仙字,为忆多情妓女麦氏秋娟。见渠声色性情人赞羡,更兼才貌的确两相全。今日天隔一方难见面,是以孤舟沉寂晚景凉天。你睇斜阳照住个对双飞燕,独倚蓬窗思悄然。”显然是借用书生缪莲仙的典故来暗讽“她”所托非人的爱情悲剧,最后被自己深爱的男人亲手杀害,不得始终,有屈难诉,难道她不会“理屈词穷”吗?
反观书生缪莲仙与妓女麦秋娟即使天各一方,却常忆起往日的旧情绵绵。昔日,南音曲词结合粤语生动通俗的词汇、古典诗词的馥郁雅趣,最能传绎粤珠三角一带居民的独特语言风貌的原生态歌谣。作为怨曲的南音,唱词大多借书生与妓女的爱情作隐喻,折射出人性共有的无助困境及飘泊心绪。法朵是葡萄牙的传统怨曲,以悲恸的曲调与歌词,如海上飘泊的水手对未知前途的迷茫,诉说人类对宿命的无力抗争。南音和法朵同属怨曲,且皆以命运作为歌咏主题,回顾小说《长衫》的成书年代,正值20世纪40年代的“二战”期间,作者江道莲亲眼目睹了当时澳门遭战争蹂躏的惨况,邻近地区的难民涌入小城,生命如同蝼蚁。话剧《长衫词》藉由南音和法朵交织而成的哀怨曲调,粤声与葡韵的揉合,再现澳门传统女性的命运悲歌,以及澳门本地多元文化的共融、共生的社会特性。
参考文献:
[1]卢颂宁、莫兆忠.从“演书节”思考阅读与演释[C]//语言:2015澳门剧场研讨会文集,2015:66.
[2]贾渊、陆凌梭.起源问题:澳门土生的家庭与族群性[J].RC文化杂志,1993(4):19—34.
[3]刘剑雯.性别与话语权—女性主義小说的翻译[M].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6:45.
[4]Pamela Abbott, Claire Wallace,Melissa Tyler.女性主义社会学[M].郑玉菁,译.台北:巨流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8:161.
作者简介:余思亮,博士,澳门科技大学国际学院助理教授。研究方向:文艺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