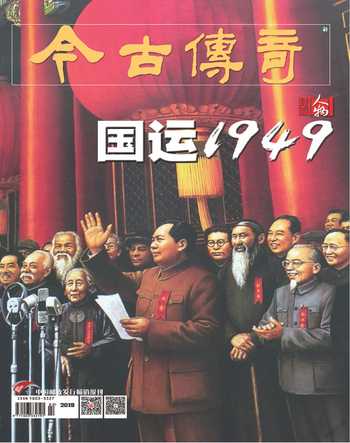蒋氏父子曲折的传位之路
李思达


整肃外戚,摆平功臣
从1949年6月到1950年3月,蒋经国整日随侍在
蒋介石身边。等到彻底撤到台湾之后,有些嗅觉灵敏的人已经看出,蒋介石已经坚定地要交班给蒋经国
1977年,蒋介石已去世两年,蒋经国完成了最后的布局,等着名正言顺地继位。而在此之前,他们都做了什么?
“经儿可教,纬儿可爱”
1909年夏,一名算命先生铁口直断,说蒋介石第一个太太毛福梅生下的儿子必将贵不可言时,只有蒋介石母亲王太夫人相信。她带着毛福梅前往上海,直到怀孕之后才返回奉化。
10个月后,正在日本的蒋介石得到家乡母亲传来的口信,他的长子蒋经国于1910年4月27日诞生,母子平安。此外,王太夫人還有一个奇怪的要求——在族谱上将蒋经国登记为蒋瑞青(蒋介石幼弟,4岁时夭折)的儿子。对于母亲的这个要求,蒋介石一口答应,不过这个要求也给蒋氏父子带来了一些小麻烦:后世有人因蒋氏族谱和奉化县档案记录而产生流言,称蒋经国不是蒋介石的亲生儿子。
蒋经国10岁之前,蒋介石都对他表现出一种冷淡的态度。当然,这也不能完全怪他。在当时的革命风气下,人人都希望和家乡的一些旧事务决裂,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风潮中。而当时的蒋介石也正在外地参加革命,直到1920年蒋介石返乡省亲之前,蒋经国都没怎么见过父亲,一直在祖母和母亲的照顾下成长。从此时起,蒋介石似乎才恍然大悟这是自己唯一的亲骨肉,开始重视对蒋经国的教育。差不多在这个时候,他的日记中第一次出现了对自己孩子的记载:“经儿可教,纬儿可爱。”(同年,他领养了4岁的蒋纬国。)
从此时蒋介石给蒋经国的信件和他的日记来看,蒋介石只是按照当时通行的传统方法来教育他,开蒙是用四书以及其他古文,为此还专门延请了当地的两位硕儒顾清廉和王欧声。不过,见过世面的蒋介石已经意识到传统教育的不足,在蒋经国12岁时将其带到上海接受教育。那时,父子二人之间的教育互动就十分频繁:蒋介石把自己读过批注的书寄给儿子,要其好好揣摩,还要求蒋经国将自己的去函保存下来,有空就取出来温习——不过因为他常常忙得没空写信,所以可供蒋经国揣摩的信件很少。
1925年,15岁的蒋经国被送到吴稚晖创办的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上学。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国共合作气氛的感染下,他很自然而然和左翼学生打得火热,不仅认识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众多共产党员,还定期去苏联大使馆看电影,和使馆人员经常见面。如果按蒋氏父子的教育模式来看的话,蒋经国此时的思想动向应该是一一向父亲汇报过,然而蒋介石对蒋经国的左倾倾向似乎毫不在意。
不久后,蒋经国向吴稚晖提出申请,要求推荐他去莫斯科,当吴稚晖询问他为什么要去国外的时候,蒋经国意气风发地回答:“为了革命!”吴稚晖哈哈大笑,告诉蒋经国:“革命就是造反,难道你不害怕吗?”随即让他回去再考虑一下。两周之后,坚定的蒋经国再次向吴稚晖表示决心去莫斯科,吴稚晖这次没有再阻拦,只是说:“去试试也好,年轻人多尝试一次也是好的。”
为了此事,蒋经国还专程去了一趟黄埔,先是找到“上海姆妈”陈洁如,在她帮助下取得了蒋介石的同意。不管是为了获得苏联支持,还是认同联俄容共,总之此时国民党内都不认为送子女去苏联是什么危险的事情——蒋经国的行李,就是以后反共最积极的陈果夫给准备的。1925年10月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我再次提示经国。我决定允许他到苏联进修。”
政治人物的两面:苏维埃培养出来的人才
从1925年到1937年,蒋经国都是在苏联度过的。从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到列宁格勒的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从列宁格勒又到莫斯科迪纳摩电厂和郊外的集体农庄;然后又被送到乌拉尔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在1933年左右还被发配到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极有可能就是古拉格,在那里呆了9个月才又回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一家大型机械厂担任主管,还和当地的一名女工菲伊娜·伊巴杰夫娜·瓦赫列娃相恋结婚;直到1937年4月19日才回到中国。
在很多有关蒋经国政治思想的研究中,人们都会注意到他以后在赣南和台湾所实行的许多政策都深受苏联影响,颇具共产党色彩,甚至就连当时国民党内部也有人讥讽从苏联回来的蒋经国就是一名共党分子。的确,这12年正是蒋经国人生观和政治观形成的重要时期,这段苏联经历给他的思想和作风留下了深刻烙印。他在施政中重视下层民众,勤于了解底层民间疾苦,和他这段颠沛流离的苏联经历不无关系。然而,蒋经国在苏联学到的,绝不仅仅是亲民。
当蒋经国到达莫斯科时,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对决还没有结束,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共产国际“托派”气氛浓厚,率队迎接蒋经国到来的,就是当时“托派”干将之一、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而年轻气盛的蒋经国则顺理成章地投入了“托派”的怀抱。他是如此活跃,甚至让许多人认为他就是中山大学中“托派”的组织者。但到了1927年蒋经国临近毕业时,共产国际派代表和他谈话,认为他可以进入军事学院进修,但条件是必须放弃“托派”思想。大约在4月底,他突然放弃托洛茨基运动,成了中山大学中第一批退出“托派”的学生之一。事实证明,这次“退托”非常及时,因为到了1928年1月,托洛茨基和拉狄克就被分别发配到中亚和西伯利亚,米夫奉命在中山大学“肃托”,凡是没有退出“托派”的中国学生悉数被捕,大多数命丧异域。
这是蒋经国第一次在政治上玩出180度大回转。事实上,以蒋经国的敏感身份,和参加过“托派”的前科,他在苏联却能平安地度过血雨腥风的二三十年代,还在大肃反高潮的1936年12月14日差点儿加入苏共,这件事情本身就非常说明问题。他的恩师拉狄克和图哈切夫斯基,还有他认识的各级地方干部,不是被流放就是被枪毙,但蒋经国却在日记和回忆录中对这些朋友和老师的经历只字不提,仿佛什么都未曾发生,继续默默地工作、上进,争取入党,这些都或许从另一面透露出他性格中惊人的冷静。不仅如此,在苏联时,他在政治上的谨慎成熟就已经让人为之咋舌:1928年初,中山大学一些人写信给正在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的蒋经国,提议成立一个江浙同学会,由他担任会长。这一举动很快就被苏联政治保卫部门侦查到,却始终找不到蒋经国参与其中的证据。但实际上,蒋经国一直暗中花费心思交好一些来自江浙的同学。据他的同学严灵峰后来回忆,当时蒋经国为了接济江浙同学,甚至卖掉了自己的收音机。由此可见蒋经国心机之深沉,做事滴水不漏。
在蒋经国处事风格之中,有着令人费解的矛盾性:他能深入民间,注重底层,促进民主,表现出和蔼亲民的一面;但在另一面,当手握大权之时,他也能不动声色地杀得血流成河,制造白色恐怖。无论是亲民和蔼促进民主,还是手腕狠辣排除异己,蒋经国都能在两种模式中随心所欲地转换,都毫无心理障碍。这恐怕来自他在苏联的训练,正是这种政治手腕,让他日后稳打稳扎,一步一个脚印地斗倒诸多实力和资历雄厚的大佬,顺利继位。
“打虎”失败的教训:唯有儿子真可信赖
随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展开,蒋经国顺理成章地于1937年4月19日返回中国。值得一提的是,陪伴他长途跋涉从莫斯科穿越西伯利亚抵达海参崴的,正是后来的中共重要人物康生,两人在离开海参崴之前还联名给莫斯科发电报称:“现在,党派我回国……请转告共产国际执委会,我会恪遵党纪……”
其实蒋经国已经志不在此,他更在意的是和父亲重逢是否会顺利。出于种种理由,他在苏联曾经发表过和父亲决裂的公开信,虽然后来他推诿自己是被逼的,但是由于白纸黑字印刷在《真理报》上被蒋介石看到,还是让他非常尴尬,在和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讨论回国细节的时候,他还曾担心地问道:“你认为我父亲希望我回国吗?”
蒋介石当然希望他回国。他曾在日记中多次表示“我深盼儿子能回来”“先母在天之灵一定欣慰经国归来”。不久后,两人在杭州的国民政府主席别馆中会面,在这次会面中,蒋介石让蒋经国先在溪口老家读书:书目一如12年前,还是《曾文正公家书》《论语》《孟子》和王阳明文集。
虽然父子间已经冰释前嫌,但此时的蒋经国还远远谈不上接班人。眼下的他在山头林立的国民党内只是一个既无资历也无军队的小角色。只有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认识到“奇货可居”,向蒋介石提议让蒋经国以保安处少将副处长的名义赴江西,随后又任命他为赣南第四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自此,蒋经国算是拥有了一块自己的地盘,正式走上仕途。
作为自己事业的起点,蒋经国在赣南雄心勃勃,号称要把“赣南建设成为人人幸福的乐园”,“成为三民主义模范区”,做到“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人人有工做”。不过,他在赣南做出的成绩正如其传记作者江南(刘宜良)所说:“热闹有余,成事不足,禁禁烟赌,抓抓土匪强盗,尽可放手大干,且容易看见成绩。一旦动摇到国民党的根本,注定非败阵不可。”
事实也是如此,当1948年局势逐渐恶化,为了挽救经济崩溃的命运,蒋经国受命去上海“打虎”,当他正洋洋得意地将自己的赣南经验搬到上海时,却没有料到十里洋场完全不能和江西的山村相提并论。当“打虎”打到了孔祥熙的大公子孔令侃身上时,孔令侃求救于宋美龄,而宋美龄找到正在北平督战的蒋介石,逼他下令让蒋经国放人,使得局面一发不可收拾。
“打虎”失败给予蒋经国极大的刺激,有一段时间他的情绪极为糟糕,一度陷入绝望,每日借酒浇愁,常常喝得酩酊大醉,时而大哭时而大笑。受到刺激的不仅仅是蒋经國,还有蒋介石。在这种刺激之下,蒋介石第一次产生了就连妻家外戚都靠不住,在给自己拆台,唯有亲生儿子才是真心为自己的念头。恐怕也就是此时,他坚定决心:要将自己的江山交给蒋经国。
蒋介石为儿子铺路
从1949年6月到1950年3月,蒋经国一直处于赋闲状态,在仕途上陷入了停顿。这9个月里,他能做的只是整日随侍在蒋介石身边,陪伴他度过最难熬的一年。然而,正是这种时时刻刻的陪伴,让父子俩的感情和默契日益加深,也正是这段时间父亲每日的耳提面命,让蒋经国在政治上日趋成熟和圆滑,摆脱了赣南和上海时期的鲁莽。等到彻底撤到台湾之后,虽然没有任何明显的征兆,但有些嗅觉灵敏的人已经看出,蒋介石已经坚定地要交班给蒋经国。
退守到台湾岛后,蒋介石进行了一次全方位重新整合。对蒋氏父子来说,此次整顿是一次深刻的反省和浴火重生,更是一个为子承父业铺平道路的天赐良机。尤其是败退台湾之后,昔日政军界诸多大佬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地盘和军队,使得蒋氏父子可以从容布局,控制整个岛内的局势。
首先被蒋氏父子盯上的,就是在大陆时呼风唤雨的孔、宋、陈三家。对这三家“皇亲国戚”的弄权舞弊,蒋介石一直都有所了解,只是在来台之前,他面临的党内外敌人尚多,不得不对孔、宋、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换取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的鼎力支持。但退到台湾之后,岛内已是蒋氏“清一色”,无论是经济还是“外交”都不需要再借助他人,所以早就成为众矢之的的孔、宋、陈三家就成为绝好的杀鸡儆猴对象。
最先出局的是四处树敌的CC系二陈(陈立夫、陈果夫)。退台之后,蒋介石一边号称要改造党务,一边又不给CC系控制的“中央党部”好脸色看,只要是“中央党部”送来的文件,他一律不看不批原件退回。陈立夫被逼得没有办法,试探着提出要为大陆失败负党务方面的责任,不再参加以后的改造工作,而蒋介石听了他的表态之后一言不发,让陈立夫心里顿时凉了半截,知道从此出局。事后宋美龄去看望他,劝其皈依上帝寻找精神寄托,而陈立夫指了指挂在墙上的蒋介石照片,意志消沉地说道:“这个活着的上帝都不相信我。信上帝又有什么用呢?”事实上这个“活着的上帝”不仅不相信他,甚至还对他恨之入骨,转头就令他在24小时内出境,让他再也不能在台湾政坛上兴风作浪。
此时的宋美龄全然不知道蒋氏父子的三把火就要烧到她家人身上。1952年7月,国民党“七大”召开之后不久,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唐纵以“中央党部第一组”的名义向“总统府”提交报告,称以孔祥熙和宋子文为首的13名“第六届中央委员”在海外未归队,建议直接撤销党籍。宋美龄知道此事后大为愤怒,认为是蒋经国在背后捣鬼,更联系起上海的往事,闹个没完,最终迫使蒋介石让步。
虽然在这一回合的斗争中,宋美龄事实上保留了两人的党籍,但却在政治上陷入了更大的被动。对她来说,孔、宋家人的确是她的至亲和精神上的寄托,但以当时台湾的政治气氛,在人人都在知耻后勇,痛改前非之时,她依然还像在南京时那样要包庇自己的亲人,激起了不少人的反感。后来蒋介石的秘书周宏涛在回忆此事时,还表达了恨自己当时势单力薄,无法帮蒋氏父子撤销孔、宋等人的党籍之意。从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当时蒋氏父子和宋美龄之间微妙的关系。
由于蒋氏父子把住了“吸取教训”这个道德制高点,所以蒋经国越是坚持原则,越是对宋美龄的不智之举进行抵制,就越获得舆论的好评,也更能反衬出宋美龄的无理取闹。其实从头到尾,宋美龄在政治上就没有对蒋经国的地位构成过威胁。在南京的时候,蒋介石还需要她拉拢美国,大搞“夫人外交”。但到了台湾,地缘政治的现实已经迫使美国不得不确保台湾,蒋氏父子已不需要“夫人外交”就能维持良好的双边关系,也就更不担心宋美龄的挑战了。实际上,蒋经国对待宋美龄更像对待一个名贵的花瓶,在公开场合总是小心翼翼地关爱备至,礼貌尊敬,实际上根本没给过她任何掌权机会。
由情治到军队,蒋经国掌权之路
虽然在台湾蒋介石已经能排除其他所有山头和派系,建立起蒋氏父子的强势威权体制,但要想真正实现传位,还是得一步一个脚印地来。而蒋介石最先传给蒋经国的,就是维护威权体制最重要的机构:情治机构。
撤台之后,蒋介石曾经想过让毛人凤将保密局交给蒋经国,而让毛人凤改任副职辅佐他上马。但一生精明的毛人凤居然在此事上犯了一个大糊涂。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美国深深介入台海局势,使得毛人凤判断以前长期负责对美外交的宋美龄地位会水涨船高,甚至有可能在蒋介石百年之后上位,因此走上了夫人路线,拒不肯将情治机构移交给蒋经国。对毛人凤这种莫名其妙的自信,就连他的老部下叶翔之也觉得不可理喻,劝他好好和蒋经国合作,但毛人凤却充耳不闻。
1950年3月,蒋介石连下三道手令,一是派蒋经国重建军队政治机关;二是派俞鸿钧负责设计台湾财政经济秩序;三是任命“台湾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缉为“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当时的彭孟缉只是一个中将,在将星云集的台湾算是级别较低的。但是蒋介石坚持要用他来领导所有的情报机关,用心无非有二:一是利用彭孟缉地头蛇的优势去力压毛人凤等人;二是故意让低级别的彭孟缉来担任毛人凤的上级,打击其气焰。彭孟缉也不辱使命,为了完成蒋介石交代的任务,在台湾演出了一招“杯酒释兵权”的好戏。
为了打开局面,彭孟缉在“保安司令部”里面找到了戴笠的学生——熟知情治部门内情的郑绍远,在他的帮助下,以“保安司令”的名义宴请当时所有“中央情报单位”的副主管。酒过三巡之后,彭孟缉突然拿出蒋介石的手令,要求统一“情报系统”,并且提出所有机关的谍报工作人员,必须持有“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颁发的证件才能“合法”办案,并请在座诸副主管加入“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由于事发突然,又有蒋介石手令,副主管们只能纷纷签字成为“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委员,成了彭孟缉的直接下属,随后又把在自己单位情报工作人员的资料统统交给了彭孟缉——从而让“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事实上架空了以前的情报机构。随后,彭孟缉识趣地请辞,将整个情治机构拱手让给蒋经国,而毛人凤则被挂起,不久之后就病死了。
其实,真正对蒋经国继位造成阻碍的,还是代蒋介石掌控台湾,官拜“副总统”的陈诚。自撤台以来,陈诚一直主持台湾实际政务,尤其是实施土改在民间获得了极高的威望,另一方面,无论是在“三民主义青年团”,还是“青年军”时代,陈诚都是蒋经国的上司。无论是从功劳还是资历来说,蒋氏父子都无法轻易绕过陈诚。最终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出马,压住陈诚,力保蒋经国继位。
1957年国民党“九大”之时,陈诚在党内已是副总裁,而蒋经国只是中央常委委员。无论从资历还是政绩来看,蒋经国都急需时间弥补。但此时最缺的就是时间,因为按“宪法”条款,于1948年开始当选“总统”的蒋介石,到1960年已任满两届,理论上应该退职。而以当时的形势,蒋经国无论怎么刷政绩都赶不上陈诚,除非“修宪”让蒋介石连任,保持现有体制让蒋经国继续积攒实力。
对于陈诚有接班的可能性,蒋介石思前想后,最终使出了一招耍无赖来解决:他用修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方式,让自己可以无限连任,让陈诚的梦想化为泡影。同时也明白无误地告诉所有人,蒋氏小朝廷要玩父子传位的游戏了。经此之后,连任“副总统”的陈诚心灰意冷,于1963年12月辞去了長期担任的“行政院长”一职。面对此时资历尚不足直接接任的蒋经国,蒋介石又精心安排了一步妙招——选择没有派系也没有根基的技术官僚严家淦作为过渡人物。而严家淦知恩图报,一上台便让蒋经国以“行政院政务委员”的身份兼任“国防部副部长”。“国防部部长”是蒋经国的儿女亲家俞大维,军队实权自然是落在蒋经国手中。被夹在中间的陈诚此后一直心情郁郁,于1965年3月5日病逝。
对于陈诚的逝世,蒋介石又喜又悲,葬礼极尽哀荣。悲是因为陈诚作为他最亲信的部下,长期忠心不二;喜则是因为陈诚的去世彻底解决了蒋经国的继位问题,岛内再也没有任何障碍可以阻止蒋经国继位。1969年,严家淦任命蒋经国为“行政院副院长”,事实上将所有行政大权拱手交给了蒋经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