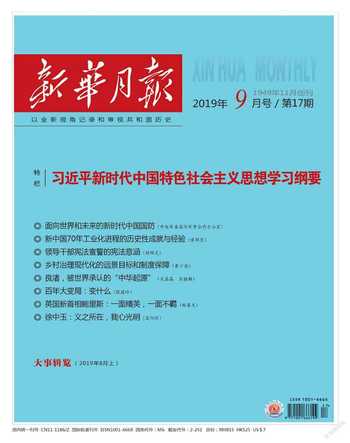人类阅读之谜
薛巍


在大约5000年前,古代的苏美尔人、中国人和南美人发明了文字,自那开始的1000年间,阅读能力推动了人类的智力和文化的发展,极大地扩展了人类学习、创造、探索和记录我们的思考、感受和知识的能力。阅读就像是给我们的大脑提供了一个外接硬盘,让我们能够进入人类的过去。
当我们认字之后,阅读看上去很简单:眼睛看着词语,然后大脑提取出词的发音和意义。阅读是效率很高的获取信息的方式,它看上去不费力气,每分钟能读500个字,能够忍受字的大小和字形很大范围的變化,我们甚至能根据上下文推断生字的含义。如今阅读司空见惯、顺理成章,但法国认知神经科学家斯坦尼斯拉斯·迪昂指出,阅读是一个悖论:文字系统在4400年前才从新月沃土地带诞生,拼音文字也只有3800年的历史,而人类说话和唱歌已经有7.5万年的历史。“从人类进化的进程来看,这些时间跨度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从进化的角度来说,人类并没有充足的时间来形成专门的阅读神经回路。我们的大脑原本是为了适应非洲大草原的生活而设计的,而如今我们却兴趣盎然地用它来阅读纳博科夫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对于许多问题,进化都有时间去形成解决办法,但要用很长时间。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的祖先需要识别面孔、认路,但不需要去看菜谱、读文学名著、看各种报表、刷微博。阅读没有成为天生就会的本能,而是像走路、说话一样需要学习。
我们的大脑是如何习得阅读的呢?人类的基因并没有出于适应阅读的目的而进化,如果人脑没有为适应阅读而进化,那么实际情况就应该反过来:文字系统必须适应大脑的生理限制而演变。几千年来,书写者们想方设法设计适合灵长类脑使用的字词、符号及字母。文字系统变得越来越容易阅读,集中使用少部分记号,用它们组合出各种音节和文字。在各种语言中,字母一般都只有三笔,越简单的记号出现次数越高,比如T和L是最常见的,其次是X和F;所有的文字都是白纸黑字,对比强烈,为视网膜中央凹提供高密度的最优刺激源。
当我们读一句话时,大脑每次只能吸收7-9个字母,因为我们要用视网膜的中心地带(中央凹)来阅读,那里的视觉细胞对光线高度敏感并具有高分辨率,它在视野中占到大约15度视角。把字符串放入中央凹,它们才能处于焦点,所以眼球在阅读时要不断移动,每秒钟跳动四五次,每次前进7到9个字母,不断把信息带入中央凹。因为我们是从左往右读,右眼会为接下来的字符串做好准备。阅读时我们每一次眼跳只能辨别出10-12个字母,包括注视点左侧的三四个和右侧七八个。心理学家设计过一个实验,眼睛在跳动时,如果把注视点之外的文字换成没意义的组合,读者并不会注意到。如果眼睛不动,让文字移动,每分钟最快可以看1100-1600个单词,“看到那些声称可以让你的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1000词的快速阅读法的广告时,一定要持怀疑态度”。
从左往右读会略微提高阅读的速度和准确率,因为右眼可以直接把信息送到左脑的视觉词形区,它像一个“文字盒子”,它接收视觉输入,识别出字母与单词的形状,然后送到负责解码读音和意义的区域。单词激活脑中意义碎片的过程如同壮观的涌潮,一个单词可以在神经网络中得到共鸣,产生巨大的同步振荡,席卷上百万个神经元。认字之后,神经元还要构建一个大脑字典,统计出语言的韵律和拼写模式,协调识别意义与声音的网络。最终,一个普通的英语读者可以在十分之一秒内,把一个词跟头脑中储存的5万多个词中的一个匹配起来,理解它在文中的意义并顺利地前往下一个词。
在形成阅读能力的过程中,文字系统既适应大脑既有的回路,也要全面改造它们,所以学习阅读就是在重组大脑。“每节阅读课都会使神经元发生调整,之前与物体或面孔识别有关的一些视觉神经元,现在用于字母识别……在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的生物体内,存在大量冗余的神经元,许多神经元执行同一种粗糙的分辨工作,学习会产生更精确的表征。”
只有人类能够使用文字,迪昂说,这完全是因为我们比较走运,“人的大脑并不是完全适应阅读需要的。较差的视觉分辨率、迅速下降的学习曲线以及让人烦恼的镜像对称倾向……”灵长类动物有抽象学习能力,能识别任意曲线组成的图形,甚至能识别数字、给数字排序。灵长类动物具备跟人类相似的学习符号的初步能力,但没有创造出自己的文化符号。“它们缺失的不是学习能力,而是发明创造以及传播文化的能力。”人类的创造力来自大脑的综合能力:大部分灵长类动物的大脑都是模块化的,整个大脑分为几个特定的脑区,人脑前额叶皮质以及其他相连的脑区专门化程度较低,脑区之间的横向连接打破了模块化,可以对信息进行汇集、重组和综合。
曾经阅读等于大声朗读。阅读时发声是一种社会习惯,在当时这是必要的,因为当时人们面对的情况是单词堆在一起,没有空格,而拉丁语是一种不熟悉的语言,大部分阅读者都必须像小孩子读书一样边看边嘟囔。我们阅读时能够直接从书面文字直达语义,而不需要经过发音吗?还是我们肯定要先把文字转换成语音,然后才由语音转换到语义?一些研究者认为,不存在默读,一定要先把文字转换成语音,书面语言只不过是口语的一种副产物,我们必须把单词读出来,才有可能明白文字的意义。而其他人认为,转换成语音只是阅读初学者的特点。对于更成熟的阅读者来说,能够高效地直接把文字转换成其意义。现在,研究者们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两种方式都存在,而且是同时运作的。我们能够默读,但即使是熟练的阅读者也会利用词语的读音,不必动嘴唇,在更深层的加工中,自动提取出词语的发音的信息。语音通路与词汇通路并行运作,并相互支持。读一个新单词时,发音往往是唯一的对策。对于常见单词,我们不需要通过脑海中的发音来缓慢地解码。但我们仍然会在无意识水平上激活这些词的发音。
西方曾经流行整体教学法,注重篇章理解,敦促儿童接触有意思的故事。迪昂认为,阅读离不开把字和读音匹配起来,因此“阅读教育必须避免把孩子的注意力从字母水平转移开来,要对那些装帧精美的阅读手册持保留态度”。远程、在线课程也是不够的,“儿童并不是通过重复地把词语与相应的物体进行联系来学习语言的。当听到一个新词语时,他们通过追寻说话者的眼神,来确定他所指的是什么。只有当他们理解了说话者的想法,并能根据对方的知识和能力来考虑各种线索,才会为听到的新词赋予意义。如果仅靠一个扩音器重复与某个物体有固定关系的词,我们便难以进行学习。文化传播需要人去理解他人的想法”。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52期。作者为该刊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