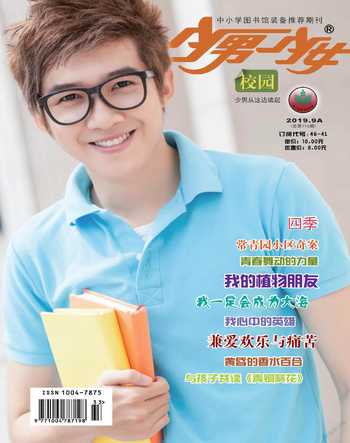写景散文如何处理好审美关系?
2019-09-10 07:22:44
少男少女·校园 2019年9期
问:
我写散文,很多时候被老师批评“为写景而写景”,写景散文应如何处理好审美关系?
答:
你的问题,牵涉到作者与景的关系,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我”与“物”的关系。
我们不妨拿范仲淹的著名散文《岳阳楼记》来说明一下。
该文中,有一段很漂亮的文字: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这里写的是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登岳阳楼,观洞庭湖。
眺望那辽远的洞庭湖水面,平静极了。湖水映著柔和的天光,沙鸥时而飞翔,时而栖止,美丽的鱼儿游来游去;湖岸和水间的小洲上面,兰花水草青翠芬芳。到了夜色降临,那轻纱般的薄雾也消散了。看那洒在水面上的皎洁月光,宛如浮动着的碎金。静静的月影在水中好像沉下的一块圆玉。听那悠扬的渔歌啊,不时从远方传来……
此时此刻,登岳阳楼的人感到了无限的欣喜。他“心旷神怡,宠辱偕忘”,简直被眼前这一切陶醉了。
范仲淹在这里生动地写出了我们所要谈的审美关系。
登岳阳楼的人并不去探讨洞庭湖的水系源流,也不留心那湖水消长的规律。
他在这里显然不是在做科学考察。
他与洞庭湖之间,不是一种理论关系。
同样,他对洞庭湖也没有教徒朝圣那样的崇拜和虔诚——他们之间也不是一种宗教关系。
他与洞庭湖,是一种审美关系:一派迷人的洞庭景色作用于登岳阳楼人的头脑,使他体验着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和激动,从而得到一种巨大的鼓舞和力量。
“我”与“物”,要有联系,切忌写了一大段与主题无关的景色,才能避免“为写景而写景”。
猜你喜欢
现代装饰(2024年1期)2024-02-27 08:39:10
故事作文·高年级(2023年10期)2023-10-23 11:21:36
东坡赤壁诗词(2023年1期)2023-05-30 00:41:39
东坡赤壁诗词(2022年3期)2022-05-29 04:58:53
音乐教育与创作(2019年9期)2019-05-16 09:34:10
校园英语·下旬(2018年5期)2018-08-17 00:05:24
中国三峡(2017年4期)2017-06-06 10:44:22
北方音乐(2017年4期)2017-05-04 03:40:00
中华诗词(2017年11期)2017-04-18 09:02:11
中国国情国力(2016年6期)2016-06-28 07:0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