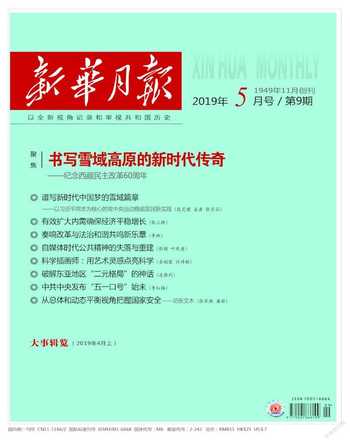未来社会:你愿意接受机器人量刑吗?
杨延超
机器人量刑对法官裁决意义重大
人工智能完成的精准预测,不仅对被告人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法官也具有重要意义——审理刑事案件的法官要完成的恰恰是精准量刑,并且精准到每一天。
人们无法想象一名法官作出幅度量刑判决后的结果。比如,法官判决被告人有期徒刑3-5年。显然,这样的判决完全不具有可执行性。据此,法官量刑需要具体到每一天,而这与人工智能的精准预测完全匹配。因此,人工智能的量刑预测对法官作出判決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刑法中关于“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罚”等规定使每一个罪名及其量刑空间在刑法上都有明确规定,而刑罚的可预测性是法律实现秩序价值的必然要求。
诚如德国著名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所言:“保证法律的确定性仅意味着法律是可以预测的,并不一定就能抵御那些完全多余或者不公正的法律。但是,这种可预测性至少能允许人们独立地规划自己的未来,并且在规划中及行动的考虑中纳入法律秩序的要求。”
在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看来,秩序的本质意味着个人的行动是由成功的预见所指导的,即人们不仅可以有效地运用他们的知识,而且还能有信心地预见到他们能从他人那里所获得的合作。
对此,德国哲学家、法学家费尔巴哈在“心理强制说”中也道出了刑罚可预测性对于减少犯罪的意义,即“行为人由于确信实施犯罪的欲望会带来更大的恶害,就会抑制犯罪的意念而不去犯罪。为了起到心理强制的作用,需要预先用法律明文规定犯罪与刑罚的关系,以便预示利害,使人们知晓趋避”。
法律规则为行为作出指引
人们研究量刑预测,最初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个别法官的“任性”。
通过对以往所有判例的学习后,机器人集合了以往所有法官的集体智能,从而有效防止因个别法官的非理性行为作出偏离较大的判决。从这个意义上讲,量刑预测与追求法律公平正义的目的一致。
在幅度预测场景中,刑罚是向人们传达犯罪将会受到惩罚的理念。这种理念最终会在人们的内心形成震慑。正如刑法学家贝卡里亚所言:“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因为,即便是最小的恶果,一旦成了确定的就总令人心悸。”
当量刑结果可以精准预测时,原有的震慑效果也将悄然发生变化。刑罚结果的预测会导致法律秩序朝完全功利主义方向发展。
比如,当一家企业已经提前知道用于生产的污水将导致环境污染并会受到处罚,企业所考虑的主要问题是违法成本与违法所得之间的关系;进而,企业会考虑要不要污染环境以及将环境污染到什么程度。按照著名法律经济学家波斯纳提出的观点,人在从事违法行为时会计算违法成本与违法所得之间的关系。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强调法律的指引功能。的确,法律的指引功能可以告诉人们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从而引导人们从善弃恶。然而,在绝大多数场景中,法律制裁的条款会设置一定的处罚范围,这既迎合了复杂实践的需求,也给执法者以自由裁量权,同时也为制裁本身制造了一定的模糊性。这一模糊性做法对树立法律的权威是必要的。
事实上,一旦行为者触犯了法律,他们会纠结执法者的执法尺度,甚至会因惧怕获得法律范畴内最严厉的处罚而焦虑不安。在这样的“焦虑不安”中,法律的警示、教育、处罚等作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法律带给人们最好的状态是:法律规则为人们的行为作出指引,而最终的刑罚结果又呈现模糊色彩,些许的模糊意味着不确定性和恐惧性。因此,法律也因具有神秘面纱而更富有魅力。
机器人量刑将改变庭审格局
可以预测的是,机器人通过对大量样本的学习,会预测出具体犯罪行为的量刑。在这种情况下,机器人已经考虑到既往发生过的所有相关案例以及可能对该量刑产生影响的所有因素。从客观上看,这是人脑做不到的,同样也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法治的统一和法律的公平。
通过在实验室完成的大量实验,我认为机器学习预测犯罪完全可行。这个结论将会极大地影响法律行业的职业生态。
首先,机器人预测量刑对法官执业产生影响。法官是否会被机器人取代的命题,被再一次提及。当机器人坐在了法官席上,这不仅是技术问题,而且还涉及人类社会最根本的哲学命题:机器人审判人类与人类命运终结者之间的关系如何?由此引发的机器人审判的合法性争议将远胜于机器人量刑的准确率。在人类主宰社会的前提下,机器人终将以法官工具的身份出现在审判中。毫无疑问的是,机器人可以极大地提升法官的审判效率,甚至可以最大限度地去除主观性而提升案件审判的公正性。机器人预测量刑在客观上导致自由裁量权的空间被极大压缩。机器人量刑的结果会深深影响法官的裁判,从而令原本法律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被机器人限制在一个极小的空间范围内。
其次,在机器人预测量刑场景下,律师的辩护方向也将有所调整:由法律之辩转向事实之辩。法律之辩与事实之辩是律师辩护的两个方面:法律之辩是找到能适用本案的全部法律,以期达到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目的;事实之辩是尽可能地寻找对当事人有利的证据,还原案件事实,尽可能地对当事人更有利。机器人预测量刑是在假定某个事实成立的情况下对刑量作出预测。比如,在交通肇事罪的审判中,各方需要在法庭上出示证据还原案件事实,如果律师能找到受害人存在过错的证据,无疑将对本案具有重大意义。这属于事实之辩的范畴。一旦事实无可争辩,机器人的量刑预测便成为可能,律师对于法律适用的理解或将让位于机器人基于一个确定事实作出的分析。
最后,在机器人量刑预测背景下,法庭辩护的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原本轻证据、重法律的辩护场景最终将演化为重证据、轻法律的崭新辩护格局。
(摘自《法律与生活》2019年第3期。本文摘自图书《机器人法》,法律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