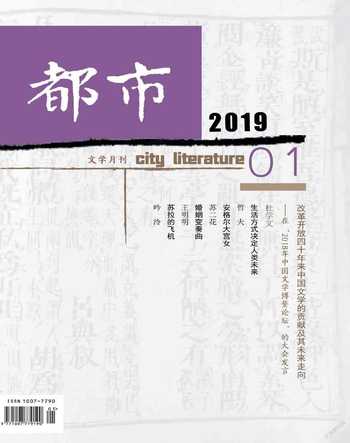传统的价值不容置疑
王立世
一提传统,有些人就流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传统似乎与落后沾亲带故,难登大雅之堂。今天我讲传统的价值,更多的是针对诗坛长期以来对传统的疏忽、懈怠给新诗带来的负面影响有感而发,今天也想借董耀章先生的诗歌创作实践来说明现代与传统割裂的危害,以及新诗回归传统的必然。
可能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年轻时特别想远走高飞,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到了一定年龄,经历了各种变故和人世沧桑之后又特别想落叶归根,回归生你养你的那片土地,甚至死后都想埋在故土。我们写诗也一样,年輕时喜欢用形容词,追求华丽,也喜欢用动词,彰显生命的蓬勃。喜欢雕琢,重视外在的东西。年老时开始返璞归真,追求自然质朴,大量使用名词表达人生感悟,有意减少辞藻和技巧的成分,把无技巧看作是最高的技巧。
改革开放后,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新诗迎来了“五四”以来又一次革命性的变革,涌现出北岛、顾城、舒婷等一大批被定义为朦胧派的优秀诗人,随后又出现了以韩东、于坚、西川、欧阳江河等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这不同于传统诗歌的风景,是中国新诗百年最亮丽的风景之一。此后,诗坛越来越热闹,流派越来越多,诗越来越看不懂。有趣的是读诗的人越来越少,写诗的人却越来越多,有人嘲讽会按回车键就能当诗人。这些说法虽然有些偏激,但也说明了诗坛表面的繁华无法掩盖事实上的荒凉。新诗被西化,传统被割裂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导致新诗被冷落和边缘化的命运。西方诗歌被简单移植,玩文字游戏成为时尚,雾里看花、水中捞月成为潮流,千奇百怪,无所不有。诗人严重脱离现实生活,热衷于炫技和卖弄,这样的诗人数量不少,随处可见。这样做的结果是新诗不但没有走向世界,反而面临新的尴尬。这时人们才从梦中惊醒,嚼别人嘴边掉下的馍渣嚼不出什么味道,重复别人永远不会是自己。丢掉传统,淡化民族特色,走向世界绝无可能。外国很多意象诗确实不错,但在我们的唐诗中意象诗早已出现。美国诗人庞德学唐诗,我们中国诗人又去学庞德,究竟是谁学谁?唐诗宋词为世界诗学提供了中国经验,艺术价值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蓄意割断新诗与旧诗的血脉关系,就会迷失方向。觉醒者在寻根,盲目者在断根。不知从哪里来,就不知到哪里去。丢掉传统就像丢掉了灵魂,失去方向就会感到迷惘。我理解的传统,不仅仅是技艺,更重要的是人文精神和民族气魄,当代诗歌缺失的正是这些,需要向传统学习,从传统诗学中补钙。
新诗迷失方向后,回归传统是必然的。回归传统就像回乡一样温暖踏实,能让新诗重新找到精神家园和文化自信。
今天召开董耀章先生诗歌研讨会,意义就在此。对董耀章先生而言,不用讲回归,他年轻时的诗就具有传统之美,历经了中国新诗的重大变革和风风雨雨后,他始终在坚守自己的诗歌理想和美学追求。对传统的热爱,对中华文化的信仰,不为任何风声所动,表现出坚定不移的定力,这是难能可贵的,体现出一种文化的自信和自觉,也有利于形成个人较为稳定的风格。冰心老人说过,一个人只有年老了还在坚持写诗,才是诗人。有的人确实具有写诗的天赋,写出几首好诗就销声匿迹了。很多诗人耐不住清贫和寂寞,改道易辙,升官发财去了。董耀章先生一生献给了山西的文学事业,长期担任《火花》《九州诗文》主编,连续几届当选为省文联副主席。更难能可贵的是坚持写诗几十年,坚守传统几十年,一如既往,不改初衷。现在年过八十,仍然笔耕不辍,令人感动,让人敬佩。下面结合董耀章先生的诗歌创作,谈谈我对传统诗学价值的思考和认识,以期对新诗创作有所启发和帮助。
一、大众化。文学的大众化早已提出,董耀章先生走的就是大众化的道路,当代诗歌越来越小众化、贵族化。他的诗质朴自然,明白流畅,不像当代一些诗人,喜欢玩文字游戏,喜欢在诗中说梦话。有一种误解,认为大众化就是脸谱化,就是对个性的削减泯灭。其实大众化与个性化并不矛盾,如果个性化的东西能够实现大众化,文学才能获得长久的生命力。大众化不是新诗才有的,《诗经》为大众化开了好头,唐宋诗词把大众化提到了新高度,白居易、杜甫是大众化代表性人物,他们的诗老百姓都能读懂,像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杜甫的“三吏”“三别”。大众化的诗歌很多,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李白的《静夜思》、王维的《杂诗》、贺知章的《回乡偶书》、韩愈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柳宗元的《江雪》、刘禹锡的《乌衣巷》、李绅的《悯农》、李商隐的《夜雨寄北》《乐游原》、王安石的《梅花》、苏轼的《题西林壁》、范仲淹的《江上渔者》等等。这些诗是古诗中的口语诗,用大众化的语言表达大众化的情感,不仅同时代人能产生共鸣,而且流传久远,一直被人们喜爱。既与选取永恒的题材有关,又与诗歌的大众化有关。有人认为大众化就是下里巴人,灰眉土脸,比不上阳春白雪,于是就千方百计把自己打扮成贵族。有人认为口语诗是新诗才有的,上面所举的旧体诗比当代的口语诗还口语。很多当代诗歌比这些唐宋诗歌写得都拗口,只有花言巧语,没有真情实感。只有辞藻,没有内涵。内心越强大的人,越不注重外表,甚至不修边幅。内心越空虚的人越在意外表,喜欢浓妆艳抹。写诗也一样,真正的好诗是用最朴实的语言表达最真挚的情感、最深刻的思想,这是最具难度的写作。外表繁复艰深内里浅薄苍白是容易的,也是失败的。大众化不是千人一面,因为大众化不排除个性化,也不等于简单化,同样可以达到情感的浓度、审美的纯度、思想的高度。
二、音乐性。董耀章先生的诗如行云流水,读起来朗朗上口,具有音乐美。《我爱大海》《山西我们永远爱你》等诗歌已经谱成乐曲在传唱。诗歌是在音乐声中诞生的,应该说是先有音乐后有诗歌。《诗经》中的好多诗是在劳动过程中随着劳动的节拍唱出来的。闻一多先生提出了诗歌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把音乐美放在首位。当代诗歌的音乐美几乎丧失殆尽,不要说吟唱,读起来都是结结巴巴。古体诗富有节奏感和韵律美,很多适宜于谱曲歌唱,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李煜的《虞美人》等等。新诗无须像旧体诗那样讲究平仄押韵,但如果没有内在的旋律就是一大缺失,新格律诗的提出自有其道理。只有那些发自心灵深处的诗歌才可能形成优美旋律,像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唱出来是很美的。那些无病呻吟、生编硬造的诗歌不可能形成优美的旋律。
三、民族感。凡是称得上伟大的诗人,都是本民族的代言人,李白是,杜甫是,文天祥是,艾青是,田间是,牛汉是,荷马是,莎士比亚是,普希金是,米沃什是,聂鲁达是,惠特曼是。一个诗人的创作不能反映本民族的生活、情感、理想、信念,他的价值从何谈起。董耀章先生的《英雄的太行山———为纪念抗日战争60周年而作》《烈士墓前的发问》《四访狼窝掌》等等,我们从中读出了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坚强不屈的伟大精神。《万家寨之歌》流淌着三晋儿女汹涌澎湃的豪情。中国元素、山西气魄,民族特色,历史积淀,人文关怀,构成了董耀章先生诗歌的壮美风景。再反观一下当代诗歌,很多诗如果不署名,读后会认为是外国人写的,为什么会这样呢?缺乏民族特色和时代内涵,写得不是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是从西方诗歌中拼凑出来的。艺术来源于生活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如果能处理好生活与艺术的关系,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就不会出现东施效颦的窘相。
我们讲大众化,讲民族性,不能不讲人民性,毛泽东讲文艺为人民服务,就是讲文学的人民性。当代诗歌的人民性在哪里?把小我强调到不适当的位置,膨胀的病态的位置。小我没有表现出大我,没有处理好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人民性就是共性,小我就是个性。共性是通过个性体现的,个性如果不能表现共性,个性也就失去存在的价值。共性没有个性的支撑,也是苍白的、虚弱的。诗歌创作应防止两极,一极是片面强调个性,脱离时代和环境。另一极是片面强调人民性,陷入空洞的概念化,进行口号标语式创作。艺术上的左摇右摆是不足取的,如何处理传统和现代的关系至关重要。我讲传统的价值,不是复古,也不是对西方诗学的全盘否定,而是讲传统与现代的对接,东学与西学的融合,实现传统的现代化,西学的本土化,不能将传统与现代割裂,东学与西学对立。当代诗歌是个性出来了,共性没有了,传统丢掉了,西学学歪了。这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一个长期都没有解决好的老问题。我是从宏观上分析当代诗歌的病症,当然新诗百年的探索是在迂回曲折中前进的,不乏经典之作,如郑愁予的《错误》、芒克的《阳光中的向日葵》、徐志摩的《沙扬娜拉》、张枣的《镜中》、余光中的《乡愁》、江一郎的《向西》、欧阳江河的《一夜肖邦》、周涛的《野马群》、木斧的《端午》、西川的《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叶文福的《火柴》、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汤养宗的《父亲与草》、张二棍的《韭菜》、李元胜的《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海子的《日记》、张执浩的《高原上的野花》等等,都是传统与现代完美结合的杰作。我要说的是传统的价值不容否定,继承的同时也要发展。外来先进的文化不能拒绝,不能吃夹生饭,一股脑儿吸收,存在消化的问题。如果能把二者的关系处理好,新诗的生态就会有大的改观。
我主要从以上三个方面总结董耀章先生诗歌的艺术特征,也是为了印证传统的价值不容置疑这一观点。讲传统,无须羞羞答答,我们要理直气壮。实际上,董耀章先生的诗歌除此以外还有很多特点,比如大家习惯拿意象评诗,董耀章先生很多詩歌体现出大众化、民族感、音乐性,又不失意象美。他的《月下品茶》就达到了这样的效果,诗中这么写道:“苦雪水苦雨水/涩眼窝咸泪水/月儿杯中久泡/泡白一头白发”,就是这么短的诗,出现了茶、雪水、雨水、眼窝、泪水、月、杯、发八个意象,意象可谓密集。写了苦、涩、咸三种味道,泡与品两个动作,茶水、雪水、雨水、泪水、月光几种色彩。品茶是中国文化,月下品茶更有意味,品的是生活的各种滋味,人生的各种滋味。这首诗适宜于吟唱,色彩明朗,形式整齐,具有闻一多先生讲的“三美”。这首诗是用大白话写成的,妇孺都能读懂,写的又是我们民族生活的一道风景,具有大众化和民族性。内涵丰富,情感蕴藉,语言质朴,生动形象,真实可感,体现了传统诗学的美和价值。这首诗表面的浅显与内在的深刻、语言的平静与情感的浓郁构成强烈的感觉反差,产生了不一般的审美和冲击,读后觉得余音犹在,意味无穷。传统的价值在董耀章先生的诗歌中得到了具体的生动的有力的见证,若能加进一些现代文化的因子,那风景将会更美。限于时间,我就不再展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