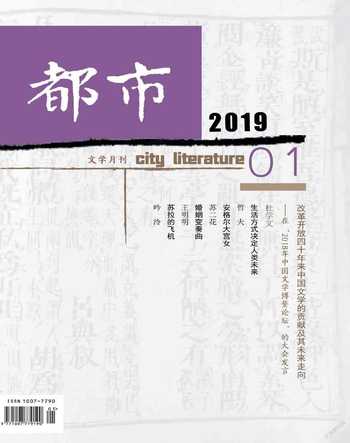马克福利欧大街43号
白琳
最开始我住在马克福利欧大街43号。
那是一间紧靠地铁口的公寓,设施很好,大铁门进去,还有内庭,有整堵墙的衣冠镜。住客们大多是罗马市民,习惯用香水,进了电梯香风阵阵,只不过品类太多,混在一起有点面目全非。
电梯很小,只能挨挨挤挤站下三个人。如果要带行李上去,就只能够一人一行李。老电影里那种,一张外拉门,然后是对开门,手动推开,合上,按按钮,咚一声,一顿,就上去。习惯了两三天。晃荡一声上去的时候,才有了在异乡的感觉。晃荡一程停下来,下电梯还要把两道门重新关好,不然这电梯别人就没办法再用。头一阵子和一个来考罗马美院的男孩子一起住,他没有习惯,有一晚电梯就停在我们这一层下不去。第二天一早就来了两个保安,很客气地给我们上了一课。虽然是上课,临走时却把谢谢说了一筐子。这是礼貌性强势教育。罗美男孩子满面通红,热气四溢,此后不曾再犯。
沿街的建筑有很多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在城里上考察课的时候,常常就这样出入了别人的内庭。这些住宅民居从前大多都是贵族的宫殿,现在一格一格被拆成小小的单元。庭院里的石柱雕塑,都还好好地在着,有一些还完好地保留了盾形纹章,鹰,孔雀,鱼,鹅,龙蛇,海豚,麋鹿牛羊等等动物,就那样简写又夸张地衬着山脉,河流,树叶,搭配着丰富的色彩和纹饰,刻印在一个家族的脉络里。———好多家族也都投身于岁月长河沉了下去,只有这些脉络从时间里浮了上来。除了人的残缺,破碎的面容和损坏的四肢,看着快要凋零的却仍然活着的树,还有如影随形的寂静,脚下的铭文,额上的家族徽章,都浸泡在温热的地中海气流中。
有时候仰着头看向那些窗户,会看到一株朝上或者向下长着的植物,也有时候,看到打开的窗户,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手臂支着窗沿,吸烟,聊天。罗马的天空到了冬天很湿润,阴雨天出去也不会觉得冷,就是一派温和的润。阴天的时候,雾让整面墙壁的绘画也跟着湿漉漉起来。教授C把四十年前他来罗马时候的激动和喜悦分享给了我们所有人。在一条又一条七扭八拐的巷子里穿行的时候,也会告诉我们哪家店的东西很好吃,在哪里他又做过什么。C是客座教授,只在罗马待完这个冬天就要回到英国去,每次快要下课,都发消息给太太(太太是原装,C深爱,看到她眼睛里还会放星星),那位看上去温和又平凡的女士每次都在教授C授课终点附近的一家小咖啡厅等他。然后他们一起,追忆过往,去他曾经去过的他至今难忘的餐厅吃飯。
教授C讲述的罗马,无论是两千年以前的,还是四十年以前的,都有迹可循。尤其在他而言,罗马的静止让人惊奇,一切都没有太大的变化,四十年只不过一瞬间,他就成了一个老人。每当他扛着一只帆布包,穿着卷边的洗得变了形的格子衬衫大步向前或者驻足观看的时候,一些诗句就从我的眼前掠过:心游目断三千里,雨散云飞二十年。豪竹哀丝真昨梦,爽砧繁杵又惊秋……我没有跟着他一起忆旧,我只是很好奇那些庭院里的窗户,有一些有三角楣,有一些有半圆拱,有一些什么都没有,只有合住的百叶窗。虽然知道那里面和我的居所相差无几,但还是扼不住想象的潮流。
言归正传。
马克福利欧大街四十三号还住着两只猫,一只布偶,一只豹猫。初次见面,豹猫躲得老远,动作敏捷。如果稍微靠近,就会发出低吼,野性未泯。布偶是另外一番景况,还不等我把那只26寸大行李箱放好,就翻开肚皮让我揉搓,她仗着自己好看,肆意奴役他人,一点也不忠贞,见谁都翻肚皮,生人来了一开始还欣喜,觉得她和自己尤为亲近,几次之后,大家也懒得理她,娇憨太过,就是滥情。倒是躲得老远的豹猫,偶尔和熟人玩耍一下,就有点小小珍贵。
在马克福利欧住了一阵子,也没有见到房东。房产中介小刘说,是个中国人,很有钱。房子空了大半年,每个月一千六百欧的房租都不要,也不着急房子没租出去,就那么随意地可租可不租地耗着。我来的时候他回国去处理事务,直到我搬走的时候也没等到他回来。后来我的税号被寄到了旧地址,去取的时候才打了照面。话不多,个子不高,看上去苍白而孱弱。
他女朋友正好相反。
住进去差不多一周之后,来了一个女生,个子高挑,身材好,但骨架大。脸上涂得粉白,过白。我看过她卸完妆的样子,很接地气,比涂了脂粉好看,皮肤也没什么大毛病。穿着黄色带帽卫衣裙蹲在地上和布偶玩耍的时候,年龄看着小一些。有一天半夜里起来在走廊上遇到她抱着猫摆拍,妆容精致,面色惨白,脖子颀长,穿着露肩雪纺连衣裙,碎花瓣碎叶片从肩头飘飘拐拐地落下来。拍完扔了猫要出门,一迭声嫌猫掉毛。那天她穿了三寸高的高跟鞋,所以从卫生间出来穿一双凉拖的我就只好仰视她。那时候我想到了米开朗琪罗的摩西。原计划为了放在上部而雕刻的有一点变形的摩西最后放了下来,所以就看着比例不协调。身体宽大,过于魁梧。
几天之后我们略微熟悉了一点,互相加了微信。在卫生间外的小厅或是在厨房门口的拐角遇到也偶然会聊聊天:
我以前是公务员,辞了工作来的。
来了做什么?
也想考美院来着,但是学了三个月语言现在就放弃了。
那么然后呢?有什么计划?
没计划。就四处看看呗。
要留下还是回国?
肯定不留下。不过我有一个朋友在罗马美院念书,不用去上课也能过,她老公,啊不,她男朋友和罗美的人关系很硬,我那朋友就根本没去上课也能顺利毕业。
倒是有听过罗美很没有节操的故事……
可不是,我那朋友两年的时间,就干了一件事,生孩子。
现在结婚了吗?
还没,不过又怀了二胎。那男的不是一般人……
加了微信之后,我在房间里待到无聊的时候就点开看看。女孩子朋友圈里每一张照片都半裸,所有的腿都修长无比,裙角被提到极限,各种部位都呼之欲出。她朱唇轻启,眼神迷离,举着布偶当道具,配一些图文不符的说明。此处不再赘述。
她不是特别喜欢小动物。和布偶在一起的时候,也只是当个玩偶道具。这两只猫很贵,都在2000欧以上。她说她送了人一只,那只便宜一点,1600。
会想它吗?
不会。它得了皮肤病,有一块秃了怎么也长不好,难看。
我住着的那阵子,只看到一次她素颜的样子。那天她很羞涩,一次也没抬眼和我对视。
尽管知道女孩子虽然会把自己收拾得体体面面,但家里乱成一团也是常有的事。但因其是房东先生的另一半,我还是对她寄予厚望。
因为房东不在,我住进来的时候公共区域乱得不像话。厨房很大,刀叉餐具却丢了一桌。还有没有吃完的面包片,敞着口发了霉,一包砂糖倒在煤气边,撒出来许多内容,上面爬满了来觅食的蚂蚁,黑色的蚂蚁,棕色的蚂蚁,皮肤不一样,长相也多少有一点区别,也不知道究竟是不是一家。偶尔还有一只歇着的苍蝇,死掉了尸体还贴在壁砖上的蟑螂,一张很旧很油腻的抹布垂挂在灶台上,以前大概是白色的,我遇到它的时候它已经救不回来了,皮肤褶皱,布满了裂纹,还黏着黑色的不知道多少天以前生成的残渣。每次开厨房门的时候,布偶和豹猫都会跟着進来,豹猫还是小心,布偶纯粹就是跟人,见到人就把肚皮翻出来。等过了很久,我早已搬出那间公寓之后的某一天早晨,想到那些场景的时候,我想起了《记忆的永恒》,只不过我的记忆里面,树上挂着的不是钟表,而是一只雪白的布偶。那些窗户和阳台,就变成了平静的海面,死寂的旷野。
我忽然也就理解了布偶的黏人。因为它可能太痒,它实在无力承受那些痒的重量,所以只好借助一双又一双手来缓解它皮肤上的折磨,表现得轻浮又浅薄。猫砂很多天不换了,屋子里气味爆棚。帮我打扫房间送东西的朋友总说,这样下去不行,一出电梯就会闻到难以忍受的臭味,不多久就会有人投诉,严重的话还会被罚款。所以房东女朋友来的时候我心有期待,希望她可以收拾一下猫咪,顺便关照一下房子的卫生环境。
然而我就是白想了这许多的内容,因为她来了之后房间更乱。猫砂不但没有换,还不小心被踢翻了一些在过道。卫生间的洗漱台上摆满了化妆品,盖子都没有合好,有一些粉底液沿着瓶体流了下来,用过的卸妆棉的尸体铺在洗衣机上,上面红黄黑一片又一片。卸妆水也敞着口,等细菌进去跳舞。洁面乳横躺着,脖颈的褶皱里全是黑泥。粉扑和海绵球灰蒙蒙地扔在台子上。
脸会烂掉的吧。有时候我想。因为实在太脏了。
一开始我很想和分租的室友商量一下,想一个比较合理的解决之道,比如说一起请一个家政,每个月清洁两次。或者是每周一个人做一次清理。但是我总也没有和他见面的机会。来考罗美的周同学每天都在打竞技游戏,我敲门推门他都处在战争状态。虽然和周同学是两个时代的人,但我也很知道游戏的重要性。精神高度集中的周同学的背影看上去还是很有专注与专业味道的。他一来罗马就买了特别大的显示屏并配置了新主机,他的房间与其说是一个美院生的房间,不如说是一个游戏职业人的房间。
你是选手吗?有一次趁着周同学去厨房泡面我问。
不是啊,就是玩玩。周同学耳朵红了。他面色很好,常常不是这里红就是那里红。
我觉得周同学也不像是一个会操心生活环境的人,所以没有多说。他几乎足不出户,有一次一个女孩子来,在卫生间门口碰到我,自我介绍是周同学的同学,一起来考美院的。那女孩子小巧可爱,留着过肩发。来家里的第一件事是洗澡,洗完澡浴室就成了潮汐退落的沙滩。
后来又来了几次,也是洗澡和沙滩。
我见惯不怪。这边留学生认识两天就恋爱的不少,恋过之后很快就分手的也不少。
除了有限的几次交流,我到底都没怎么见到周同学和房东女朋友。一个是寄居蟹,一个是猫头鹰。陪伴我最多的,反而是布偶和豹猫。其实到最后,布偶大概感受到了我的不耐烦,也不怎么撒娇了,倒是豹猫,慢慢和我熟悉起来,愿意和我一起玩一只小竹条或者一只小铃铛了。
我住的那间房子有大大的阳台。阳台底下是热闹的街道。右边有一家印度人开的水果店,我在那里还打印过一份文件。很贵,打印一张纸要一块。如果在学校打印的话一页纸是两分钱。买一个打印机也才只需要25块。因为这样,我也几乎不在那里买水果。而是会走一个街口,转弯,去一间小超市采购。住着的房间也挺大,蓝白基调。白色太白,蓝色太冷,房间太大。太大的感觉,就像是始终是一个不能装满的水瓶,中心晃荡,毫不踏实。
我偶尔在那间房子里感到孤独。这也可能是因为我刚到罗马,还没有什么朋友。孤独的感觉只能在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的途中才能被体会到。那时候我常常会想到,我在国外。可是等我走上大街,看到那些外国人的时候才会意识到,我才是一个外地人。被这些非外地人看成外地人,起码我认为他们是非外地人并羡慕他们这些非外地人。对,我羡慕他们。我在几个没有前后联系的夜晚站在阳台上从外部观察这里的生活,我知道我已经被排除在一切联系之外,心里想着成千上万个此刻被灯光照明着的酒吧,那里的人们任凭黑暗笼罩着一切,丝毫没有我这些烦恼。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烦恼,他们的烦恼并不值得羡慕,但彼时彼刻我却愿意与他们中的任何人交换一下位置。
没有课的时候,我就到附近的渡槽公园去散散步。公园这个词真是可以矮化它原有的美感。罗马的公园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是自然和人文的天然结合。简单来说就是一大片超出公园范围的野外和站在卧在野外的土地上的历史遗迹。渡槽公园里有意大利松树和广阔的草地,还有长长的小路。无论是早晨还是傍晚,都有人在跑步。
傍晚,那里就是一个小小的生活区域。附近的居民带着孩子或者狗出来散步。穿过两排渡槽之间的领域,散落的古代建筑,在面前显示了它的宏伟壮阔。有一个工作日的早晨,我又去了那里,就像一片旷野,我发现,旷野里还种着白菜。
在马克福利欧大街住的短暂的十天,是我在罗马唯一的短暂孤独。我改掉了在国内晚睡的习惯,每一次都睡得很早,睡得很沉,睡得很累。我的睡眠就像我读的某一本小说,我做的梦也好像是完全重复我过去做过的梦。我在梦中进行搏斗,仿佛在与一种既无意义又无时间、地点的生活搏斗,我力求找出梦的意图与梦中的道路;它应该有自己的意图、有自己的道路,可我找不到,就像人们开始读一本新书时一样,不知道这本书会把你引向何方。我在梦境之中要寻找一种抽象的、绝对的时空,并沿着一条明确的路线前进。但是,当我觉得我快要找到的时候,我却醒了,发现我躺在床上并未动弹,一切重新开始。
后来,等我搬到帕米络托娅缇大街之后,除了和朋友们聚会到很晚,喝了酒或者吃了很多东西或者不得不连夜写作业之外,我睡得很好,睡得很沉,睡得很平静。在罗马,我第一次进入了没有梦境的睡眠。
第一次有这样的睡眠是在曼谷来罗马的飞机上。因为长久的疲惫和紧张感,因为有免税店里买来的颈枕,我睡得很沉,睡得很好。且越睡越安心。我身边的意大利母女很安静,我睡得很安心。就是睡到最后,脚有一点肿了,鞋子不大好穿进去。在曼谷飞往罗马的十一个小时里,在12192公尺的高度,9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和零下57摄氏度的气温里,我陷入了死一样的睡眠。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已经飞行了8461公里,还有572公里到达罗马。在那些时间里,我把疲惫都睡了出来,它们从我的每一个毛孔里挥发出去。因为那漫长的睡眠,到罗马之后,我如此新鲜,那么轻松,一点也没有经历倒时差之苦,仿佛我本应该就在那里出现。
我决定从马克福利欧大街搬走是一瞬间的。我觉得那里不属于我。我不属于那里。我和我的外部一点也不融合。有时候命运就是如此,当一个念头乍然显现,那也许就是一种指引。指引自己向更好的地方而去。
我很快找到了新的住所,拎着箱子搬家。我在窄小的电梯空间里第一次被意大利人夸奖。夸奖我的是一个年纪很大的老太太,花上衣黑裙子,银发,皱褶,干瘦。左手臂上挽着一只方形皮包,另一只手拎着从超市采购回来的食物。她语速很快,看着我的眼睛说话,满眼都是温柔的笑意。
她说:这位女士,你很漂亮也很可爱。
我说:谢谢谢谢。
她说:是真的,我说的都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