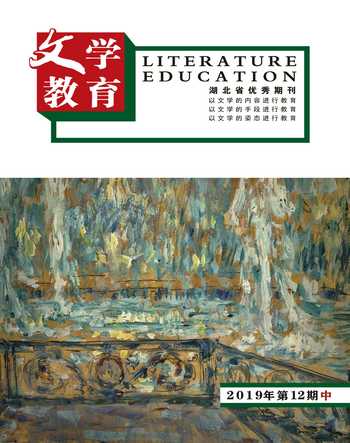生命回响、古典意识与诗学重建
从代际来看,1981年出生的赵目珍算是80后诗人。从类型来讲,学界普遍将他视为新世纪“第三条道路诗派”核心成员,并指出他们的诗歌创作追求后现代的写作范式,力图将诗歌的思想和艺术有机结合。然而,这样先入为主的判断很大程度上起了遮蔽和混淆的作用。一来,自80后诗人出场,他们的诗歌质量和玩诗姿态就备受质疑。实际上,不少被选定为代表的80后诗人并不能标示80诗歌的整体水准。二来,任何类型或群体的命名很容易造成作家个性和个体写作特色被忽视。恰是如此,抛开代际和类型意义的身份认定,我更看重作为特定个体的赵目珍,更乐于发掘他诗歌创作的个性。近年来,他陆续出版了诗集《外物》《假寐者》和散文诗集《无限颂》等,将诗歌当作安妥灵魂和诗意栖居之所在,虔诚书写对自我、时代和世界的生命体验,传达出现代与古典交融的诗意。
一
赵目珍是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但他在新诗写作和文学批评等领域同样有着不俗的成绩。从《外物》到《假寐者》,历经十余年的沉淀,他的新诗写作逐步走向成熟。他对个体、生活、自然、社会、历史、时代和世界的体察和认知,都在诗歌中得到了呈现。恰如王家新指出的:“他书写自我的世界,直至其痛苦燃烧的内核,而又保持着对全部生活的敞开;他在诗艺上博采众长,但又渐渐显露出个人的音调、美学取向和语言功力。”[1]平心而论,赵目珍的确将“自我世界”和“全部生活”最大程度上敞开和融合,形成了与生命对话的审美特质。
入选“星星诗文库”丛书的《外物》(2014年)是赵目珍的第一部诗集。这部诗集涉及主题广泛,包括“大音希”“外物”“小人物”“故乡在北”等四辑。新近出版的散文诗集《无限颂》(2018年)列入灵焚和周庆荣主编的“我们·散文诗丛”第五辑,分为“孤独者”和“闲情赋”两辑。而诗集《假寐者》(2018年)则包括“击壤歌”“还原诗”“局内人”“寓言诗十九首”“谈论一座城池”等五卷。不难发现,这些诗集的篇章命名别具匠心,耐人寻味,从中又可见到诗人的个人情怀和诗学观念。每部诗集中收录的诗歌根植传统,对接当下,典雅且厚重,空灵又不失沉稳,在题材选择、表现形式上显出一种艺术穿透力。
这样具有穿透力的诗歌主要得益于诗人对人与自然、个人与生活的看透和洞察。读赵目珍诗歌,我们能直观感觉到那种迎面扑来的自然气息。换句话说,他诗歌传达出了一种自然觉醒,“从万物中汲取,不腐、不朽将成为一种可能。”(《万物生》)紧跟诗人的步伐,我们一起走向那梦中最美的群山。且看,“薄暮,山中煮水”,“鸟声沉睡。野草与沟壑布满了深邃。”(《山中》)那空山中“云绕开了雨。/花朵像沉睡中的幽灵,一会儿开在这里,一会儿开在那里。/动物们正在聚集,或者离去。”(《空山》)且听,“起雨了。孤寂的雨夜似乎总是会出现不朽的神迹。”(《春夜独坐怀故山》)走在深山的我们,“对着一场雨下落,就如同对着/内部的潮汐涌动,然后按时退去”,“面对一场雨/又有如面对一场盛大的宴席。”(《对雨》)此时,“山雨隔绝了尘世”,“是一种苟且,也是回望中的深潭。”(《深潭》)
在赵目珍笔下,花草树木,鱼虫鸟兽,均可入诗。生长在荒野的野草,“在田畴边,在丛林里,在山冈上,在泥涂中,亲爱的野草,它们是那样的野性。”(《野草,及其肉身》)而“此刻的荒野/满眼都是奔跑的黄昏/满眼都是灿烂的烟火。”(《荒野笔记》)且观,“还有那些南飞的乌鹊,它们辨不清历史的黑白/它们鸣鼓入蜀,或入江东;与入鲍鱼之肆/抑或芝兰之室,看似并不相关/月仍旧明,星依旧稀。良禽择木而栖。”(《乌鹊记》)且思,“那些三叶虫、鹦鹉螺、鱼龙/以及石莲和大树上的懒慵/几万年的春睡/都已寄托在岩中。”(《春睡帖》)很大程度上来讲,诗人通过诗歌努力恢复人与自然不可割舍的联系,强化了个人/人类的感情投射和对现实生活的超越,从而抵达到了一种更高远的生命境界。
诗人对春夏秋冬、晨光暮霭的感知极其敏感,体现出了异常强烈的时空意识。在春天,“那些细琐的花儿开满了忧伤。”(《春风度》)“沙鸥水鸟,抖落一身輕狂。/漫山的春色宜人。”(《春梦赋》)在夏日,“于焦灼的时间与空间,消夏的萤火,在昏暗的丛林深处进行闪耀。”(《消夏》)给人印象深刻的是,诗人对黄昏感触最为敏感。单从篇目来说,就有《暮歌》《暮霭中》《薄暮诗》《暮归诗》《天将暮》《暮归》《小小的黄昏》《黄昏时分,我终结了一段旅程》等。诗人体悟到:“暮雨苏苏,即将辞行留仙居。”(《商略黄昏雨》)在《暮晚中》,诗人还更深切感叹:“暮晚虽好,却终须告别。这是一个无法逃脱的结局。”当然,与“暮晚”相对的“晨光”也多次出现在他的诗歌中。在《晨光诗》中,诗人写道:“黄昏凝固太久。恍惚的大地此起彼伏/晨光中的雾岚散尽了对抗/苞米上升为整个一天中的主角。”从上述两个意象来说,截然相对的晨光和暮晚实则是明与暗的交替,既代表着纯粹的时间,也是流动的生活,又可视为个体生命的不息。
除了自然万物和山川时空,赵目珍的诗歌还有喜怒哀乐等情绪流动,饮食起居等日常生活。像《相见欢》《独坐》《听风》《套中人》《沉默以后》《忧伤诗》《重阳诗》《宴饮诗》《考场诗》《还乡诗》《在人间》等等。在《与妻》中,诗人惭愧说到:“如此生活将减轻你的茫然无序。/让失掉的、远去的以及无法追回的,全都回归——人生有寄。”在《第十四天,致女儿》中,诗人深情告白:“对于你,我有很多的殷勤要献。但时间似乎尚早。/那就让我们一起置身于这强硬的光阴,伴随着日月星辰,顺流而东吧。”此外,还有诗人生活和谈论的“一座城池”。在这里,有“生存”的体悟,有“异乡”的“体验”,有“黄昏时分,我终结了一段旅程”,“我陷在一片人群中”,“我们只是身处一隅”,感受“大雨倾盆之后”的滋味。所有这一切,诗人反复在记录“一座城市的断想笔记。”如此,“只要心无挂碍/尘埃洒落一地,隐喻顿然归真”(《秘境:关于一座城市的断想笔记》),我们似乎也可以感受诗人在个人与生活的交融中达到自足和超然的生命回响。
二
若说赵目珍诗歌的“生命回响”是基于诗人对自然和社会、现实和生活的观照与体悟,那么他诗歌中的古典意识则是新世纪新诗自觉回望传统的重要体现。关于新诗的现代与传统问题,李怡认为,新诗“在漫长的历史中建立的一个又一个的古典理想常常都为今人公开地反复地赞叹着,恢复诗的盛唐景象更是无数中国人的愿望”,而“回忆、呼唤、把玩古典诗歌理想,是人们现实需要的一部分,维护、认同古典诗歌的表现模式,是他们的自觉追求”。[2]说到底,赵目珍的诗歌着实提供了新诗现代与古典交融的写作路径,展示了新诗现代意识与古典意识并行的一种可能性,很大程度上自觉接续了新诗的历史关怀与文化记忆。
对于年轻的当代诗人赵目珍来说,这样的古典意识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或者说,这种古典意识在他的诗歌中到底是如何体现的?细读《无限颂》《假寐者》等诗集,我们很自然会发现新诗的古典意识首先可以是借助古代诗词为题,但仍以现代新诗为体。比如《击壤歌》《短歌行》《将进酒》《摸鱼儿》《逍遥游》《如梦令》,等等,均是如此。实际上,不论是为题,还是为体,诗人根本上都是在用现代的、个体的、鲜活的生命重新去激活古典诗性。比如,在《短歌行》中,尽管我们所看到的不再是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但诗人所写的“晚风无须多吹,坚固早就输于了永垂不朽/渔与樵张酒庐下,笑谈已成审美疲劳”,却又引人无限深思。又如,在《将进酒》中,诗人写道:“我仍然相信,我们/可以重建一个最美的黄昏/那一刻,英雄们临水而居/所有人都默然不语/好酒代表了四散飘零/中空的酒碗代表另一个故乡。”很显然,诗人所表达的同样也不是李白那种豪气满满的“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而是投射了当下人更为细腻的自我感知。再如,在散文诗集《无限颂》中,诗人将《击壤歌》置于“孤独者”的篇章中。在诗集《假寐者》中,诗人不仅将“击壤歌”作为卷名,而且还专以“击壤歌”为题名作诗。诗中写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从不久违的日出与日落,它与我们有些迥异。”而诗歌以“击壤,击壤。彼世何世兮?”的设问作结尾。可见,这首《击壤歌》在原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基础上极大丰富了意象,提升了诗境,焕发出了全新的审美活力。
从古代诗词中提取诗意也是赵目珍探索新诗写作路径之一。简而言之,他选择从古诗词中撷取核心意象或部分关键性词语,并将这种古典意象与现代思维加以熔铸和重塑,从而产生新的诗味和诗意。比如《乌鹊记》中,“一定要南飞吗?南,不过是一个虚置的方位。”这其中既隐含着诗人对那些南飞的乌鹊何去何从的诘问,又有着他对乌鹊“万物得时,吾生行休”的确证。又如《山居诗》中“飞鸟从遥远的时空来逃避浩劫”,“它们不过是并行于水上的两只野鸭/幽冷的水晶之夜,坠入荒诞的神化。”还有《打开陶渊明的十二种方式》,一是“你向澄明奔走”,二是“你幽深的雅志,正荡涤于青云”,三是“宝剑也未曾失去你桀骜的象征”,四是“你的高蹈到底该如何措置?”五是“你为何要化身渔人,去寻一个生前梦后的烟霞之地?”……更有“聊乘化以归尽。你的别离正接上王子猷当年的弥天大雪。”在“我”与“你”的对话中,诗人用新诗的形式释放或者阐释了古代诗词中未曾为人所关注的信息,接通并赋予了传统诗学更多样的内涵。
不论是取意,还是借题,或是改写,毫无疑问都是新诗“现代性”与“古典性”互动的表现。像现代的地铁就这样进入诗歌:“一段旅程/其实就是一段喘息/我们并非懂得许多世故/出了站台,茫然四顾/然后驻足。若有所思:/啊!好一段混沌而又充满了/可能的归途。”令人质疑的是,现代诗歌的古典意识是否意味着是背离了新诗的发展路径?或者说,这是诗人们个性丧失,走向庸常的表现?诚然,新诗在百年发展历程中不可避免遇到某些困境,但都非问题的关键所在。当下,以否定传统的激进姿态出场的新诗自觉不自觉认同古典诗歌的审美和艺境,恰恰在某种意义上展现出了当代年轻诗人们的个体感知和审美取向。正如郑敏所说的:“现代性包含古典性,古典性丰富现代性,似乎是今后中国诗歌创新之路。”[3]从这一意义上来讲,现代意识与古典意识在全新的时空中得以叠加和变奏,这也正是以赵目珍为代表的青年诗人们的借古典酒杯抒现代情感,并实践着“中国诗歌创新之路”。进一步来说,赵目珍诗歌的这种古典意识,尤其是现代与古典的融合的审美特质,使得诗歌呈现出一种意蕴深远的美学倾向和文学精神。
三
在《我始终坚持诗的各种可能性》中,诗人自认:“这‘可能性’包括了诗歌在功能上的可能性,包括了诗歌在创作中出现‘好诗’的可能性,包括了读诗和解诗的可能性,以及‘诗意’无处不在的可能性。”事实上,赵目珍所说的这种“可能性”还包括了诗歌究竟“写什么”和“怎么写”的可能性。在《无限颂》的“序言”中,丛书主编更是直言,对于散文诗的态度,我们是要“摆脱‘是什么’魔咒,探索‘写什么,怎么写’”,特别是“在表现的多元性问题上,新的探索必须是我们不懈的追求。”[4]对此,我们可作出这样的判断,一方面,赵目珍自2006年开始诗歌创作时就一直在诗歌的表现形式和精神向度等方面不间断探求;另一方面,诗人在提升诗歌的宽度、广度和深度的同时力求重建诗学。
可以认定的是,赵目珍这种重建诗学的尝试首先表现在诗歌形式的创造。从诗集的分类来看,他既写诗歌又写散文诗。即便是诗歌创作,他又尝试创作寓言诗、还原诗等,践行着他所认定的“诗歌有各种各样的写法。任何写法都可以出好诗。”他的“还原诗”偏向日常生活的再现与个人情绪的传达。这里有《虚无诗》《悲伤诗》《悲欢诗》《忏悔诗》《自省诗》《忧伤诗》《不安诗》,也有《闲坐诗》《醒来诗》《同行诗》《还乡诗》《寄居诗》《宴饮诗》《静候诗》等。诗人意在让人意识到:“你要相信,弦外的真相才真正有趣/请记住你所忽略的,忘却你所专注的/有一些真实终将消泯/而我们常常还原虚假的真实//面对万物的存在,我已經决定抽身而退/前途未卜先知。”(《还原诗》)在“寓言诗”中,诗人化用并改写了“坐井观天”“惊弓之鸟”“亡羊补牢”“叶公好龙”“守株待兔”“刻舟求剑”“滥竽充数”“揠苗助长”“掩耳盗铃”“望梅止渴”“饮鸩止渴”“买椟还珠”“对牛弹琴”“杞人忧天”“庖丁解牛”等十九个寓言故事。这些诗歌似乎在告诉我们:“合二为一,通观全局/有什么呢/不过都是为了正经地活着。”(《捕蝉》)对于散文诗,他的理解别具一格:“它是独立于散文与诗之外的一种体裁”,“散文诗有它独立的精神和气质所在,这种精神和气质根植于人类性情的萧散以及诗意栖居的理想欲求。”可见,诗人对诗歌形式有着多元探索,并有个人创见。
很显然,诗歌表现形式的创新不过是外在表现,内在的还是诗学观念的更新。在《外物》中,赵目珍曾明确提出了“诗歌是存在之思向美与哲学的无限靠近”[5]的诗学观念。这一观念与郑敏主张的“诗歌与哲学是近邻”无疑是契合的。他的诗歌大多都受到哲学凝视,在感性的意象中闪现出诗思相融合的理性之光。在《无限颂》《假寐者》中,两部诗集中不同主题的对立相当明显,但诗人似乎构筑起了两个世界,一个是他自身所处的此岸世界,另一个则是他向往的彼岸世界。在一个此消彼长的年代,诗人感慨:“娱乐至死啊!话语场已被颠覆。/诗性从此消失。/无法承受的考验,风靡一时。”(《近思录》)如同施战军所指出的,赵目珍的这些诗“关乎心灵,关乎诗学;关乎生灵,关乎哲学。”可以说,诗人正是通过“诗”与“思”互动串联起两个世界,以此实现由情及理的审美转换。进言之,赵目珍诗歌的哲学沉思很大程度上显示了新世纪青年诗人的才情和智慧。
之所以由诗人的诗歌表现形式的探索拓展到诗人的诗学更新和重建,是期望进一步在更为深层的意义上观照诗人的价值指向。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暮归》《旧归途》《归途》《又是归程》《清晨,我们奔赴南山》《途中手记》等诗歌显示出赵目珍处于“低处”的“在路上”状态。具体来说,“我因生于低处而萌生野心。/无数的暗影,独立苍茫之中。”(《低处》)于是,诗人踏上了归途:“看到了安托山,我就知道了归去的方向”,“我们——潜伏了太多的欲望,已忘记了如何正确前行。”(《归途》)在归途之中,“我不能顺时穿越/我只能随地铁打发自己的归程/夕阳正在消失/风景由现到隐/当然,我也正在接近故乡/接近那些无法回避的门禁。”(《又是归程》)历经千里迢迢地跋涉,诗人“带着一阵清风,衣锦还乡”,“我想说——/第一个打破衣锦还乡的人,是勇敢的人/但如今,即将还乡/我仍然有些近乡情怯,怕对来人。”(《还乡诗(一)》)可是,面对夜深人静时,诗人“旷日持久的/异乡感,又开始起起伏伏/我的归属感,一时全部消除。/无法解释这其中的缘由,/越是解释心中就越是杂乱。”(《异乡》)应该说,这种悖论式的情感体验和哲学基质使得赵目珍的诗歌抵达了新境界和新高度。
谈及“诗性”存在的可能性,赵目珍认为:“‘诗意’无处不在,它并不依赖于语言。它就在‘存在’当中,并且时时给我们以惊喜。”我们也可以说,赵目珍的诗歌从哲学、历史、现实和个人等多维介入,既有现代和古典的融会贯通,又有传统哲学和西方美学的陶化熔铸、接续整合诗学主张并进行诗化的表达。关于这一点,确实让我们很期待,也很惊喜。同时,诗人的个体存在方式和个性化表达,那种经验、视野和才情的展示,还有自我价值的彰显,同样给人以惊喜。
参考文献
[1]赵目珍:《假寐者》,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272页.
[2]李怡:《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3]郑敏:《中国诗歌的古典与现代》,《文学评论》,1995年第6期.
[4]赵目珍:《无限颂》,北京燕山出版社2018年,第5頁.
[5]赵目珍:《外物》,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
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世纪江苏青年作家群落研究”(2018SJA0513)和2018年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资助成果。
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80后小说家的审美新质研究”(项目号:19ZWC003)阶段成果
(作者介绍:陈进武,现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和文学批评研究。发表研究论文7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