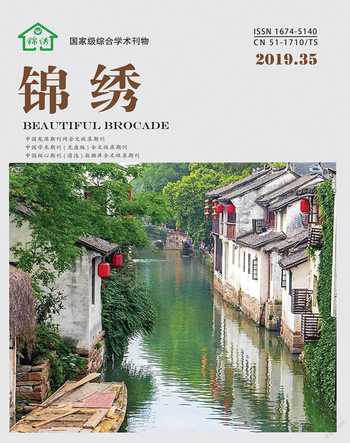少年的肩上应是草长莺飞与清风明月草长莺飞
汪祖涛
台上咿咿呀呀的唱个不停,台下座无虚席。少年的眉目透着点点星光,尘封的记忆碎片悠悠回荡在脑海……
“师傅,咱们这是去哪?是去冒险吗?爸爸妈妈怎么没有跟来?”
“傻孩子!”
众人哈哈大笑,饱经风霜脸庞透着淡淡的忧伤。不谙世事的黎初看着陌生的众人,那是他幼时第一幅画卷:颠簸的木车上,是他学艺记忆的开始。
数月之久,地势开始陡峭,车愈发颠簸。晨曦乍现,大师兄起身接替师傅的班继续赶路。黎初也赶忙起身跟着师傅学二黄和西皮的唱腔,师傅唱一句,黎初便跟着唱一句。黎初坐得比以往都端正,手势也摆的有模有样,只因昨日师傅因为唱的不好而狠狠的打了黎初的屁股,到现在还是疼得刺骨。黎初心里明白,师傅是恨铁不成钢,不像那狠心的父母,抛弃自己的那刻,一眼也不曾望向自己,手中攥着那大洋,面庞无法掩饰的喜悦。只是那时的他单纯的如同一个傻子,黎初清秀的面庞有许些狰狞,不禁苦笑。
师傅观察入微,轻抚黎初的头,默默地陪伴着他的身旁,清风和睦,路上偶尔传来梨花的香。
“小师弟,那边有河,去灌点水,路上喝,等到了西藏就不一定有水了。”
“嗯,好。”黎初迈着自己的小腿急匆匆地赶了上去。
“二师兄,师傅会京剧,那师娘也会吗?我还从来没见她唱过呢。”一双眸子炯炯有神地看着二师兄。
“哈哈哈,当然会啦!而且连师傅都自愧不如呢。”
“你可不知道,师娘是梨园的,那摆个身段,甩两下水绣,扬几声珠圆玉润的歌喉就把年轻气盛的师傅给迷住了。我听大师兄说过,当年师傅从北平到扬州表演遇见师娘,想当初师娘和师傅一见钟情,戏班子走了,师傅偷偷留了下来,戏班子发现后回来,师傅挺着胸板说要对师娘负责。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黎初摇了摇师兄的袖摆,“继续说嘛,然后怎么样?”
二师兄和三师兄便惟妙惟肖的入了戏,唱起了京戏,四师兄则当了旁白。
就这样师傅被戏班子关在了小黑屋里。
“相公,一日未见,我早已相思断肠。”后音拉得悠长,悲伤的情调让黎初浑然不知地入了戏。
“娘子,于你不能相见,我饭不得食,心依然老。”
“相公,我们双宿双飞,做一对相伴鸳鸯罢了。”
“娘子,往后余生,只伴你年华似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后来,师傅日夜不食,大病一场,戏班子以为师傅活不了多久了,便把他留在扬州。不过在师娘的悉心照料下,师傅渐渐的好了。师傅大病初愈,一堆情话说得师娘便不顾一切和他私奔。那时大师兄和你一样不过七八岁,跟个憨子一样被师傅拎着就跑,想想那场景我就想笑。
黎初听得津津有味,仿佛身处其中,戏了,回味无穷。
正值春分,天依旧寒风瑟瑟,师娘用被子裹着黎初,大家也是将衣服拉得更紧了。远处,夕阳的光辉映照广阔的大地,以一种温暖的色彩调和着衣服的冷色调。到了,真的到了……
藏族同胞也未曾见过这些外族人,却友好的让黎初一行人入住,将他们的青稞酒,牛羊肉,然后又用酥油茶调了奶茶给众人。不过语言有别,弄得有些疏忽。
黎初和众人住进了藏族的民居,是一种碉房,用乱石和土筑成的房屋,墙体上厚下薄,透过窗户,雅鲁藏布江镶嵌在高山旁源远流淌,梵音悠扬地从山上飘来,犹如听着安眠曲的大自然流淌心间。匆匆忙忙地将戏曲道具,乐器安置好,便睡下了。
微光初醒,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走来,“你们是中原人!”
睡眼朦胧的黎初看到一个说话自己听得懂的藏族人,激动的站到眾人前方。
“你说话我听得懂诶!”黎初不禁凑了上去。
“哈哈哈,好灵气的娃,我小时候去过中原,不仅会中原的话,还会写一手好字,我还教过一些藏族人。”蓦地,老爷爷身后冒出了一个小姑娘,好奇的打量着这些与自己长相略有些不同的人。一双灵动的大眼睛四处流转,眼神落在了与她同龄的黎初身上。四目相视,黎初无处安放的小手有些不知所措了。二师兄悄悄的推了黎初,黎初脚步不稳,跌倒之际小女孩将他扶住。抬首,女孩赠他一抹笑颜,默契的眼神无须多说一句话,女孩牵着黎初的手,冲出房屋,迎面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天气还未褪去寒气,远方便有了一望无际的绿,看看自己的身边却仅有寥寥几根。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景象果真不是虚构!
俩人肩并着肩相依着坐在一起,“你……字?”
“你是说名字?我叫黎初,黎初的黎,黎初的初!”
“黎初,哈哈哈,……意思。我叫次仁洛桑。”
天际云雾乍破,几只莺徐徐掠过,小巧玲珑,在空中发出几声清脆的鸟啼。次仁洛桑干净的眸子倒影着飞翔的莺儿,仿若这世界都在她的眼睛里。黎初想要帮次仁洛桑把莺抓来,诺大的草原上寻觅着,一蹦一跳地努力追赶,次仁洛桑拉着他的衣袖示意她不要莺儿,莺很可爱。蹩脚的语言从她的口中溢出仿佛音乐一般动听,黎初静静地看着,忘记了岁月的婉转与流逝。
天如同台上的帘幕一般缓缓地闭合,疯了一天的黎初和次仁洛桑依在椅背上,急促地呼着气,气像白雾一样交融,消散。藏族人民也都找了座,静候开始。黎初倒是有些担忧,他们听不懂只能看真的能欣赏到戏曲的艺术之美吗?不过师兄师傅他们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黎初心中莫名有了些许底气。
帘幕缝隙间透着光亮,光亮以一条线向外扩展,台上悠悠唱腔骤然开始。那女子举止娴花映水,弱柳扶风,恰似那宛在天宫的仙子,在高台之上挥舞着洁白的衣襟。俩个男子在旁附和,领着佳人四处游览。女子的双眸秋波灵动,手眼身法步十分到位,炉火纯青,生动传神,渲染着美感,让不懂戏曲的藏族人体会到艺术之美!国粹生香,余音绕梁,宛转悠扬的曲调连绵不绝,“那冰轮离海岛,乾坤分外明,皓月当空,恰便似嫦娥离月宫,奴似嫦娥离月宫……”“好一似嫦娥下九重,清清冷落在广寒宫。”结合着汉调以徽剧的精髓,唱出了京剧的魂魄!女子扮相是人间雍容却有一种超脱凡间女子的媚态。藏族人民不禁侧目,默叹,以为绝妙。
六宫粉黛三千转,三千宠爱一身专。是《贵妃醉酒》!
沉浸在戏曲中的次仁洛桑蓦地惊醒,目光留在了黎初身上,这个清秀的男孩却并未发觉,依旧沉浸在戏中,久久涌现在脑海中,难以忘怀!
“你也要上场吗,黎初。”
“不行呢,我加入戏班才几个月,不过我以后一定会成为京剧大师的,像梅兰芳一样开创自己的京剧表现体系!”
“梅兰芳?可爷爷说过京剧最厉害的是同光十三绝!”
“梅兰芳是现代京剧大师,他很年轻,也很伟大!”黎初的脸庞上满是憧憬,眸子炯炯有神。
次仁洛桑提着小手,俩指朝天,“等你成了京剧大师,我去看你表演,我发誓!”
“嗯!我一定会成为大师的!”
春风十里,少年的心事随着这片草原、莺啼、诺言悄然萌发在这方阡陌。
清风明月
别了,西藏。
别了,承载他的稚嫩与牵挂的高原……
黎初牵匹瘦马,踽踽而行,身后西坠的残阳,不舍地目送着那抹消瘦却又挺拔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
她还是迟了……
“黎初!”一个落落大方而又皓齿明眸的女孩蓦地扑向黎初,泪水打湿了黎初的肩膀,黎初沉默着,泪水在眸子中打转不敢轻易落下。
次仁洛桑哽咽着,“你真的要走了吗?不能再留下一些日子……”
“现有国,后有家,原来来到西藏本就是为了避免战争毁坏京剧艺术,但现在国家都岌岌可危,我们必须回去,能做一点是一点!”
“洛桑。”
“嗯?”
“我最后再给你扎一次头发吧!”
黎初轻轻扶起次仁洛桑的青丝华发,散发的清香有扑朔迷离之感,似一层厚密的细软的黑丝璎珞似的遮住她的脖子,轻纱一样垂在肩上。黎初笨拙的将头发拉直,一圈一圈地编好,却又因为一个失手,发梢松动,头发散了下来。黎初尴尬地挠了挠头。
“你手还是那么笨,不扎了,你静心赶路吧,你师父师兄还在等你。”
“那我走了,你要好好的。”
“黎初,我以后要是见到你,你再为我扎一次头发好吗?”
“好!”黎初掷地有声的说。
一行人骑着马,拖着货物再一次踏上这条归路。“师傅,要是小师弟像你一样,估计就留在那大草原上八头驴也拖不回来了。”大师兄搂着黎初调侃。“七年了,小师弟都成帅小伙了,咱们也都二十出头了,好怀恋北平的烤鸭啊!”二师兄躺着木车上看着天空。“你个没出息的,咱们去为抗日军队演出增增士气,你到光想着别的了。”师娘猛地拍了二师兄的大腿,四师兄笑得前赴后继,“哈哈,二哥就是欠揍,还有啊,回去不能叫北平了,我听说北平改为北京啦,得叫北京烤鸭。”大家欢欢喜喜,而师傅一直沉默着,“黎初,好好学戏,别忘了和那姑娘的诺言,大丈夫要信守承诺!”“嗯!”
1943年初,北方的寒流还未完全褪去,戏楼中已然多了几分热闹的气氛。黎初在台上咿咿呀呀地唱着《霸王别姬》,唱念做打,在胡琴的声声曲调下,时而铿锵有力,时而婉转悠扬,时而雄浑端缘,时而清脆高昂。配合着形与神,一首京曲唱出霸王的不屈高昂。戏落幕,台下一阵掌声经久不息。
“请问,是黎先生吗?这里有您的信。”
“信?对,我是黎先生,这上面写的是我的名字。”黎初拿着信件,拆封开来:黎初,好久不见,想我了吗?你肯定想了。爷爷同意我来找你了,我可是费了九六二虎之力呢,我现在中文学了许久,不会像以前那么稀里糊涂啦!你可得好好招待我,我这次来就不回去啦,我要陪着你,跟你一起去面对你说的战争。你可别忘了你要成为京剧大师的!我不久后就要赶来验收成果,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哦。不说了,我得赶紧上路了。
黎初的脸庞透着红润,微微上扬的嘴角似乎有说不完的欢欣,小心翼翼地将信叠好,放进柜子里。
夜里,黎初辗转反侧无法入睡,起身,独自一人坐在院中。遥望,夜空星星点点,宛若有条璀璨星河连接织女星与牛郎星,月亮悄悄地圆满,黎初蓦地想起今儿已到了正月十五,明月皎洁如玉,庭院盈满了月辉,手指间似乎还有着水一般的触觉。想着很快能和次仁洛桑相聚,顫颤的心满是期待,清风拂过,几片竹叶落下,黎初兴致一起,提笔写了一封信留给次仁洛桑……
有一些日子了,黎初还没盼到次仁洛桑,在门前踱步。一个身穿军衣的人停在门前,黎初赶忙上前迎接。
“您是黎初先生吗?”军官脸色很难看。
“对,我是,有什么事吗?”
“我们突击队在前线发现一女子中枪,失血过多,濒死之际一直在喊你的名字。”
黎初双手颤抖,青筋暴起,近乎恳求的说道“次仁洛桑!她没事吧,她没事吧!你们救了她,对不对?”
“先生,您不要激动,您口中的女子已经失血过多,离世了,她的尸体我们放在门外了。”
黎初匍匐在地上,失声痛哭……
黎初艰难的爬向门外,跪在她的身旁,“次仁洛桑我记得你说过我要为你再梳扎一次头发,我记得,你起来好不好……”黎初用着颤抖的双手,一把一把地将头发攥紧,像从前一样一圈一圈地交叉编起,泪珠顺着发梢延伸,头发扎好了,可她依旧闭着眼睛,面无表情。这是黎初第一次为她扎发成功,可她却不在了……
次仁洛桑离世后,他心已亡,改名黎末,来祭悼死去的爱情。
一九四六年正月十五,月挂中天,清风徐徐地拂过少年的衣袖,黎末从回忆中惊醒,台下坐无虚席,少年的他眉目星星点点,身穿蓝衣遥对着一件空落落的红衣,咿咿呀呀地唱着,眸中仿佛有抹熟悉的倩影,少年英气,一袭长袍,唱尽俗世红尘,演绎悲欢离合。“人生不易难相和,生死茫茫两相隔,曾是相配莺飞双,天道无情又何妨,怎道是金风玉露,怎感言一生相许……”台上唱尽年少情长。那一刻,风不吹,云不走,日月共生,天地恒古。
戏终,少年咳出一口鲜血,缓缓倒下……
三月后,在打扫遗物时,柜中留着一封信,上面写着收件人:次仁洛桑。师父和师兄们不知次仁洛桑早已不在人世,于是将信寄往西藏。
又是一年春,草原上重新萌发了青草,送信人将信交给老爷爷,上面写着1943年赠次仁洛桑。打开信,上面写着:洛桑,你说的对,我常常想你,也在梦中梦到你好多次,还是那样广阔无垠的草原,莺儿踽踽飞着,环绕着我们,我给你编着头发,那时总是编不好,你便怪我手笨,然后就去找爷爷给你编。现在可就不一样了,我天天去看着师傅给师娘编头发,学了很多,这次再也不会手笨啦。我还要唱京剧给你听,师傅说了我现在要比他老人家还要厉害呢,不出几年我也可以成为像梅兰芳一样的京剧大师,等你到了,我在台上,你在台下,我只唱于你一人听,等你。
山上飘来梵音,老人安静地躺着椅上,将信夹在洛桑的日记本里,喃喃自语:“丫头,现在好了,他那么爱你,估计已经成家了吧,不回来看我老头也没关系,你只要幸福就好……”
一场戏曲,道尽锦瑟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