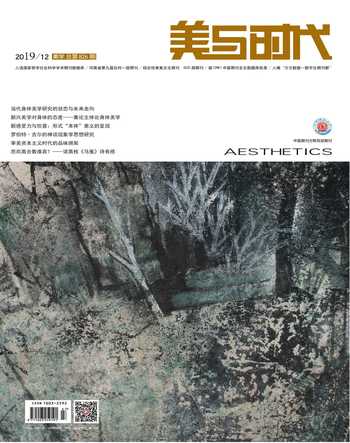《诗经·郑风》恋歌的情与思
摘 要:《诗经·郑风》中的婚恋情歌或描写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和坦率表白,或描写幽期密约的兴奋和邂逅相遇的喜悦,或描写真诚的相爱和刻骨的相思,或描写失恋的痛苦和爱情受阻的哀怨。可以说,这些诗作基本上反映了那一时代郑国青年男女追求爱情的全过程。这些贯穿婚恋与爱情之主题的歌咏,无疑是郑地民俗风情和民众普通人性的典型呈现。
关键词:诗经;郑风;恋歌;情思
《诗经·郑风》共21篇作品,有5篇主要是反映郑国贵族政治生活的,蕴含着好贤尚直、崇武尚力的主题,展现郑人的政治意识和族性特质;有16篇是反映郑国民众的婚恋生活的,贯通着婚恋与爱情的主题,展现着郑国民众的普通人性和郑地丰厚的民俗风情。
《郑风》多情歌,学者普遍认为与郑国所处的地理位置、风俗习惯及审美风尚密切相关。从地理位置而言,东迁以后的郑国,其所处之地为旧殷商文化的中心区;从国民构成而言,既有深受殷商文化影响的原住民——“商人”,又有随郑桓父子东迁而入住繁衍的外来民。史上“郑卫”合称由来已久,重要原因就在于郑卫之地同是殷商旧地,同受殷商文化的沾溉,在民情风俗上具有许多相似之处。《史记·货殖列传》说:“郑卫俗与赵相类。”同传并记中山之俗曰:“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馀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忼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治,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琴,跕屣,游媚富贵,入后宫,遍诸侯。”[1]又有《吕氏春秋·先识览》载:“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切倚,固无休息。”[2]从中约略可知这几个诸侯国民众思想观念较少受周代礼制的束缚,男女之间的交往相对自由。《汉书·地理志》记述郑、卫之俗:“土陿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3]1652“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故俗称郑卫之音。”[3]1665明确地指出郑卫之地的风俗特质。“亟聚会”犹言“屡聚会”①,郑卫之地一年中男女之间举行多次聚会,大可想见其“声色生焉”之盛况了。
从《郑风》情歌所涉及的场景来看,郑国男女聚会的地点主要是都城的东门附近及东门之外的溱洧河岸。东门附近的聚会应是与郑国的社稷等祭祀活动相关,而溱洧河岸的聚会则主要与郑人的祓禊活动相关。从时间上说,郑国的这两个宗教与民俗活动的举行可能在同年中相同或相近的时段,亦可能在不同的季节。
《东门之墠》为郑国都邑之女子向心上人表达爱情的恋歌,首章:“东门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则迩,其人甚远。”先言物事,次言人事,曲传心事,对心上人的思念之情喷薄欲出。二章:“东门之栗,有践家室。岂不尔思,子不我即!”直赋物事与心事,思而不得见,不得见而愈思,竟至于心生埋怨了。这言简意赅的短歌,表达出女子对心上人的思之切和情之至。《出其东门》是心有所属的男子自抒其对爱情专一的心曲。首章:“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二章:“出其闉闍,有女如荼。虽则如荼,匪我思且。缟衣茹藘,聊可与娱。”诗人巧妙地运用比喻、借代、对比烘托的手法直赋所见所思,于直说中见出诗人对爱情的坦率真挚和深情专一。
《东门之墠》和《出其东门》两首作品,当是在郑国社稷祭祀活动之后青年男女聚散游乐时的歌唱。郭晋稀认为此两篇为“所咏只是一事的”组诗:“《东门之墠》所说的东门墠阪,即是东郊原野;从郑东门而出的《出其东门》,当然也到了东郊原野。两篇所写:一个是来自东门女子,一个是本在东郊居住的男子。这个女子东风无主,春怀正炽,所以求爱于男子。没有料到这个男子家储碧玉,业已成婚。《东门之墠》是女子所唱,怨恨男子的漠然寡情。《出其东门》则是男子所答,说明自己室中有妇,所以落花有意,流水无情。”[4]40这是一个独到的见解,但这种巧妙的推想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出其东门》为已婚男子之作,是为了表达自己对妻子的专情。
然而笔者认为,《郑风》中的所有情歌都是未婚男女表达爱恋之作,《出其东门》中的男子也同样如此,他所专情的“缟衣綦巾”“缟衣茹藘”的女子只是一个衣着朴素的未婚姑娘。从诗中“出其东门,有女如云”“有女如荼”来看,与《东门之墠》没有对应性,两者不当存在一唱一答的关系。因此,两者应是各自独立的。不过从诗歌产生的背景来看,倒是可以归为“东门”组诗。此外,《子衿》一诗虽未明言“东门”,但从诗中所言“城阙”来推测,此诗很可能也是以东门聚会游乐场景为背景的。首章云“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二章云“縱我不往,子宁不来”,末章云“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从内容上看,此诗和《东门之墠》一样,因对心上人强烈的思念却不得以相见,这个多情的女子又爱又怨、以歌传情,表达心中热切的爱恋。
东门之外的溱洧河岸,是郑国青年男女聚会游乐的又一场所。在溱洧河边的歌唱是以郑国祓禊习俗为背景的,这已是普遍的共识。《溱洧》之诗,诗两章的前一部分,都是对郑俗上巳节男女群聚的热闹场面的集中描述。而各章的后八句,则是具体叙述参加上巳节庆活动的士女相约游玩同乐的言行与事件始末。此诗反映了春秋时代在仲春祓禊之时,郑国男女自由相会相欢的民俗,反映了向往自由恋爱的民情。诗中言“维士与女,伊其相谑”“维士与女,伊其将谑”,其实是对欢会中对歌传情活动的描述。
《萚兮》《山有扶苏》《狡童》《褰裳》就是一组“伊其相谑”的欢歌。在“士与女,殷其盈矣”的群欢场面中,热情似火的女子率先邀歌:“萚兮萚兮,风其吹女(汝)。叔兮伯兮,倡予和汝。/萚兮萚兮,风其漂女(汝)。”可以想象,这多情的歌声定会撩起众多青年男子的歌喉,你来我往,响彻云霄。或许是哪位男子的鲁莽挑逗激起了辣妹子的娇嗔:“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山有乔松,隰有游龙。不见子充,乃见狡童。”或许是这样的娇嗔让那憨嗤嗤的男子一时无法接受,竟变得垂头丧气、沉默不语了。那本已对他动心的女子便一改泼辣盛气,深情地唱出心声,企望其知晓自己的爱意:“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怎奈如此的柔情竟然不能消解那男子的心伤,他不但不能谅解她的娇嗔,而且无视她的一番真情。柔情而烈性的女子就不再客气了,她傲然高歌:“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思我,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思我,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在一连环颇具戏剧性的组歌中,彰显出歌者在追求爱情时敢爱敢恨、自由、自主、自信的人格精神。
郭晋稀在《风诗蠡测初篇》第十条“组诗初探”说:“我认为民风本来有很多组诗,由于入选,有所删节,加之入选以后,编次几经改动,所以后人认为各自成篇,中间并无有机联系。如果仔细推敲,有些组诗是依旧保存了下来。”[4]38他指出:“《山有扶苏》《狡童》《褰裳》《溱洧》就是一组诗。《山有扶苏》《狡童》《褰裳》三篇,通过狡童或狂童这个人物,贯串组织起来,连成一气。《褰裳》篇里,提出了‘子惠思我’,便‘褰裳涉溱’与‘涉洧’,而《溱洧》一篇,真是写的溱洧之游。所以四篇合成一组,是相当清楚的。”[4]39此论诚为卓见。不过笔者认为,《萚兮》一诗宜归入这一组诗,其中的关联如上所述②。
在对歌求爱中有的男女未成佳愿,有的男女则如愿以偿。《风雨》一诗是女子向心仪男子热情示爱,唱出其心中的喜悦:“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风雨潇潇,鸡鸣胶胶。即见君子,云胡不瘳!/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她的浓情“君子”心领神会,她的美丽“君子”真心赏爱,他便用真诚的赞美回报于她,歌曰:“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臧(藏)!”(《野有蔓草》)彼此的心灵交汇、一见钟情,让双方获得了性的愉悦和爱的满足。《风雨》和《野有蔓草》虽然未必存在一唱一和的对应关系,但若将两诗牵合起来品味,两者存在情事上的内在关联和暗相呼应,未尝不是一种可能。从这个角度上说,《风雨》与《野有蔓草》二诗,共同演绎了春秋时代郑国民众中“君子”与“美人”之间性与爱的欢歌。
《女曰鸡鸣》和《有女同车》是表现爱情进展顺利的作品。前者选择一个生活的片断,“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记述一对男女过上了同居生活:在一个星光璀璨、行将破晓的美好时分,女促男兴,射凫取雁。二章是女子承前所言而自述心愿:“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男子感其情意,答之曰:“知子之来(勑)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情歌互答,恩爱有加,以佩相赠,情定终身。闻一多《风诗类钞》谓此诗“乐新婚也”[5],似不确,细味诗意,应是“乐同居,盼新婚”也。《有女同车》是男子深情回味与心上人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显然,他对心上人非常满意,内心充满喜悦,热情地赞美她的美貌和品性,并唱出了心中的誓言。
如愿以偿的男女,在奔往爱情的归宿——婚姻道路上却又有着不一样的遭遇。有的能够以物定情,以心为誓,琴瑟之乐可期,婚姻之日可待(如《女曰鸡鸣》和《有女同车》所体现的);有的却受到流言的中伤、或遭遇情人的变心,或受到家人的干涉、礼法观念的束缚,爱情可能得而复失,婚姻仍旧遥遥无期。《扬之水》当是一首因谗言离间导致爱情岌岌可危、女子努力挽救爱情的诗,她喻之以物、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扬之水,不流束楚。终鲜兄弟,维予与女。无信人之言,人实迋女!/扬之水,不流束薪。终鲜兄弟,维予二人。无信人之言,人实不信!”愤恨之下是女子的恳切与坚贞。《遵大路》可能是一个遭遇情人变心的女子为挽回爱情所做出的哀求,亦可能是与《扬之水》主人公有着同样遭遇的女子对心爱之人的恳告(两诗甚至有可能为同一作者):“遵大路兮,掺执子之祛兮。无我恶兮,不寁故也!/遵大路兮,掺执子之手兮。无我魗兮,不寁好也!”缠绵悱恻之情、忧愁哀怨之心,在简短的倾诉中昭然外露、感人至深。
《将仲子》和《丰》当属于因家人干涉、礼法观念束缚导致爱情受阻的作品。《将仲子》是一首女子唱给心上人的情歌,面对热烈追求她的“仲子”,内心矛盾不安。一方面她对“仲子”满怀挚爱;另一方面又承受着舆论压力,害怕父母兄弟的责难,畏惧别人的闲言碎语,使得她不能同意“仲子”逾墙幽会的鲁莽行动。因此她对“仲子”婉言规劝以表心曲:“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二章云:“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三章云:“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她强调自己并不是不爱他,而是现实中存在种种羁绊,限制着她的身心自由。《丰》诗中的“子”,曾与《将仲子》中的“仲子”一样热烈地追求他的爱情,竟至于上门提亲迎娶的故事。“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历来论者多以为追叙男子上门迎亲之事,这是合理的推想。而那女子当时则或因父母的干涉而“不送”“不将”,正如前文引戴震所言:“盖言夫俗之衰薄,婚姻而卒有变志,非男女之情,而其父母之惑也。”由于當时的“变志”并非出于本心,追求爱情获得归宿才是真心的梦想。那仍未婚配的女子,在新一次的聚会欢歌活动中,终于不再害怕父母诸兄之管束,不再畏惧人之多言。面对昔日的情人,她坦言内心的悔恨,满腔热忱地重新发出爱情的邀请,率性高歌曰:“衣锦褧衣,裳锦褧裳。叔兮伯兮,驾予与行!/裳锦褧裳,衣锦褧衣。叔兮伯兮,驾予与归!”这毫不保留的真心真意,无疑代表着郑国未婚女子的心声。爱情需要归宿,幸福的婚姻是她们最终、最真、最切的追求!
《郑风》是反映爱情生活的作品,或描写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和坦率表白;或描写幽期密约的兴奋和邂逅相遇的喜悦;或描写真诚的相爱和刻骨的相思;或描写失恋的痛苦和爱情受阻的哀怨。可以说,这些诗作基本上反映了那一时代郑国青年男女追求爱情的全过程。
注释:
①“亟”有“屡次”、“一再”之义,《玉篇·二部》:“亟,数也。”《左传·隐公元年》:“亟请于武公,公弗许。”《汉书·刑法志》:“于是师旅亟动,百姓罷敝。”颜师古《注》:“亟,屡也。”
②郭晋稀认为:“《兮》与《丰》,两篇也成一组。《兮》诗云:‘叔兮伯兮,倡、予和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丰》诗则说:‘叔兮伯兮,驾、予与行’,‘叔兮伯兮,驾、予与归’。把这些句子细味起来,两诗的关系也就清楚了。”对此笔者并不认同,而认为《丰》与《将仲子》在用词和表意上的关联更为密切,宜归为一组。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3263.
[2]许维.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国书店,1985.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郭晋稀.诗经蠡测[M].成都:巴蜀书社,2006.
[5]闻一多.风诗类钞一[M]//闻一多全集(第四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520.
作者简介:刘挺颂,博士,肇庆学院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先秦文学与诗礼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