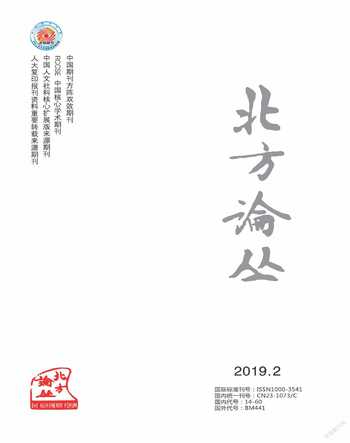怪诞叙事之惑
[摘要]伊丽莎白·乔利是驰名世界的澳大利亚女作家,其怪诞的创作风格一直是评论界热议的主题。从乔利的叙事风格上探索其怪诞的根源,与澳大利亚现实主义写实叙事理论相背,乔利的怪诞叙事风格关注人的心理乱象、人们超现实的欲望和人对传统价值观的僭越,所采用的碎片化、虚实交错和悖谬的手法,意在引起读者对自我与社会、现实与想象、传统与价值重建等三对关系的叩问,思考在复杂多元的世界重建社会规则和道德约束。
[关键词]伊丽莎白·乔利;怪诞;叙事
[中图分类号]1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9)02-0083-07
Confusion on Grotesque
Misunderstanding on Elizabeth Jolley1 s Multiple Narrations
LIANG Zhong - xian
(Mudanjiang Normal College, Mudanjiang 157012, China)
Abstract :Elizabeth Jolley ( 1923 - 2007) is a world - famous Australian woman author, whose Grotesque writing style had been the hot topic among critics. This paper manages to explore the hidden reasons behind, concluding that Jolley * s difference lies in that she took postmodernist narrative theories asthe guiding of her writing skills, which goes the opposite from the Australian modernist style. Focusing on peoples* psychological confusion, the super — realist desiresas well as moreself — centered sense of worth, she employs fragmentation, intersecting of fact and fiction, and paradox, in order toquestion more abou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elf and society, reality and imagination, tradition and reconstruction.
Key words:Elizabeth Jolley; Grotesque; Narration
20世纪前半叶,澳大利亚文学致力于建立独立的民族文化身份,坚定维护民族主义文学的立场。“在澳大利亚文学史上,劳森[Lawson]起着一种承先启后的作用。自他而始,澳大利亚文学完全跳出了英国文学的藩篱,具有了自己的民族特色,从而走向成熟”[1](p76)。著名的民族主义女作家迈尔斯·弗IS克林(MilesFranklin,1879—1954)把民族主义文学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她坚决主张表现澳大利亚地方色彩、发展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文学。她曾致信时任澳大利亚总理奇弗利[BenChifley]说:‘没有我们自己的文学,我们就是哑巴。在当今这个不安宁的世界,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自己的解释,既向外部世界也向我们自己为此,她设立了“迈尔斯·弗兰克林奖”用于奖励澳大利亚本土的作家。此后,涌现出众多民族主义作家。他们力图摆脱对欧洲文学的模仿,把澳大利亚文学从帝国叙事转变为澳大利亚民族叙事。他们热爱澳大利亚这块土地,讴歌澳洲民族精神,创作出以现实主义手法为主,以表现丛林、牧场、城镇、矿山等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塑造了具有粗彳广、豪爽、幽默、乐观的典型民族性格烙印的文学人物,努力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持文学的民族文化独特性。I960年代以后,澳大利亚文学在前半叶形成的突出主题和传统,已经实现了本民族文學精神自我定义的关键一步。文学作品中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人与澳大利亚特有的荒野、平原、山岳、丛林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他们特有的丛林生活,以及他们与严酷的自然环境作斗争的欢乐与痛苦,豪迈与坚强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文学的象征。尽管这种民族主义文学的历史不长,但在渴盼确定的民族身份的澳洲人那里,这种文学已经成为民族主义的里程碑。文学界有理由相信,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文学应该坚定地沿着这个文学传统走下去。
澳大利亚文学界普遍盛行写实文风之时,怀特(PatrickWhite,1912—1990)以大相径庭的写作方法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1973年)。继而,伊莎白·乔利(ElizabethJolley,1923—2007)的作品出版了,她不描写丛林故事(bushstories),不书写澳大利亚英雄,也不体现伙伴情谊(mate-ship),更不用现实主义手法,这种超越民族认同的叙事模式给评论界带来的不仅是困惑,还有反感和排斥。尽管她的短篇小说受到了例如《西风》期刊的好评,欣赏她的独特声音与富有个性的创作,但她多数作品与澳大利亚人的文学趣味还有相当的距离。在I960年代,乔利的稿件就由于其怪异的叙事风格遭到了奥古斯和罗宾逊出版社(AugUSandRobinson)总编毕阿特丽丝.达维丝(BeatriceDavis)的拒稿:退稿彳g上写着乔利精神错乱,需要心理帮助。1983年,《斯科比先生的谜语》(MrSco6ie’提名迈尔斯.弗兰克奖时,又一次被达维斯否决。乔利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银鬃马》1980)出版时,就受到了批评界的垢病:“这个人神经出了问题,应该去看医生。”[3](plW>)®海伦·丹尼尔(HelenDaniel)则认为:“作为乔利第一部发表的小说,《银鬃马》令人失望地晕头晕脑,无精打采,堆砌了一堆无用的东西。”[4](pW)笔者认为,伊丽莎白·乔利之所以引起广泛争议,是由于她的作品突破了传统叙事上的有机性和严密性,解构了传统价值上的民族文学的典型形象,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对象。她以后现代的叙事手法如碎片叙事映照后现代人心理的凌乱无序、以虚实交错展现想象与现实的交织、以悖谬冲突展现传统价值与现代人欲望之间的矛盾冲突。
一、碎片叙事映照无序现实
经典的叙事模式追求线性叙事的规则,凡是作品都会有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如同设计好的程序一样,每一个步骤都为下一个步骤做了铺垫。每个步骤之间是线性的发展逻辑,是构成作品整体不可缺少的一环。澳大利亚民族文学倡导的就是传统叙事,作品专注于叙事结构的整体性、有机性和严密性,但世界已进人一个分工无限细致、秩序被打破、理性让步于非理性时代,人类的生活充满着碎片,逻辑性和必然性已然不复存在。传统文学沉溺于对现实的真实描写已经无法满足时代对于文学的要求,所以,怀特就把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揶揄为“沉闷的新闻体现实主义的物”[1](p'78)。后现代文学在创造新的文学表现手法方面,致力于表现人们对自我的关注,叙事更重视读者的体验,情节表现更致力于创造思绪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游弋,也体现为意识在回忆和想象中反观自身的跳跃。
乔利80年代出版的小说多数都是这种内省式叙事,作品中主要运用非线性叙事方法,各部分之间毫无铺垫可循。比如,运用意识流手法表现时空倒错,常常把叙事的焦点聚焦在过去与现在交替瞬间,表现现时与未来之间的割裂,故事完全没有明显的延续和连贯,一切都在跳跃和流动,犹如意识的碎片。那些荒诞离奇的情节、怪异扭曲的人物性格、破碎混乱的时空交错、完全是违反常规的叙事结构。读者难以判断故事从何开始,到何处结束。在这一点上,妮娜认为,乔利是一位与弗吉尼亚·伍尔夫一样真诚和智慧的作家[5]。她的很多小说一开篇就展现了女性话语的非线性文本空间。
(一)以碎片化作为手段,书写人们的思绪飞扬
乔利的故事没有明显的目的性,情节与情节之间、事件与事件之间错综复杂,毫无头绪。以这种方式,她试图在澳大利亚文学的集体意识话语中抽离出个体意识的表达和言说,以表达个体在混乱的世界里紊乱飞扬的心理思绪。在她的三部曲《我父親的月亮》(MyFather’sMoon,1989)、《陋屋热》(仏“&哪,1990)和《乔治家的妻子》Geodes’W货,1993)中,主人公维拉·莱特(VeraRight)以回忆跳跃的方式回忆自己上学、护士实习和未婚母亲的生活片段,故事所披露的现代生活,就好像发生在遥远距离以外的事情,读者很难判断故事里各个情节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时间碎片化、话语碎片化、情节碎片化以及思维的碎片化,读者感受到的是叙述者时断时续的叙事,思维忽前忽后的漂移;读者需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把毫不连贯的片段通过一系列的短故事,在头脑中重新整合为有助于理解的故事线索。书中大多数事件都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之中或之后,但是作者的讲述并没有按照“前、中、后”的发生顺序。其思绪在不同阶段中飞来飞去,一会儿表现二战战场撤退的伤病员,一会儿又表现犹太人的逃亡,再一会儿就是战争导致的人格破碎和心理疾患。二战时期的生活背景,如电视机、茶歇舞和社区生活里神秘的宗教派别活动都是通过飞舞的思绪凌乱地暗示,而不是明确地表述出来。读者能明显感觉到事件和事件之间时常有时序上的突然漂移,即叙事上表现出快速的语气迁移,青春躁动中蕴含紧张的陶醉,叙事上作者刻意保持着距离,似乎在刻意远距离观察和分析莱特青年期的交错遭遇[6](pll3)。凡此种种,都表现出人们意识不受时空限制的特性,其流动性和间断性正是人们对影响自己生活的不同片段的回忆。
(二)叙事上的破碎、断续和跳跃,表达了人的错位和生活的真实
碎片化的叙事之所以没有其完整性,是因为其不需要对价值进行挖掘和求证。也正是由于其缺乏价值立意,给人的感觉类似的作品仅就叙事而叙事,甚至是文本之间的碎片化片段会不停地反复利用。乔利就善于“将先前的文本、作品、体系的片断当成自己的资料而加利用;旧的文本、作品或体系崩溃之后,其片断仍然流传于世,作为碎片而发挥影响”m(p39)。《氏部曲》之间明显存在片段的重复,情节被分解为破碎的细节和场面,叙事从一个故事片段跳跃到另一个故事片段的现象。这种时间的跳跃、倒转和重叠根本无法重组,同时也表现了空间的错位与分解,反映出的却是真实的生活。特别是维拉进人医院实习期间,作品揭示了作者的反战情绪以及对二战真实状况的揭露。战争导致的民族间的敌我矛盾已经反映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社会随着战争进人人人自危的状态,失去了正常的生活秩序,自我已经失去原有的生活轨道。维拉不顾一切地爱上一个已婚的医生,并成为未婚妈妈,反映了莱特内心世界极度缺乏安全感。抓住一个救命稻草,是颠沛流离的碎片化生活中人们自然的求生反映。错乱的生活秩序使人与人之间冷漠无情,真假难辨的温情自有难以抗拒的力童。现代文明的道德规则失去价值感召力,在与人潜意识欲望冲突中败下阵来,才导致主人公产生错位交叉。因此,叙事话语的错乱零散化就是现时外在秩序和人的内在秩序错乱的一种正常反应。
(三)紊乱的思维空间,彰显了人面对现实的无力
现代社会的技术革新,带来世界的多变复杂。普通人能够把握和改变的事情非常有限,就连自己的命运也难以把握。因此,没有什么是普通人能够解决的,人们无力改变现实,只能退回到内心世界。在多情而猜疑、敏感又脆弱的心理空间,信马由缰是人们唯一能够做到的事情,所有的爱恨情仇都可以在想象中实现。在《牛奶与蜂蜜》1984)中,乔利的叙事也随着雅克布的人生回忆,不断地在他的童年、青年和堕落后的中年之间移动,美好向往、自我陶醉、堕落任性,其间不断穿插着获得的希望、失去的痛苦和被剥夺的无望。他回忆了很多层面,过去年轻时代、青春时代,以及童年与父亲在家乡葡萄园一起生活的日子,甚至是母亲去世之前的孩提时期。过去的记忆通过意识过滤,使得雅克布逐渐清晰地认识到,在求生的欲望下,他只是一个被人榨干油水的摇钱树,过去的生活就是一个肥皂泡。因此,他在生活中的享受、他对爱情的追求,以及他对未来的向往,不过是一场欲望战争中的牺牲品。反映了二战后社会生活的匮乏,贵族阶层靠剥削雅克布不劳而获的现实。在人剥削人的社会中,一个毫无判断能力、毫无辨别意识、毫无招架之力的青年,希望通过求学获得美好生活就是一个幻想,只能沦落为别人搜刮金钱的工具。因此,雅克布的碎片式回忆是面对无情现实的无力,他漂泊的意识只能反映惨淡人生带给他的心理沮丧。
二、虚实交错呈现精神混乱
后现代对中心的解构反映在叙事理论上,就是从“传统的经典叙事学转向了后叙事学,从讲究统一性、整体性、逻辑性、稳定性的宏大叙事观转向了多元性、碎片性、反逻辑性、不确定性的小叙事观”[8](p35)。乔利就喜欢多元架构方式,即在故事里讲述故事,具有巴赫金的复调意味,例如,在小说《斯科比先生的谜语》《皮博迪小姐的遗产》(MissPeabody’sInheritance,1983)和《可爱的婴儿》1985)中,她都采用了小说套小说的手法,使作品中现实和虚构交错、故事人物和现实人物相混、故事情节和现实情节交融,不仅使故事中的主人公感到迷惑,就连读者也常常虚实不分。有的是两个第一人称叙事,有的是两个第三人称叙事,两位主人公复杂的内心独白、怪晃的情节、混乱的思绪相互嵌人交叉展开,展现了普通人面对困境时,常常产生的混乱精神状态。这种虚实相间的叙事一方面通过幻想、假象表现出超现实的意味;另一方面,通过有意的欺骗和蒙蔽,表现出不确定的未来走向,读者完全意识不到人物的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小说经常混淆真实和虚构,幻想与事实,实际上是自我疗伤的一种慰藉,如同心理治疗,用虚构填补空白,用幻想填补缺失。
(一)虚实交错反映了人们对未来的内心焦虑
唐敏认为:“具体感受到的意象为‘实’,反之,抽象的情思为‘虚”’[9](p'257),似乎是说,具体意象为形象思维,而抽象情思为抽象思维。但实际上,后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实有可能是虚,而虚有可能表现为实。恰如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实一体,难以辨别。比如,在《可爱的婴儿》中,主人公艾尔玛·波姬(MissAlmaPorch)小姐为了赚取生活费和积累写作素材,应聘了一个暑期学校。在给校长的第五封信里明确表明:“我的课程完全是文学的,只与人类的冲突和冲突的解决有关,而且没有过分的商业或政治口气。”[W]7)但在暑期学校所感到的是扑面而来的商业化气息,校长把她的作品当作赚钱的工具。她受聘来指导剧本排练,想不到却让她用自己尚未完成的小说当脚本。减肥女士们并不在意精神营养,她们陶醉于波姬创作的故事中,并把生活与故事中的人物混淆起来。分不清什么是现实,什么是虚构,就连读者也分不清了。影响人物命运的主要事件基本都被切割成许多“碎片”,分散在小说的不同章节里。这些事件发生时,我们只能知道它们的某一个片断,其他片断则在以后的章节里通过其他人物的回忆或谈话有意或无意地展示出来。这一切都超出了波姬的想象,她“完全的文学”遭遇到一点也不文学的陷害。正如丹尼尔(Daniel)所指出:“由于荒谬之下的可怖现实主义,整部小说就是一个作家的噩梦。”[11](p13)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乔利突然在《可爱的婴儿》故事的结尾告诉读者,故事中所发生的一切不过是波姬小姐在公共汽车上所做的一个梦。弗洛伊德认为,梦是人受压抑的无意识表现,而所谓受压抑的无意识,就是一种被压抑的精神状态。它表现了波姬小姐面对新的工作、未知的生活氛围、陌生的共事人群时,产生强烈的身份焦虑。小说对未来的展望與惧怕以虚实交错的形式宣泄出来,虽然让人难以捉摸,但展现了观念与本能、潜意识及梦相交融的人类深层心理的形象世界。
(二)以虚代实暗示出人格分裂
把想象当成现实,把虚构的故事当成真实,在虚与实中混淆界限,辨不清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认识可以反作用于现实。乔利结合后现代文学叙事理论,在创作中巧用了意识流手法拓展了精神叙事的空间,表现出后现代人碎片化的精神分裂状态。《皮博迪小姐的遗产》有多个叙事者,但所有的叙事者都不可靠。乔利以小说套小说的结构讲述了三个不同的故事一样——霍普韦尔(Hopewell)信中讲述的是自己在澳大利亚的故事,多罗丝(Dorothy)所向往的是自己对澳大利亚这个新世界,而霍普韦尔的小说里的女校长桑恩(Thome)则表现了三个中年未婚妇女在公众场合令人尊敬的举止风度但私下里却逾越道德底线的龌龊行为。霍普威尔把自己正在写的小说,一章一章地寄给皮博迪小姐。当多罗丝·皮博迪阅读和重读这部小说时,她感觉自己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即一个自由、浪漫和激情的世界。她渐渐开始以为故事是真实的。在这个世界里没有她所遭遇的清规戒律,也没有她所遇到的对青春的压抑。小说中,“新(澳大利亚)”和“旧(英国)”两个世界不同话语的相互碰撞、相互冲突带给皮博迪小姐的观念冲击力,彻底击垮了皮博迪对现实世界的信心,她把现实与想象的世界混淆,不仅开始按小说的话语改变自己,还试图把书中的话语搬到现实中。凡是在小说中读到的,她都好奇地想在现实中切身地去实践。当幻想冲击了她自己的生活时,她的行为开始变得反常,与以往闺中小姐不同,她开始醉酒并胡闹。结果,连她的上司贝恩斯(Bains)先生都以为她精神错乱,给她放了三个月的假。这实际上是以想象代替现实、以幻觉作为追求的人格分裂。
(三)实中有虚揭示心理错乱
乔利善于运用艺术的超现实手法,僭越一切现实中的理性和逻辑,在虚构的世界里自由地发挥想象力,创造力,使怪异的气氛一直游荡在故事中。乔利的迈尔斯·富5克林奖(MilesFranklinAward)作品《井》(77ieWe//,1986)中,主人公赫丝特·哈拍(HesterHarper),与其收养的孤儿院女孩凯瑟琳(Katherine)舞会结束后回家,凯瑟琳闹着要自己开车,结果撞倒了一个人。惊慌失措之际,两个人把死者推进院子中的废井里。从此,故事陷人超现实的噩梦中。赫丝特房间里的大笔现金丢了,她认为是被井里的死者偷的,让凯瑟琳下井找钱。凯瑟琳拒绝,她说那人还活着——跟她谈过话,并求了婚。“她觉得自己听到外面有一个声音。她认为是一个人在不停地叫啊叫的……待大风再次刮来时,那个声音就听不见了”[12](pl94)。凯瑟琳胡言乱语的癔病症状和赫丝特受压抑的歇斯底里,与梦幻般的阴郁混淆一起,使现实和幻想难以分辨。对于身临其境的人来说,那种经历非常可怕而又滑稽。“井中的未知物,成为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谜,对两个女人的幸福生活和故事的情节已然造成了干扰”[13](p57)。这种干扰表现在,自从两个女人把撞的人扔进井里之后,她们就开始了幻想之旅,现实与想象纠结在一起,终究谁也没有搞清楚井里面究竟有没有人,海斯特到底丢没丢钱。读者也不清楚哪些是幻想的,哪些是真实的,什么是清醒的,什么是错乱的。小说浓墨重彩的心理描写揭示了人们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变时那种面对现实的巨大压力、无路可逃、无法解脱转而沉迷于超越现实的幻想以其逃避现实压力的心理错乱。
三、悖谬叙事令人难以理解
叙事上的怪诞往往是与逻辑性相悖的荒诞性所致。这种荒诞性被称为悖谬,正如叶廷芳指出,悖谬的感性形态是“怪诞”[14](pl67)。按照他的观点,现实中之所以有太多的悖谬现象,是因为多元论的宇宙观框架内,一切单向思维或定向思维都存在着局限性,无法反映世界的多元性。因为世界已经不是过去的世界了,用简单的黑白分明、真假易辨、善恶显然、美丑界清等观念很难描述这个世界,现实往往是多元因素互相融合,难分难解。现实中很多自相矛盾的现象都是悖谬的不同表现形式,它与人们的期待相冲突,往往给人以怪诞的印象。在文学中,悖谬的形式之一就是运用自相矛盾的话语,即在否定一个肯定的同时做出另一肯定,反之亦然。喬利的叙事实际上就是对以往价值观念的反拨,因此,作品中处处暗示着自相矛盾的悖谬现象。每一部作品中她都叙述了与传统意义相悖的故事,同一部作品中,也处处触及悖谬。这正是其作品令读者困扰和迷惑的地方,也是引起评论界褒贬不一之处。乔利正是在作品中运用了悖论作为推动故事发展的动力,很多故事一波三折,人物发展迷惑丛生,创造了很多令人难以理解也难以忘怀的主人公形象;向读者揭示了后现代人类普遍面临的现实矛盾:
(一)道德与自由的悖谬暗示人性与物性的冲突
道德遵循的是社会规则,自由追求的是个体欲望的实现。即使在后现代时代,社会规范与个人自己之间的矛盾也远远无法解决。因此,个人的欲望追求与道德规范的制约永远是不可克服的冲突。《克莱蒙特大街的报纸》(T^e^Ve皿paper0/C/are腳,Street,1981)[15]中的“周报”(Weekly)追求自由生活的过程,就凸显了道德与自由的悖论。从开始处处为弟弟着想,对弟弟有求必应,到出卖弟弟;从收养流浪猫,到溺死刚出生的小猫;从无怨无悔地照顾俄国没落的贵族娜斯达西娅,到用计将她困死在梨树下的淤泥中,她逐渐地从别人的附庸、保姆,蜕变为自己的主人、他人的地狱。如果说,起初周报的行为是利他的,那么随着她自己生活目标的确立——即买一处房产和土地,她发现自己已经无力再承受利他的代价。因此,周报在自由追求自己的生活目标时,他人、它物就变成了她的绊脚石。在自由和道德之间,她选择了自由,放弃了道德。但是周报实现了目标后,内心始终也没有摆脱弟弟维克多和娜斯达西规事件的阴影,她听不得与弟弟相似的声音,看不得娜斯达西娅的坟包,时时刻刻受着良心的谴责和煎熬。周报在道德与自由的悖论上所做的选择令读者难以理解,令人不禁疑惑乔利的创作初衷。但乔利是否在引导我们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道德和自由相辅相成,二者须臾不能分离。追求道德诚然具有代价,但为了自由而放弃道德,其精神则陷于永远的束缚之中。因为,生活空间的自由,并不代表精神和心理的自由。以毁灭别人生命为代价换来的自由,将永远无真正的自由可言[16](1)81)。
(二)理想与现实的悖论渗透出个人与社会的冲突
个人的愿望与社会的现实一旦不能统一,理想与现实就形成某种对立和扭曲。当理想已经渐行渐远,现实已经呈现出对理想的否定之时,却依然不肯面对现实,苦守着理想的生活范式,这就是《牛奶与蜂蜜》中海姆巴奇的现实。对于典型的资产阶级家庭来说,身为澳大利亚的奥地利裔犹太难民,海姆巴奇在澳大利亚这个新世界里依然秉承奥地利贵族传统,竭力维护家庭的理性秩序,确保所谓的“理想、体面”的生活;作为奥地利人,他看重等级、注重品位,但疯癫却成为他们家挥之不去的梦魇。先是海姆巴奇把自己的妻子送进了疯人院并对外保密;后来又把自己的疯痴儿子瓦尔德瓦尔秘密关进了阁楼。因为家有疯癫意味着家庭理性秩序的颠覆,更意味着家庭的耻辱。疯癫的非理性性质,预示了海姆巴奇家理想与现实的不可调和性。因此,他们只能制造疯癫不在场的假象以维护其虚假的理想。为了确保自己对高雅生活的追求,海姆巴奇把雅各布当成了摇钱树,利用“大提琴王子”这个虚假的理想,不断地从雅各布的家人那里掠夺财富。并把自己的女儿路易斯嫁给了雅各布。但是现实却跟海姆巴奇开了一个大玩笑:雅各布爱上了麦洁,路易斯与弟弟疯痴儿乱伦,又生了一个呆痴女;雅各布一把火烧了家产,并烧坏了那双弹琴的手。海姆巴奇一心打造的高雅王国瞬间崩溃。追求本来以为是正确的理想,结果反而被证明错了。小说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对理想越是执着,理想反而离自己越远?为什么要摆脱不如意的现实,却总是被现实紧紧地困住?这种悖论有无可能解决?即人们有无可能在理想与现实冲突之时,根据现实调整理想,使理想更加符合实际?
(三)价值的悖谬揭示传统的濒危个人的自由发展到极致,对社会的价值就是无尽的颠覆与否定。依社会规则看来,个人的极度自由对社会规则和公众利益是一种不道德的伤害。依据李荣明的观点,“在社会的角度上看是应当的行为,在个人的角度上看是不应当的,反之亦然。悲剧性的对立导致了特殊的语用背离。在社会陈述中得到肯定的,在个人的陈述中必须予以否定”这不仅是绝大多数文本的陈述方式,在乔利的小说里,也到处充满着这样的价值悖谬。《新约全书》号召人们背弃谎言,追求真理,但在《牛奶与蜂蜜》里,海姆巴奇对雅克布树立的目标“大提琴王子”从一开始就知道是不可能实现的谎言。《旧约全书》中的摩西十诫中告诫人们不可杀人,但是《牛奶与蜂蜜》《克莱蒙特大街的报纸》都有为了个人利益而伤害他人性命的情节如《牛奶与蜂蜜》中的男主人公海姆巴奇是一名虔诚的教徒。一方面倡导着教义;另一方面,却挖空心思地敛财。虚荣就与财产联系在一起,而财产是男性行使权利的工具之一。其女儿路易斯乖巧可爱,犹如爱的使者,但在杀死情敌上毫不手软。因此,传统的价值观遭遇挑战,人们对自我和自由的追求犹如沱江的野马,不可控制。《牛奶与蜂蜜》中瓦尔德玛尔这样的疯癫儿就代表着这一现实。他可以不受上帝的约束,任由自己发挥自由意志。在价值判断或追求中,人们常常遇到的问题就是这种言行不一。《斯科比先生的谜语》[18]中,有处处体现出某种与社会价值不符的意义悖谬:一是医院的名称和医院里的现实相悖:圣·克里斯托弗和圣·裘德医院的名称本来含有仁爱的神圣意义,但故事开篇却用了9页共30份的夜班记录描写3号病房里的赌博行为。二是疗养院的工作本应该体现对老年人的照顾,但这里的老年人却像囚犯一样动辄受到护士们的惩罚。斯科比先生想喝一碗粥却到死也没喝上;因为说错了一句话,却被惩罚——由年轻女护士带去洗冷水浴。三是疗养院本应是救死扶伤的场所却处处盘算着怎么剥夺老人的财产,就连斯科比先生临终时也不放过,拿着财产转让协议逼着即将咽气的斯科比先生签字。小说揭示了在商业气息十分浓厚的语境下,传统的价值意义是否需要继续坚守?如何坚守?
(四)快乐与痛苦的悖论揭示情感的迷失
洛克认为:“感官由外面所受的任何刺激,人心在内面所发的任何思想,几乎没有一种不能给我们产生出快乐或痛苦来”[19](p94)。因此,人们常常把快乐、痛苦与善良、邪恶联系在一起,即能给予人快乐的为善,凡带给人痛苦的就是恶。但生活中的快乐和痛苦往往不随着人的意志为转移,因为快乐和痛苦的感觉会在达到一定程度后走向其反面。尽管洛克希望人们能够保持在一种适当状态,但逾越这种适当原则的人不在少数。追求快乐的欲望往往会左右人们的意志,甚而采用极端的方式,其中“包含了某种自甘堕落的病态成分”[20](p74)。极端自我的快乐往往造成他人的痛苦,而他人的痛苦带来的复仇就是自我快乐的终结,并陷人不可挽回的悲剧。乔利的小说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无论是物爱,还是情爱,主人公都爱得那么专横,那么执着,那么热狂,无可避免地陷入善与恶、爱与恨的悖论。例如,《牛奶与蜂蜜》中的主人公雅各布循着“新享乐主义”的观念走自己的路,就是为了追求快乐,但在追求快乐的同时,无可避免地伤害了很多人,甚至是将一些人引向了不归路。他与有夫之妇麦洁的私通关系已经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甚至在他带着妻子路易斯与麦洁夫妇去郊游时,竟不顾一切地与麦洁偷偷地做爱。这极大地伤害了路易斯的感情,使她陷人自卑与绝望的痛苦之中。路易斯为改变自己的状况铤而走险,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措施——唆使弟弟瓦尔德瓦尔害死了麦洁。故事的结局是,追求快乐反而陷人痛苦,无论是麦洁、雅各布,还是路易斯都没有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获得快乐。这种情景在《代理母亲》中的埃德温教授、在《情歌》(Love1997)中的道尔顿.福斯特(DaltonFoster)、在《井》中的赫斯特·哈拍(HesterHarper)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再现。乔利作品中的主人公缺少改变自身的勇气。在热情的追逐中生命体验的都是悲观的结局,快乐和痛苦的悖论在人生的旋涡中挣扎着,踉跄着前行。
四、小结
冯友兰认为,哲学是对人生的系统的反思。文学作品的魅力在于反映现实的同时,能够引发人们对现实的审美思考,尽管不是系统的,但却是哲学系统反思的基础。因此,乔利作品风格的怪诞,实际上是文学叙事多元化的表现。碎片化、虚实不分,以及悖谬常理的叙事方式,实质上表现了现代和后现代社会交替阶段文化价值的冲突。当工业社会迅猛发展带给人们更多的便利时,随之而来的是人们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科技更发达、物质更富裕、闲暇时光更多,人们对自我和社会的反思能力更高。乔利小说敏锐地捕捉到人类与自然、,与社会、与他人之间关系的变化,所以,作品中主人公的思维层面,表现为在思想中飞翔,在幻想中遨游,在回忆中品味人生。在行动层面,充分表达了与原有价值观相悖。实质上是反思不受陈规陋俗的约束,是对人生自由的追逐。这种追逐导致人们常常把虚幻当成现实,把现实嵌人幻想。虚实不分的状态恰恰反映出人们处理自己与外部世界关系上的无力,对社会规则和道德约束的回避,对这复杂多变世界的抗衡。对自由越是极度追逐,越是与社会规则相悖,越是遭遇悲剧。乔利并没有给出解决这种矛盾的药方,但阅读作品必然引起读者对自我与社会、现实与想象、快乐与痛苦等三对关系的叩问,弓丨导人们进一步思考在理性与非理性关系中如何正确把握自我,如何处理好个人欲求和他人欲求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复杂多元的世界重建社会规则和道德约束。一方面体现文明发展的包容性;另一方面,体现后现代社会规则的开放性,从而创造出既有自我又有社会、既符合现实,又充满想象;既娱乐自我,又不伤害他者的文明秩序。这可能就是乔利幻想的理想社会。
[参考文献]
[1]王培根.试析澳大利亚文学的历史演进[J].南开学报,1994(6).
[2]邱世凤,杨儒平.迈尔斯·弗兰克林——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文学的象征[J]·成都大学学报,2013(5).
[2]Woolfe,Sue;Grenville,Kate.ElizabethJolley:MrScobie,sRiddle[M].MakingStories:HowTenAustralianNovelsWereWritten.StLeonards,NewSouthWales:Allen&Unwin,1993.
[4]Daniel,Helen.Riddlesofmortality[J].TheAge,SaturdayExtra,Feb3,1983.
[5]NinaSankovitch,TheJoyofDiscoveringElizabethJolleyandHerVeraWright,February25,201012:33PM,http://www.huffing-tonpost.com/nina-sankovitch/the-joy-of-discovering-el_b_474557.html.wasawriterashonestandintelligentasVirginiaWoolf.
[6]Jones,Dorothy.L.(1990).Review:Jolley,Elizabeth,MyFatherJsMoon[J].Span:JournaloftheSouthPacificAssociationforCommonwealthLiteratureandLanguageStudies,(29-October).
[7]黄鸣奋.碎片美学在“超现代”的呈现[J].学术月刊,2013(6).
[8]杨劲松.论后现代作品分裂的叙事策略——从作品《出口》谈起[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12).
[9]唐敏.《雪国》虚实交错的世界[J].中外企业家,2015(35).
[10]Jolley,Elizabeth.Faxybaby,St.Lucia,Queensland:UniversityofQueenslandPress,1984.
[11]Daniel,Helen.AJolleycomichorror[J].TheAge,Sept.7th,1985,Sat.Extr.
[12]Jolley,Elizabeth.TheWell[M].Victoria:VikingPenguinBooksAustralia,1986.
[13]Baines,Pilar.DowninElizabethJolley’sTheWell:AnEssayonRepression,JournalofLanguage[J].LiteratureandCulture,Vol.61No.1,April,2014.
[14]葉廷芳.论悖谬——对一种存在的审美把握[J].文艺研究,1989(4).
[15]Jolley,Elizabeth.TheNewspaperofClaremontStreet[M].WesternAustralia:FremantleArtsCentrePress,1981.
[16]梁中贤.生存的符号意义——评《克莱蒙特大街的报纸》[J].外国文学评论,2007(4).
[17]李荣明.文学中的悖论语言[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
[18]Jolley,Elizabeth.MrScobie*sRiddle,Ringwood[M].Victori-a:PenguinBooks,1983.
[19][英]洛克.人类理解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6.
[20]王化学.唯美主义:世纪末的快乐与痛苦[J].山东师大学报,1992(3).
[2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赵复三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