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南戏研究及方法
刘祯 韩郁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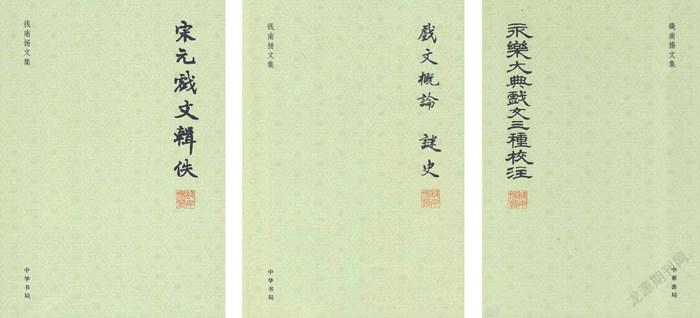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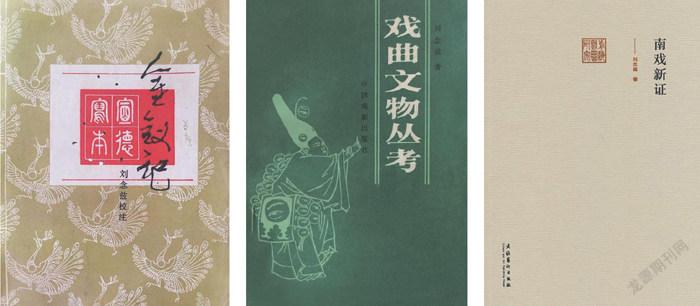
【摘 要】 南戏是我国最早成熟的戏曲样式之一,在戏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由于资料的缺乏,使其在早期成为戏曲史研究领域“一个失去了的环节”。在王国维之后,钱南扬是较早投入南戏研究领域的学者。他以“乾嘉学派”经史之学的方法治曲,通过大量文献考证,在南戏的辑佚与考辨工作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是南戏学科领域的奠基人。钱南扬之后,刘念兹以活态的方法研究南戏,从众多古老的地方戏中实地考察南戏遗存,并与历史文献互证,提出了福建莆仙戏、梨园戏是南戏重要分支的新观点,引发了各地南戏研究的新热潮。钱南扬与刘念兹一前一后,研究方法不同,他们代表了20世纪南戏研究的两个重要阶段。
【关键词】南戏;钱南扬;刘念兹;研究方法
一
20世纪,戏曲史的研究始终处于戏曲学的前沿,关于戏曲史的专题与整体研究从未间断。自王国维《宋元戏曲史》问世之后,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受王国维的学术影响,写出了《中国近世戏曲史》这样的专题史研究著作。而之后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张庚、郭汉城的《中国戏曲通史》则以整体视角,对戏曲史进行了研究与梳理。从文学史写作到戏曲史写作,戏曲史学科发展到戏曲学理论、戏曲史论的研究都占据了重要位置的阶段。
宋元戏文是我国戏曲最早的成熟样式之一,在当时与金元杂剧并盛,是戏曲史一个重要环节。正是一个如此重要的学科领域,在钱南扬之前,关于南戏的研究却可谓零星半点,是戏曲史研究领域“一个失去了的环节”[1]。南戏研究较之戏曲史的其他领域,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难题。首先是南戏的时代更为久远,古代关于南戏的文献记载,不仅屈指可数,而且本身还存在语焉不详与错舛之处,与南戏有关的专题论著也仅有如徐渭的《南词叙录》等“雪泥鸿爪”。其次,南戏本身属于民间戏曲,不论是语言文字还是表演形式,抑或艺术样态,都根植于民间。这也是古代文人对其鄙夷之处,认为其文辞俚俗、格律粗疏,对其不予过多记载与深入研究,这些均给后世的南戏研究增加了难度。
王国维是20世纪戏曲学研究的奠基人,同样也是早期南戏研究的拓荒者。在《宋元戏曲史 · 南戏之渊源及时代》中,他用了两个章节对南戏进行了考述。
南戏之渊源于宋,殆无可疑。至何时进步至此,则无可考。吾辈所知,但元季既有此种南戏耳。然其渊源所自,或反古于元杂剧。今试就其曲名分析之,则其出于古曲者,更较元北曲为多。今南曲谱录之存者,皆属明代之作。以吾人所见,则其最古者,唯沈璟之《南九宫谱》二十二卷耳。[1]
关于南戏的渊源,王氏认为始于宋代,可能要比元杂剧更为古老,认为其曲牌样式比元北曲更多地出自古曲,而今南曲谱录所存者,皆是明人所作。在缺少充实文献的基础上,王国维凭借个人见识与学识做出了这些论断,成为近代早期关于南戲研究的建设性观点,开启了对南戏研究的新认知。其后,随着南戏新材料的不断发掘,论证了这些观点的正确性。关于南戏的文辞特点,王氏在《宋元戏曲史》第十五章《元南戏之文章》中谈道:“元南戏之佳处,亦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唯北剧悲壮沈雄,南曲轻柔曲折,此外殆无区别。”[2]他对南戏宛转详尽、情辞相偕的文学与曲学特点把握得十分准确,对后世的南戏研究有启示作用。
不过,亦正是由于当时文献的稀少难觅,王国维关于南戏的研究也存在言辞模糊与错舛之处。如关于今所存最早的南曲谱录是出自明人之手这一判断是正确的,但非沈璟的《南九宫谱》,而是蒋孝的《旧编南九宫谱》。沈璟是在蒋孝《旧编南九宫谱》基础之上,考定错讹,参补新调,充实而成《南九宫谱》。再如,关于南戏所存剧目,王氏认为“最古者,大抵作于元明之间”[3]。但是随着《永乐大典南戏三种》的面世,可知现存南戏最早者为南宋时期的《张协状元》。此外,《宋元戏曲史》中亦无关于南戏的宫调、脚色、体制等方面的研究,未曾系统辑录南戏剧目,依旧为南戏的研究留下了难题。但无可否认,王国维为南戏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
王国维之后,郑振铎是较早将南戏纳入研究领域者。他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对南戏的起源、剧目等问题进行了论证,考证了包含《永乐大典南戏三种》在内的33种戏文的著录和残存情况,对南戏的研究起到了进一步推动作用。首次将自古以来被文人轻视,认为是不入流的南戏,纳入到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范畴,这本身就具有开创性,引起了后世学者对南戏的重视与研究。
钱南扬正是在这两部早期南戏研究的拓荒之作基础上,沿着王国维和郑振铎的学术道路,对南戏进行苦心钻研,毕其一生,成为南戏研究的集大成者和20世纪南戏研究领域的一座高峰。
二
钱南扬(1899—1987),名绍箕,平湖人,是我国著名的民俗学家、教育家。他192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在校期间,师从许守白、钱玄同、刘子庚、吴梅等多位名师,尤其在俗文学与曲学方面,具有很高造诣。先后任教于浙江大学、武汉大学、杭州大学、南京大学,曾任浙江省通志馆编纂、中国民间文学协会江苏分会副主席、《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分卷编委。主要成果有《谜史》[4]《元本琵琶记校注》[5]《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6]《宋元戏文辑佚》[7]《戏文概论》[8]《汤显祖戏曲集》[9]等。在南戏研究领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钱南扬的学术生涯中,南戏研究是其付出最多,成果最为显著的领域。早期,钱南扬以经史之学研究南戏,在南戏的辑佚、辨讹、校注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而后期,钱南扬则将研究的触角深入到戏曲本身,从南戏起源、剧本、内容、形式、演唱等方面入手,针对南戏本身的戏曲属性予以剖析,写出《戏文概论》。这也成为钱南扬在经历了前期南戏领域研究的积累后,走向学术成熟的标志。
钱南扬从事南戏的研究是从1924年开始的,《宋元南戏百一录》[1]花费了其近十年的时间,完成了对南戏资料一次全面与系统的搜集与辑佚。该书虽为南戏剧目与存曲的辑佚,但钱南扬亦在辑录名目之前,就南戏的名称、起源与沿革、结构、曲律、文章在历代文献中的记载,分别予以简要地梳理与辨析,以乾嘉学派严谨考证的治学方法,抽丝剥茧地从历史文献中,逐渐还原南戏的真面貌。在名称上,钱氏得出了“戏文”二字或为南戏正名,“南戏”或为“南曲戏文”的简称。而永嘉杂剧、温州杂剧应是地方之语。在南戏的起源问题上,本就有明代祝允明《猥谈》“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2]与徐渭《南词叙录》“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实首之”[3]的两种说法,从宣和到光宗要差七八十年。而钱氏则以辩证的思维,从“差异”本身入手,认为南戏从民间戏曲进入到文人视野需要时间的过渡,一种文学的方式是逐渐衍化而来的。创造性地提出了“酝酿期”的说法,认为南戏从温州当地的民间小调,经过酝酿期的发展,逐渐进入文人视野,后成为文人手中的作品。而这七八十年的酝酿与发展时期,也不算长久,故两种说法都是可信的,并没有武断地偏信其一。而“酝酿期”的说法,可谓南戏起源考辨的一个重要理论,被其后南戏研究的诸多学者所认同。在结构问题上,他通过新发现的《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以及用元杂剧原貌保存更多的《元刊杂剧三十种》与明刻本杂剧进行对比研究,得出明人喜肆意乱改古人文字的结论。认为南戏原本不分出,并且题目通常是隐于开头诗中的;而明刻本南戏中的分出以及题目或下场诗,是参照传奇所改的缘故。并从宾白、脚色、表演形式等方面阐述了南戏与北杂剧的差异之处,认为南戏宾白有韵文与非韵文两部分,是多脚色演唱制,有独唱、轮唱、合唱、对唱的演唱方式,与之后传奇的演唱体制与形式一脉相承。但在曲律上,南戏与传奇有较大差异,通过将两者的曲律进行对比,他详细阐释了南戏曲律的特性。在“文章”部分,他梳理了自《南词叙录》以来,明清文人对于南戏的评价,总结出南戏不兴的原因。除《南词叙录》外,明清两代文人大都认为南戏文辞俚俗,对其多有不满,故而对南戏曲律与文章皆不重视,使得南戏逐渐被湮没。
钱南扬以经史治学的研究之法,基本将南戏的起源、沿革、艺术特色清晰地勾勒了出来。而《宋元南戏百一录》最核心的“名目”部分,又展现出钱氏深厚的文献与考证功底。该书在剧目的辑佚上,参考了《永乐大典目录》《南词叙录》《宦门子弟错立身》《太霞新奏》《按对大元九宫词谱格正全本还魂记词调》《顾曲杂言》等,辑得南戏102本,其中12本有全本流传,残本存曲流传者45本,完全佚失者亦45本。关于曲文的搜集,又参阅了《旧编南九宫谱》《词林摘艳》《盛世新声》《吴歈萃雅》《南音三籁》《南九宫谱大全》等书。之所以能掌握这些在当时并不容易查阅的文献,一方面得益于其师吴梅的私人藏书。在吴梅的奢摩他室,钱南扬翻阅了很多珍贵的戏曲文献,尤其是明清时期的南曲谱,这在当时的北平是很难见到的,为他《宋元南戏百一录》的完成提供了文献基础。另一方面,也得益于钱南扬个人对文献的辛勤求索。作为一部文字量并不算大的著作,《宋元南戏百一录》花费了钱南扬近十年的时间,正如他自己所言“年来车驱南北,尘泌短衣,作辍靡常,迁延八稔”[1]。钱南扬在寻找文献资料和完成校对辑佚时所付出的艰辛,由此可见一斑。
在存目与存曲的辑佚上,钱南扬也并不只是简单著录,而是对所辑戏文的本事来源、流传情况、现存版本进行了详尽的勾稽。即使是已经完全散佚只存剧名的南戏,钱南扬也给予精密的考证,使读者亦能了解其本事来源与大致剧情,如:
《王俊民休书记》
案:此即系王魁事。王魁,名俊民,宋嘉祐间状元及第,见 《齐东野语》。“魁”字本非其名,《春渚纪闻》云:“宋人大抵以状元连姓相称曰‘某魁’,如马涓则曰‘马魁’。”《南词叙录》并收此戏与《王魁负桂英》,明是两本。(《宋元南戏百一录·名目》)[2]
《王俊民休书记》是一个已经完全佚失的南戏本子,钱南扬依旧通过自己扎实过硬的考据功底,从历史文献中考证出王俊民实为王魁,“魁”非其本名,使我们了解了该戏的大致情节。南戏婚变戏在宋元时期极为普遍,《王俊民休书记》与《王魁负桂英》皆为负心戏,男主人公皆为王氏,过多的相似性使两者有了对比的前提,而钱南扬正是通过这种关联性,考证出了二者的关系。
在《凤凰坡越娘背灯》的名目中,他又利用自己的民俗学知识,诠释了“背灯”为温州风俗。“女儿八字败母家者,出嫁时须遵行背灯之俗,此风清代猶然。”[3]这些都足见钱南扬治学的严谨,眼界的开阔与学识的渊博,也使得该书较其他同类著作资料,更为丰富翔实。1934年,钱南扬的《宋元南戏百一录》出版;同年,赵景深的《宋元戏文本事》[4]出版;1936年,陆侃如、冯沅君的《南戏拾遗》[5]出版。而赵景深也坦陈,《宋元南戏百一录》虽有错收,但所收录的南戏残文比自己的《宋元戏文本事》要多出不少,钱南扬看到的很多资料是自己不曾触及的,对于钱南扬的毅力与细心很是钦佩。[6]
诚如赵景深所言,钱南扬的《宋元南戏百一录》碍于当时文献与环境的局限,有一些错舛之处。但1949年以后,钱南扬依旧从事着南戏辑佚的工作,1956年出版的《宋元戏文辑佚》则进一步丰富了南戏的辑佚数量,本事来源考证也更加翔实,对于之前《宋元南戏百一录》存在的错误,逐一予以纠正。该书辑得宋元戏文名目167本,其中有传本者16本,全佚者32本,有辑本者119本。辑得佚曲近900支,考订了123种戏文的本事。是目前宋元南戏辑佚方面最为翔实的著作,也是南戏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巨著。
对南戏整理研究中的辨讹,亦是钱南扬的主要贡献之一。钱南扬的辨讹主要针对两个方面,一方面为南戏在传抄与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错讹,另一方面为前人研究时所产生的误读。对于南戏存本及存曲传抄时造成的文字错讹或疏漏,钱氏根据多本参校以及文意内容,进行了详尽的修改,不再赘述。由于前人误读造成的南戏本体认知方面的错讹,钱南扬以文献为基础,通过考据、校勘、辨伪的方法,对错处进行了翔实有力的辨析。他早期在《宋元南戏考》[1]中,针对王国维《曲录》未列南戏一项,而将宋元南戏误入明无名氏传奇之下予以更正。在《宋元戏文辑佚》中,他又考订了各参校曲谱中的失误与原委。如书中辑录第九剧《王祥卧冰》:
【一机锦】云雨歇,鸾凤分,别来愁断魂。暗掷金钱卜问君,吉凶事,尚未闻。眼巴巴绝信音,空教奴对景伤情。冷冷清清也,急煎煎睡不成,好教奴成孤另。[2]
关于这支曲牌,钱南扬出注道:
《正始》原注云:“此系古本原文。但今《蒋谱》所收者,与此尽有不同处,不识何所本也。”案:“空教奴”以下,《蒋谱》作“空教我数归鸿,不带书来也,我便扑扑簌簌泪暗倾。”其他辞句也稍有出入。以下各谱同。又案:《大成》卷三十九【北小石角 · 一机锦】下注云:“按此体,《雍熙乐府》载【北南吕调】一套四阕,《蒋谱》取第一曲误作《卧冰记》,入【南双调】,人几不知其为北曲矣。”《雍熙乐府》北套中常夹杂南套,如卷三【正宫·雁过声】“赤帝当权”一套便是;而此【一机锦】句格与《北词广正谱》【双调】所收者,大不相同,《大成》编者也见到这一点,才把它另入【小石角】,注上“与【双角】不同”,不知【一机锦】只能借入【南吕】,【小石角】原来并无此调的;其实只要看他联套方式,叠用四曲,必为南曲无疑;《大成》当他北曲,这是一误。《蒋谱》自序作于一五四九年,《雍熙乐府·安肃春山序》作于一五六六年,是《蒋谱》成书在前。说《蒋谱》取材于《雍熙乐府》,未免先后倒置,这是二误。《蒋谱》此曲收在【仙吕入双调】,而说“入【南双调】”,这是三误。故《大成》的话不足凭借。但是《蒋谱》此曲与《雍熙乐府》同,却是事实。这又怎样解释呢?大概是这两曲文字本来有些相像,后人把散曲校改戏文,而蒋氏又从改本录入曲谱罢。[3]
从这段批注可知,钱南扬在辑佚存曲时,对不同时期文献的正误加以了详细的辨析。首先从联套中,叠用四曲的形式,判断【一机锦】为南曲,故而《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简称《九宫大成》)将其看作北曲是错误的。其次,通过比较蒋孝《旧编南九宫谱》(简称《蒋谱》)与《雍熙乐府》的成书时间,发现了《九宫大成》认为《蒋谱》取材于《雍熙乐府》的先后倒置。再次,又发现了《九宫大成》在转述《蒋谱》中该曲牌时,宫调归错的失误,全面否定了《九宫大成》的观点。最后,凭借自己的曲学素养与经验,认为该曲可能是由散曲校改后的戏文,而蒋氏将改本录入了曲谱,这就合理解释了两谱中该曲相同的问题。从这简单一支曲子的辑录,即可看到钱南扬在南戏整理与研究时的认真与严谨,他从不盲信前人或机械抄录,而是通过自己细致的研究,辨析前人之讹,还原事实。像这样的例子,在钱南扬的《宋元戏文辑佚》中不胜枚举,在此不一一举例。
在《元本琵琶记校注》中,他又再次强调了前人对“寻宫数调”的误读。
寻宫数调—这里的宫,当指宫调而言;调,当指曲调而言。古代以十二律和七音相乘,凡十二律和宫音相乘叫做宫,与商、角等相乘叫做调,共得八十四宫调。而实际上,在南曲中,常用者仅九个宫调而已;而且统称“宫调”,宫与调二者亦不复区别。每一宫调,又包括若干曲调;在南曲中,曲调可分三类:即引子,过曲,尾声。考戏文格律,自南宋初发展到元末高明作《琵琶记》时,已相当进步;然自明朝中叶,昆山腔起,腔调既变,格律日严,把它和戏文的格律相比,自然又有许多不同。明人不懂得格律在随时发展,往往把昆山腔之律去衡量戏文,觉得戏文处处不合律,便误当它是没有格律的,并举这句“也不寻宫数调”为证据。换句话说:就是认为戏文的联套,可以不管笛色的高下,不论曲调的性质,是毫无规律,随意乱用的。不知这里的意思,是说:看一本戏文的好坏,不要着眼于科诨,也不要着眼于宫调,首先应该从它的内容来判断;不是说:无宫可寻,无调可数。明人研究学问的粗枝大叶,往往如此,别人不必说,贤如徐渭,也所不免,……这是不从事物的发展去看问题,致有此误。[1]
通过对“寻宫数调”的本意解读,钱南扬驳斥了前人以此为据,认为南戏不叶宫调的错误看法。认为南戏自《琵琶记》格律与宫调已经日臻成熟,但明人却以之后更为成熟的昆山腔的曲律去衡量戏文,以致认为南戏没有宫调,是街巷小曲,故而被士大夫所鄙夷,不予记录,是犯了本质的错误。并得出明人做学问粗枝大叶的看法。
对南戏剧作加以校注和整理,也是钱南扬从事南戏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贯穿其学术生涯始终。其中,《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与《元本琵琶记校注》是其南戏剧作校注方面的代表性成果。
诚如前文所述,南戏研究之难,在于它的年代久远与民间性,而钱南扬早期从事的正是民俗文学的研究。钱南扬1919年考入北京大学之后,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校内积极提倡和重视民俗文学。钱南扬也将研究的重心放在了民间文学与戏曲上面。钱南扬最早从事的民间文艺研究对象是谜语,1920年编成《谜史》一书的初稿。猜谜本是民间最普通的娱乐与文艺形式,却很难追溯其起源与发展。钱南扬通过个人的努力,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勾稽出有关谜语的历史、种类、制作方法、猜谜形式等相关记载,予以著录与解读,体现了钱南扬立足古代民间文艺研究的学术视野与个人深厚的民间文艺知识储备。之后他又致力于梁祝传说的研究,先后发表了数篇文章,成为当时该领域研究的第一人。而后,他的《市语汇钞》问世,被誉为是“抉隐发微的拓荒性成果”[2],是民间语料文献著录与研究的开先河之作。正是由于早期钱南扬通过从事民间文学与文化的研究,掌握了民俗文学研究的方法,储备了大量民俗学知识,使得他在之后从事同属民间文学且民间色彩更为浓郁的南戏研究时,如鱼得水。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面世后,关于它的研究依然困难重重。其文本蕴含了大量当时的民间俗语与俚语,涉及诸多彼时民俗与社会活动的知识,使得今人文本阅读都很吃力,何谈研究。而钱南扬却是学术研究领域甘愿“啃硬骨头”的人,承担了《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的工作。通过他的校注,文本中那些艰涩难懂的民间俗语与俚语以及民风民俗被一一诠释。
《張协状元》第一出:“(张协白)在家春不知耕,秋不知收,真个娇妳妳也。”[3]其中“妳妳”的含义,钱南扬注释:“比喻舒适。温州方言至今如此。”[4]类似这样的俚俗之语,《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中不胜枚举,他都一一予以详细注释,有些甚至将其历史出处亦加以说明,其考证功底扎实过硬,令人信服。
《张协状元》第二十七出:“(丑)先生公相,愿我捉得一个和尚。下一截把来洗麸,上一截把来擂酱。”[5]关于“洗麸”与“擂酱”,钱南扬解释说:“洗麸,从麦麸中洗出面筋来。惟洗麸不能用足,今浙中游戏,执小孩两脚簸动,叫做汏面筋。汏面筋即洗麸,可能指此。擂酱,《古今谭概 · 酬潮部》第二十四:东坡为佛印题小像云:‘佛相佛相,把来倒挂,只好擂酱。’谓和尚光头,有如擂槌。”[1]
“洗麸”本是民间洗面筋的习俗,但唯独不能用足。但浙中却有执小孩双足簸动的洗面筋游戏,对应文意“下一截把来洗麸”,实则是用当地习俗来进行戏谑。而“擂酱”则出自苏东坡打趣佛印的典故。经钱氏细致地注释后,读者可以迅速谙晓文中之意趣。将《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中所运用的彼时民俗知识与社会活动予以细致地诠释,使晦涩的文本清晰可读,亦是钱南扬校注上的重要贡献。
关于《琵琶记》的校注,钱南扬对其诸多版本进行了细致考察,创造性地将时间更晚的清代陆贻典抄本作为底本,而以其他年代更早的明代诸本作为参校本。他认为明代诸本自李卓吾之后,已被改得面目全非。而陆抄本虽为清代抄本,但其整体的抄写形制更像《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曲文与《九宫正始》所引元谱文字接近,应为陆贻典对早期元代《琵琶记》存本的一个过录本。而钱南扬所做的,便是努力恢复最为接近元代高明原本的一个《琵琶记》,并为全本疑难字句进行注释,让学力不逮者正确理解此剧。为此,钱南扬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参考了近270种文献,才完成《元本琵琶记校注》一书。《元本琵琶记校注》加之之前的《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成为南戏校注方面最为突出的代表性成果。
《戏文概论》是钱南扬在南戏研究领域的集大成之作,亦是其南戏研究进入后期的一部成熟的学术总结。从早期的《宋元南戏百一录》到《戏文概论》,可以明晰地看出其学术轨迹的变化,由早期的经史之学治曲到回归戏曲本体的艺术研究。
《戏文概论》共厘为“引论”“源委”“剧本”“内容”“形式”“演唱”六章。其中,“引论”“源委”“剧本”“形式”的内容基本是对《宋元南戏百一录》的增补与修订。在“引论”部分,增补了南戏之前的古老剧种,对南戏产生的时代背景与经济条件进行了分析。较之《宋元南戏百一录》中单一地谈论南戏的名称缘来与起源时期,《戏文概论》更加体系化。在“源委”部分,增论了戏文三大声腔海盐、余姚、弋阳各自的缘起以及之后在不同区域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嬗变。系统科学地证实了南戏这种活态的、生命力旺盛的剧种,是在不断吸收外界养分,丰富自身的过程中,才得以保持长久的生命力,为之后的学者以民间田野的方式研究南戏的活态性提供了新视角。
“内容”与“演唱”部分是《戏文概论》中最大的亮点,也是钱南扬学术路径发生明显转变的地方。“内容”与“演唱”是对南戏本体的艺术探析,他将研究的视阈转到了戏文本体价值与舞台艺术方面,不再是早期单纯的文献考证与概述。在“内容”部分,钱南扬对较为著名的南戏存本,分别从文本的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艺术特色方面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如评论《张协状元》时,他认为:“《张协状元》作为婚变戏,通过张协与王贫女的婚姻纠葛,歌颂了王贫女的善良的品质和坚强的意志;揭发了张协的丑恶面目;同时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种种不合理;对一个善良劳动妇女横遭摧残和迫害,提出了控诉和反抗。”[2]并认为它作为早期的戏文,还留有古剧的痕迹,过多的插科打诨稍显胡闹,破坏了戏台严肃的环境。但由于受特殊时代的影响,他在评论作品的主题思想与人物时,有些以阶级立场为纲,认为张协与王贫女本不应该结合,前者是剥削阶级,而后者是善良的劳苦大众,阶级矛盾是无法调和的,大团圆结局破坏了现实意义。[3]
书会与剧团,一个是戏曲剧本创作团体,另一个是表演团体,现今看来他们应属不同的工作系统与范畴。但在早期南戏中,他们可能同属一体,钱南扬在“演唱”部分,对这种情况进行了考辩。戏文《董秀英花月东墙记》下有“九山书会捷讥史九敬先著”的字样。宋元时期,有捷讥等级的官吏,但从《太和正音谱》中,可知捷讥亦是古代角色的名称。故钱南扬推测,曲本中的捷讥应为当时演员所扮演的是捷讥官而得名,并非日常生活之捷讥。[1]
【水调歌头】韶华催白发,光景改朱容。人生浮世,浑如萍梗逐西东。陌上争红斗紫,窗外莺啼燕语,花落满庭空。世态只如此,何用苦匆匆!但咱们,虽宦裔,总皆通。弹丝品竹,那堪咏月与嘲风。苦会插科使砌,何吝搽灰抹土,歌笑满堂中。一似长江千尺浪,别是一家风。
【满庭芳】暂息喧哗,略停笑语,试看别样门庭。教坊格范,绯绿可同声。酬酢词源诨砌,听谈论四座皆惊。浑不比,乍生后学,谩自逞虚名。《状元张协传》,前回曾演,汝辈搬成。这番书会,要夺魁名。占断东瓯盛事,诸宫调唱出来因。厮罗响,贤门雅静,仔细说教听。
(《张协状元·第一出》)[2]
【烛影摇红】烛影摇红,最宜浮浪多忔戏。精奇古怪事堪观,编撰于中美。真个梨园院体,论诙谐除师怎比?九山书会,近目翻腾,别是风味。一个若抹土搽灰,趍枪出没人皆喜。况兼满坐尽明公,曾见从来底。此段新奇差异,更词源移宫换羽。大家雅静,人眼难瞒,与我分个令利。
(《张协状元·第二出》)[3]
从以上《张协状元》中的三支曲牌,钱南扬分析出宋元南戏时期,书会众多,竞争激烈,相互之间既要比剧本又要比演唱。那么,很可能早期的书会与剧团没有分家,是统一的,除捷讥外应该还有其他脚色。而书会中的人一方面要进行剧本写作,另一方面还要进行脚色扮演,故而早期的南戏演员并非职业的而是业余的。在随后的章节中,钱南扬根据《太和正音谱》中赵孟頫评价演员的文字,印证了自己的说法。正因早期南戏的剧团是文本创作与舞台表演兼为一体的运营模式,故他以剧团为入口,将笔触延伸到了脚色、剧场、演唱等各方面的研究,来探析整体之间的关联性,对南戏演出的形态与特色进行了系统的勾勒。
从《宋元南戏百一录》到《戏文概论》,可以看出钱南扬将研究的视角从早期的文献考证拓宽到了舞台,回归到对戏曲本体艺术价值的研究,他的學术路径从受传统乾嘉学派影响的朴学治曲,逐渐过渡到现代学术体系之中。而他的治学视阈也从早期偏重一隅考证、赅括式的研究,上升到了史论研究,《戏文概论》从体制来看,已然颇具“南戏史”的风貌,基本架构起了南戏的学科研究体系。
王国维认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首次创造性地赋予戏曲独立的学科品格,将其从末技与附庸中摆脱出来,并用严谨与科学的治学方法第一次架构起学科的戏曲史体系,成为近代以来为戏曲写史的第一人与戏曲学科研究的奠基人。然王氏所关注的戏曲,依旧是文人写就的元曲,对于更为民间化的南戏则谈及甚少。其后的钱南扬则架构起了南戏研究的学科框架,并培养了一批精修南戏与曲学的弟子。他生前从事教学的南京大学也成为了南戏与曲学研究的重镇。以文献、曲学为基础的考据方法,也成了南京大学戏曲研究方面最为重要的传承与特色。钱南扬的弟子们秉承着他的研究方法,沿着他的学术道路,进一步开拓与延伸。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弟子俞为民,在钱南扬之后点校了《宋元四大戏文读本》[4],编著了《宋元南戏史》[5]等著作,进一步推动了南戏研究在戏曲史领域的研究进程。
三
钱南扬对南戏的研究,一路走来披荆斩棘,有筚路蓝缕之功,是南戏学科的奠基人。而在20世纪后期,将南戏研究从冷僻推向热点,引发各地学者将极大热情投入到南戏研究领域、推动南戏研究进入新局面的,是刘念兹先生与他的《南戏新证》。与钱南扬不同,刘念兹将南戏作为一种活态的艺术形式进行研究,以田野调查和文献结合互证的方法,考证出了现存剧种中南戏的遗存,对南戏的民间本质做了深度研究与推广,为南戏研究带来了新视阈与新方法,是继钱南扬之后,南戏研究领域的又一位大家。刘念兹对南戏研究的重要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新观点与新材料之挖掘;活态研究南戏方法之创新;各地方南戏研究热潮之引领。
刘念兹(1927—2010)出生于成都,195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53年东北鲁迅文艺学院戏剧理论研究生毕业。先后任职于东北戏曲学校、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戏曲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从事戏曲史论与教学工作。著有《唐短歌》[1]《宣德写本金钗记》(校注)[2]《南戏新证》[3]《戏曲文物丛考》[4]等;参与编著《中国戏曲通史》,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 · 戏曲曲艺卷》戏曲史分支副主编。此外,还发表百余篇戏剧戏曲学相关学术论文。
进入20世纪中后期,在南戏研究的学术领域,刘念兹系统地论证了福建梨园戏与莆仙戏是南戏的重要分支与遗存。如前所述,资料的严重缺乏一直是南戏研究领域的主要难题。虽然钱南扬、赵景深、冯沅君等人在南戏辑佚工作上作出重要贡献,但主要通过历史文献对南戏本身的剧目辑佚。作为与元杂剧并称,是中国早期重要戏曲形式的南戏,它的面貌绝不会完全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在当今的地方戏中依旧会有其残存,亟待更为完备的辑佚工作。刘念兹打破了前人仅从文献资料中寻找材料的局限,采取了文献梳理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以史料文献为基础,亲自对受南戏影响较大的福建梨园戏、莆仙戏进行实地考察,与史互证,得出了福建梨园戏与莆仙戏是南戏重要遗存的结论。
对于这一论点的考证,刘念兹采取了主客观互证的严谨方法。在《南戏新证》中,他考证了福建在宋代已然相当发达,在全国居于重要地位。而作为重要经济与贸易中心的泉州,在南宋实则起到了陪都的作用,是宋代皇室宗亲的聚集之处。福建在两宋以来,除经济雄厚外,更是文化与政治的要地。“据载,(莆田)当时应中央考试而获得‘正奏名’进士的就有1202人。以‘待奏名’及其他出身的有730人,通过殿试而取得第一名(即状元)的有6人。”[5]而宋代莆仙文人所著书籍,据不完全统计有637种之多,这仅为福建的一个县。北宋宰相有十人籍贯出自福建,为全国之最;到了南宋也有八人,处全国次席。不可否认,福建人在两宋时期的政坛占有重要地位。自北宋与金人对峙以来,就有大量北方与中原人口南迁,宋室南渡之后,福建人口激增。从政治、经济、文化、交通来看,福建在两宋时期处于东南一隅的重镇。在其原有基础之上,加之中原文化的南流,便促进了宋元南戏在福建地区的发展。刘念兹以清道光《漳州府志》卷三十八“民风录”记载的朱熹于绍熙元年(1190)知漳州州事,有禁止当地演戏之事,以及引陈淳《上傅寺丞论淫戏书》中有关禁戏的内容等相关材料为例证,推测南宋时漳州地区的戏剧活动已经十分盛行。这与徐渭提及的“南戏始于宋光宗朝”的时间是接近的,故而论证出南戏很可能是在温州、杭州以及福建的莆田、仙游、泉州等多地“同时出现”的结论。[6]
回归到莆仙戏、梨园戏本身,刘念兹则从剧目、脚色、乐器、表演形式等方面,论证其与南戏的关系。从剧目看,他将现存莆仙戏、梨园戏剧目与《南词叙录》中所收南戏剧目进行了比对,发现剧目基本一致。并且莆仙戏、梨园戏还保留了许多不为《南词叙录》《曲品》等前人著录类作品所记载的剧目。早已失传的南戏《朱文太平钱》,至今仍活跃于梨园戏的舞台。南戏的行当共分为生、旦、净、末、丑、外、贴七个脚色。而梨园戏与莆仙戏过去都名为“七子班”,后来加了老旦后,才称为“八仙子弟”。在梨园戏的一些传统剧目上,依旧采用生、旦、净、末、丑、外、贴的行当配置,与南戏的行当配置是一致的。南戏在宋元时期,配乐主要以鼓、笛、拍、筚篥为主,尤其筚篥是南戏音乐中最主要的标志。现今,在全国的各剧种中,除莆仙戏以外均没有以筚篥作为主要伴奏乐器的剧种。而筚篥最早可追溯至隋唐燕乐,之后一直是唐宋大曲及宋词的主要配器,后又流传于宋元南戏之中,足可见福建莆仙戏的悠久历史及其与南戏的渊源。宋元南戏以副末开场,之后的明清传奇多承袭此制。而今的莆仙戏依旧保留此制,必定副末开场介绍剧情。刘念兹将莆仙戏、梨园戏的这些艺术特色与宋元南戏进行比对,发现了它们与南戏的承袭关系。从客观的外部环境,他论证了莆仙戏与梨园戏具备成为南戏重要分支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回归戏曲艺术本身,他又发掘出它们与宋元南戏一脉相承的关系,故而他所得出的福建莆仙戏与梨园戏是南戏重要分支的结论是可信的,是南戏研究领域一个重大发现,也为南戏的研究打开了新视窗与新局面。
在《南戏新证》中,刘念兹还考证出宋元南戏剧目244种,比钱南扬《宋元戏文辑佚》中的167种多了77种。他本人又对1958年发现的嘉靖本《琵琶记》进行了校注,并与清代陆贻典抄本进行比勘,发现了两者的同源性,弥补了陆贻典抄本中的诸多错漏之处。而作为舞台演出本的嘉靖本《琵琶记》,其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文獻价值,通过刘念兹的整理与校对,使其为早期南戏演出形式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此外,刘念兹另一项重要的成果,便是对1975年出土的宣德写本《金钗记》的校注整理。他完成了对早已失传的一部著名宋元南戏剧目全貌的恢复工作。宣德本《金钗记》的发掘整理工作,对戏曲文物以及南戏研究都是一次重要突破。继钱南扬等老一辈学者之后,刘念兹对于南戏新材料的挖掘与补充予以了有力的推进。
以活态的方法对历史久远的南戏进行实地考察与研究,是刘念兹在南戏研究领域的一大贡献。关于南戏的研究,早期的学者多爬梳文献,进行细致的梳理与辑佚,其中以钱南扬用功最勤,成果最为显著。而刘念兹则在充分利用前人已做出的文献成果的基础上,亲自对福建、广东、浙江、江西等地的地方戏进行实地考察。他翻看了大量的民间唱本,从文物史料入手,以实证考察的方式与文献互证,对南戏的产生、发展、流变、剧目、音乐等方面做出更加深入的研究,开创了南戏研究的新局面。也完成了钱南扬所期冀的从地方戏剧、民间唱本中寻求南戏遗存,以求构建更为完备的戏文辑佚的设想。
刘念兹为寻求南戏新证,曾四赴福建,三至江西,两到浙江等地。翻阅了1375个莆仙戏剧本,并对老艺人与相关人士进行了访问。故而他在列举81个莆仙戏与南戏同名或情节相似的剧目时,对浙江、江西、湖南、安徽、四川等地的地方戏中与此相同的剧目、剧种亦予以了梳理。这是他20余年南北奔波,实地考察凝结而成的心血,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南戏的发展与流变过程。更为后人开辟出一条从各地方剧种,尤其是南方古老剧种中寻求南戏遗响的新方法与新道路。对我们进一步发掘南戏遗产,以活态方法深入南戏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对现存戏曲文物进行实地考察与研究,以填补戏曲史中的一些空白,是现今戏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如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便以研究戏曲文物而擅长。刘念兹很早便将对戏曲文物的实地考察,纳入到了自己田野调查研究的范畴之中。他除了实地考察莆仙戏、梨园戏的剧本外,还观摩了剧种的脚色组成、化妆、表演形式,系统全面地论证了它们与南戏的渊源,以求得到的结论合理。此外,他还考察了莆田的瑞云祖庙,证实了当地人所祭祀的戏神田公元帅为雷海青。并从当地老人处听得了关于田公元帅的传说:忠义伶工雷海青死后曾出现在莆田上空,由于身后的“雷”字大旗被云遮得只剩“田”字,故当地人称之为田公元帅。而他在江西访问青阳腔老艺人时,获悉弋阳腔与青阳腔供奉的戏神亦为田姓老君。汤显祖曾提到的清源祖师,据江西省戏校徐伯轩的说法在宜黄与乐平一带已找不到痕迹,据传祖师是有姓田、姓窦的两位。在浙江温州,刘念兹与温州高腔、乱弹、禾调等剧种老艺人座谈时,也听说了温州高腔的祖师是田元帅的说法,而全国其他剧种的祖师则为唐明皇。温州高腔在几个剧种中处于长者地位,田元帅要被供奉在正中央。刘念兹以上所提到的几个剧种均与南戏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弋阳腔、青阳腔更是南戏在流变过程中的重要支流。而他们都以供奉田公元帅为宗,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们或是南戏的支流,或是剧种早期受到了南戏传播的影响。[1]
刘念兹《南戏新证》的治学方法与诸多学术观点,引领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各地关于南戏研究的新热潮,对福建地区的戏曲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福建地区的学者正是沿着刘念兹所开辟的道路,进一步对当地的莆仙戏、梨园戏展开了深入研究。1988年,福建省戏曲研究所、泉州地方戏研究所、莆仙戏研究所主编出版的《南戏论集》[2],收录了当时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与福建省文化厅联合举办的南戏学术研讨会中的代表成果,其中有多篇文章谈到了闽南地区地方戏与南戏相关的问题。如吴捷秋《南戏源流话“梨园”》、林庆熙《略论福建戏曲的产生及其与南戏的关系》、陈纪联《唐宋遗响,南戏支派—莆仙戏源流新探》、谢宝桑《莆仙戏音乐与宋元南戏的关系》等文章,分别从福建地方戏的起源、声腔特色与南戏进行比较,论证其关联性。这显然是受到了刘念兹《南戏新证》的影响。刘念兹的《南戏新证》对有关莆仙戏、梨园戏中与南戏相同的剧目或情节,均予以了細致的梳理与介绍。福建地方戏的剧目流变、传承研究,也成为了当地戏曲研究的重要方向,代表作有:曾金铮《梨园戏几个古脚本的探索—〈王魁〉〈王十朋〉〈郭华〉〈吕蒙正〉》[3]、郑国权《从〈荔镜记〉等明刊本探寻泉腔南戏》[4]。吴捷秋的专著《梨园戏艺术史论》将梨园戏最具代表性的30个剧目的演变、流传情况进行了全面论述。[5]马建华的《莆仙戏与宋元南戏、明清传奇》一书,对莆仙戏与南戏的关系做了系统的辨析,弥补了莆仙戏较之梨园戏在当地研究力度有所不足的缺陷。[6]此外,福建省还曾多次举办南戏学术研讨会,都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当地学者通过对莆仙戏、梨园戏的起源、剧目流变等相关研究,进一步印证了刘念兹所提出的福建莆仙戏、梨园戏是南戏重要一支的说法。
在《南戏新证》中,刘念兹曾提出南戏的诞生地可能并非仅限温州,很可能是在温州、杭州以及福建的莆田、仙游、泉州等多地“同时出现”的结论。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胡雪冈、徐顺平、徐宏图为代表的浙江学者对这一论点予以了反驳,认为南戏的起源地即为温州。徐顺平《南戏首先产生于温州不容否定》一文,对刘念兹“多点说”的例证逐条予以了否定,认为福建地区传存的南戏剧目为流而非源。[1]以南戏起源“温州说”为基准的浙江地区学者,随之阐述了当地南戏学术研究的另一热点即“温州腔”。认为南戏除海盐腔、余姚腔、昆山腔、弋阳腔之外,还有第五大声腔即“温州腔”,早期南戏便以“温州腔”进行演唱。这一观点最早由叶德均提出,浙江学者大都支持。[2]从现有资料来看,“温州腔”的说法一时还难以成立,有待更多资料的发掘与考证。但不可否认,关于南戏是否最早仅产生于温州的学术争论,使得福建、浙江地区的南戏研究迎来了一个新热潮。
刘念兹在《南戏新证》中,亦曾提到南戏“五大声腔”的说法。但并非如浙江学者所提出的“温州腔”,而是“潮泉腔”。刘念兹认为“潮泉腔”是元末明初,南戏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声腔,而明刊本《荔镜记》便是它的历史见证。赵景深在《南戏新证》序言中,对这一说法予以了肯定,认为“潮泉腔”是客观存在的,而往往被史家们忽略了。[3]刘念兹提出的南戏五大声腔之说可以补正过去说法的不足,事实俱在,无可辩驳。而“潮泉腔”的提出,为广东地区关于潮剧的研究,以及潮剧与南戏关系的研究开辟了新天地。“随着《明本潮州戏文五种》《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的出版,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认同在泉、潮两地的戏文中,保留了早期南戏的基本形态。”[4]陈历明《明本潮州五种戏文与南戏的流传》一文认为,明本潮剧五种正是南戏南传的轨迹,是南戏在潮州发展的五个阶段。[5]林淳钧在《潮剧三探》中提出了潮剧源于南戏的说法。[6]而潮剧源于南戏的说法已经被当今学术界所承认,使其源流与历史地位得到了肯定。
毫无疑问,刘念兹将南戏的学术研究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引发了福建、浙江、广东等地学者们对南戏研究的极大热情。直至21世纪的今天,很多学者仍沿着《南戏新证》的思路与方法,去发掘本地地方戏与南戏的传承关系,使南戏在当代研究的进程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一活态研究的典型之例亦为其他领域所借鉴,特别是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来,“活态”研究更是成为一种方法,一种观念,一种流行。《南戏新证》所引发的学术讨论亦是对南戏研究有力的推动,使得人们越来越接近南戏的真实面貌。
从钱南扬到刘念兹,他们无疑是20世纪南戏研究领域的两座高峰,代表了南戏研究不同阶段的特点。早期钱南扬以乾嘉学派朴学治学之法,应用于南戏研究,构建起南戏研究的学科体系,填补了戏曲史上的空白,具有开拓之功,并在南戏的起源、辑佚、辨讹、校注等方面取得诸多成果,是南戏研究的奠基人。进入20世纪中后期,刘念兹将田野调查和文献结合互证的活态研究方法引入到南戏研究领域。从地方戏剧、民间唱本中寻求南戏遗存,完成了更多新材料的辑佚工作。与此同时,发现了诸多古老声腔剧种与南戏的密切关系,引领了全国多地关于南戏研究的新热潮,将南戏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故而,钱南扬与刘念兹二位先贤为戏曲学研究所作的贡献,尤其是在南戏研究领域的突出成就,是我们所不能忘却的。
责任编辑:赵轶峰
[1] 钱南扬:《宋元戏文辑佚·前言》,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页。
[1]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09页。
[2]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第120页。
[3]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第119页。
[4] 钱南扬:《谜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5] 高明著、钱南扬校注:《元本琵琶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6] 钱南扬校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
[7] 钱南扬:《宋元戏文辑佚》,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8] 钱南扬:《戏文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9] 汤显祖著、钱南扬校点:《汤显祖戏曲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1] 钱南扬:《宋元南戏百一录》,哈佛燕京学社1934年版。
[2] 祝允明:《猥谈》,转引自钱南扬《宋元南戏百一录》,第2页。
[3] 徐渭:《南词叙录》,《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39页。
[1] 钱南扬:《宋元南戏百一录 · 叙目小记》,第3页。
[2] 钱南扬:《宋元南戏百一录》,第68页。
[3] 钱南扬:《宋元南戏百一录》,第72页。
[4] 赵景深:《宋元戏文本事》,北新书局1934年版。
[5] 陸侃如、冯沅君:《南戏拾遗》,哈佛燕京学社1936年版。
[6] 赵景深:《过去对南戏研究的成就和缺点》,《元明南戏考略》,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6页。
[1] 钱南扬:《宋元南戏考》,《燕京学报》1930年第7期。
[2] 钱南扬:《宋元戏文辑佚》,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1页。
[3] 钱南扬:《宋元戏文辑佚》,第32页。
[1] 高明著、钱南扬校注:《元本琵琶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
[2] 曲彦斌:《“谜史”与“市语”:钱南扬别辟蹊径、独树其帜的研究》,《文化学刊》2017年第6期。
[3] 钱南扬校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 · 张协状元》,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页。
[4] 钱南扬校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 · 张协状元》,第9页。
[5] 钱南扬校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 · 张协状元》,第135页。
[1] 钱南扬校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 · 张协状元》,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1页。
[2] 钱南扬:《戏文概论》,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14页。
[3] 钱南扬:《戏文概论》,第118页。
[1] 钱南扬:《戏文概论》,第194—196页。
[2] 钱南扬:《戏文概论》,第194页。
[3] 钱南扬:《戏文概论》,第195页。
[4] 俞为民校注:《宋元四大戏文读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5] 俞为民、刘水云:《宋元南戏史》,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
[1] 刘念兹:《唐短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 刘念兹校注:《宣德写本金钗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 刘念兹:《南戏新证》,中华书局1986年版;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年版。
[4] 刘念兹:《戏曲文物丛考》,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版。
[5] 刘念兹:《南戏新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页。
[6] 刘念兹:《南戏新证》,第23—29页。
[1] 刘念兹:《南戏新证》,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321—325页。
[2] 福建省戏曲研究所、泉州地方戏研究所、莆仙戏研究所:《南戏论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
[3] 曾金铮:《梨园戏几个古脚本的探索—〈王魁〉〈王十朋〉〈郭华〉〈吕蒙正〉》,福建省戏曲研究所、泉州地方戏研究所、莆仙戏研究所主编《南戏论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
[4] 郑国权:《从〈荔镜记〉等明刊本探寻泉腔南戏》,《福建艺术》2012年第4期。
[5] 吴捷秋:《梨园戏艺术史论》,中国戏剧出版社1996年版。
[6] 马建华:《莆仙戏与宋元南戏、明清传奇》,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年版。
[1] 徐顺平:《南戏首先产生于温州不容否定》,《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2] 叶宇星:《〈南戏新证〉与地方南戏研究的展开》,《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3] 刘念兹:《南戏新证 · 序》,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页。
[4] 骆婧:《再议“潮泉腔”与宋元戏文的传播—从饶宗颐、龙彼得戏文研究说起》,《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5] 陈历明:《明本潮州五种戏文与南戏的流传》,《文史知识》1997年第9期。
[6] 林淳钧:《潮剧三探》,《寻根》1998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