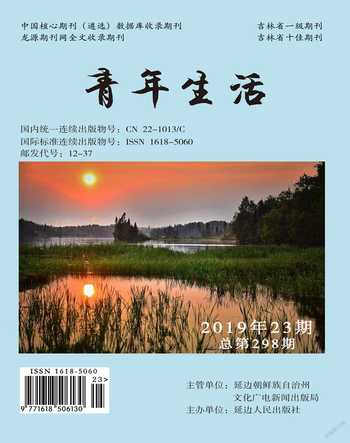探讨我国终身监禁制度的法律性质
罗艺林
摘要:终身监禁作为一种刑罚措施随着《刑法修正案(九)》的颁布而得到设立,在学界引起热烈的讨论,其中关于其的定性问题也是讨论的焦点之一,死刑立即执行替代措施说、死缓执行方式说、中间刑罚说以及无期徒刑执行方式说均非对终身监禁法律性质的准确界定。终身监禁的法律性质应当被界定为针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重特大贪污、受贿罪的犯罪分子所预先假设的一种的法律后果,这种定性不仅能够完善死刑缓期执行制度,而且符合死刑缓期执行法律后果的判断标准。
关键词:《刑法修正案(九)》 ;终身监禁;法律性质
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关注民生福祉,贯彻法治反腐精神,国家惩腐倡廉的力度不断加大的背景下,为了完善我国的反腐犯罪的刑罚体系,死缓执行的终身监禁制度在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九)》)第四十四条第四款针对特别重大贪污贿赂犯罪中得以确立。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解释》)第四条就终身监禁的适用情形问题做出了具体而详细的规定。
为了预防和惩治特重大贪污受贿犯罪,《刑法修正案(九)》设立了终身监禁的刑罚措施,终身监禁制度在立法初创和司法解释的出台时就引起了专家学者的热烈讨论,主要围绕着我国终身监禁制度的法律定位、法律性质、溯及力、时间效力、司法适用等问题进行研究。学界各大学派对此产生了诸多不一致的观点,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终身监禁不是一个独立的刑种这个观点在学界已经达成共识,但具体终身监禁的定性如何,学界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终身监禁的法律性质现在仍然饱受争议。有以下几个观点值得我们讨论。
一、死刑立即执行替代措施。
在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时,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就提出,根据法律中的父爱主义原则,谨慎适用死刑的政策,并依据每一个具体案件的特殊性,终身监禁的适用对象应当是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尤其是其中本应判死刑的,对其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有助于反映出刑法中的罪刑相适应原则,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有一些专家学者由此认为,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终身监禁的犯罪分子实际上是本应当判处死刑刑罚的,所以他们主张把终身监禁作为死刑立即执行的一种替代措施。
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我国的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之间多年来存在巨大间隙因终身监禁的确立而得到了有效填补,完善了我国的刑罚结构,在实务方面客观上确实减少了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但不能据此提出终身监禁就是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措施的观点。第一,从字面解释,“替代”顾名思义就是替换取代的意思,即替代者与被替代者是不能共存的。由此可以知道,如果死刑立即执行制度能够由终身监禁制度所替代,则死刑立即执行就应当被终身监禁全部替换取代。但事实上,终身监禁制度仅规定于贪污受贿犯罪中,适用范围远比死刑立即执行的小,且贪污受贿犯罪案件依然保留着死刑立即执行这一刑罚措施,难以替代。第二,从立法的角度来看,终身监禁附属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犯罪分子被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是能够适用终身监禁的基础,死立执与死缓之间在适用条件上存在较大的不同之处。我国《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死刑的适用对象为犯罪分子的罪行极其严重。对于不需要立即执行的死刑犯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相比之下我们不难知道,两者都有着共同前提的死刑类型,即罪行极其严重,但两者的区别在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不要求立即执行,即需要存在其他可以宽宥的情节,把终身监禁当作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措施事实上混淆了刑法设定的适用条件,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第三,从司法的角度来看,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贪污受贿犯罪分子在《刑法修正案(九)》实施之前或之后都可以适用终身监禁制度。在《刑法修正案(九)》颁布之前的情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同时决定终身监禁是刑法溯及力中的从旧兼从轻原则适用的结果,并不能说明终身监禁就是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措施;而在《刑法修正案(九)》实施之后,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同时决定终身监禁是以具体犯罪的法定刑为基础的,是现行法律框架下法官行使的自由裁量权的结果,也不是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措施。
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执行方式说。
有的学者认为,根据贪污受贿的犯罪分子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之前的表现来同时决定是否下达适用终身监禁的判决,这与传统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有所不同,相关的立法理由也说明将该新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方式定性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执行方式。
笔者反对该观点。从立法理由的角度来说,很难得出终身监禁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执行方式的结论,“判处死缓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采取终身监禁的措施”作为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阐述的立法理由之一,减为无期徒刑之后终身监禁并不能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法律后果做出限定。被判终身监禁的判决依然属于死缓的判决,但是在死缓判决中对法律后果进行了预期假设,该预期假设的法律后果是否能够实现,关键要看服刑人员的死缓的两年考验期内的表现。所以,从立法理由的角度来看,终身监禁并不是死刑缓期执行的执行方式,而是死刑缓期执行的法律后果。
三、中间刑罚
无可否认,站在死刑立即执行的立场上看,终身监禁是部分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措施。倘若是从死刑缓期执行的角度上看,中间刑罚作为终身监禁的法律性质更为突出,从概念上理解,中间刑罚是指同一刑罚可能由于执行方式的不同而不同从而形成的,存在与最重与最轻刑罚执行方式之间的、严苛程度居中的刑罚执行方法或特殊刑罚措施。
笔者反对这个主张主要有两个理由:第一,该观点可能致使终身监禁的适用范围不适当的扩大。《刑法修正案(九)》中规定因犯贪污受贿罪本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被告人是终身监禁的适用对象,而中间刑罚主张,本应判死刑立即执行的人和本应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人是终身监禁的适用对象,持这种观点无疑使得终身监禁的适用范围不恰当的扩大。第二,刑法规定的适用终身监禁的逻辑顺序表明该说不成立。用体系解释方法对《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结构进行分析:第一款中的第三项规定了贪污罪死刑的量刑标准;而终身监禁规定在了第四款,“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成为终身监禁的前提。因此我们不难看出,从死刑立即执行到死刑缓期执行再到死刑缓期执行暨终身监禁的顺序应当是适用终身监禁的逻辑顺序。该顺序中可以知道,死刑立即执行、死刑缓期执行、终身监禁三者的逐渐限缩的从属关系,死刑缓期執行属于死刑立即执行,而终身监禁属于死刑缓期执行的范畴。但是按照中间刑罚的逻辑顺序,在刑法中,关于贪污受贿罪死刑的规定无论是从重到轻还是从轻到重,都应该是死刑—终身监禁—死缓,或者死缓—终身监禁—死刑,即终身监禁都是出于死刑和死缓之中。该逻辑顺序与从法条分析出来的逻辑顺序,即终身监禁属于死缓范畴相违背。
四、无期徒刑执行方式说
有学者主张终身监禁作为无期徒刑的执行方式之一,是因为其认为无期徒刑可能出现的后果和应然的属性。有学者称,终身监禁主要依附的对象不是死刑缓期执行的判决,而是实际执行的无期徒刑,终身监禁所具有的从属性质,决定了其从属于无期徒刑的具体执行过程中。笔者亦不赞同此种观点。
第一,该观点违背了终身监禁的立法目的。立法创设终身监禁制度的目的的第一方面在于限制适用贪污受贿罪死刑立即执行的刑罚措施。无期徒刑和死刑立即执行两者的存在并不冲突矛盾,也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无期徒刑的适用不能达到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目的。立法创设终身监禁制度的目的的第二方面在于缩短了贪污受贿罪中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执行的空隙,如果说终身监禁是无期徒刑的执行方式,并不能达到缩小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执行的间隙,反而还加重了无期徒刑的严厉程度,使得无期徒刑的刑罚力度更重于死刑缓期执行,导致我国原本就不合理的刑罚结构更进一步不合理。第二,该观点背离了刑法的有关规定。《刑法》规定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可以同时决定终身监禁。而不是将终身监禁规定在判处无期徒刑的条款中,而是规定在死刑缓期执行的条款中已经能够有所说明。立法者亦没有将终身监禁作为无期徒刑的执行方式。第三,该观点的定性片面化。满足两个前提条件才能够适用终身监禁制度:前提一为判决前提即要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前提二为执行前提即死刑缓期执行减为无期徒刑。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倘若犯罪分子被判无期徒刑而非死刑缓期执行,则不能同时决定终身监禁;反之亦然,即被判死刑缓期执行同时决定终身监禁的犯罪分子,并且仅在死刑缓期执行减为无期徒刑的前提下才能够执行终身监禁这一刑罚措施。所以,关于终身监禁的定性问题我们要做全面的分析和考虑,仅仅把目光放在死刑缓期執行的判决上或者是无期徒刑的执行中都是不够全面的。
五、死刑缓期执行的法律后果
有学者主张,将终身监禁的法律性质定性为是针对被判处死缓的重特大贪污受贿罪犯罪分子所预设的一种死刑缓期执行的法律后果。笔者赞同该观点。
其一,把终身监禁的法律性质定性为死刑缓期执行的法律后果有助于完善死刑缓期执行的制度。我国本着“重刑主义”的思想,制定的配套刑罚体系结构有着死刑过重、生刑过轻的固有缺陷。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执行之间存在巨大间隙是该缺陷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该缺陷严重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为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能够更好的贯彻,就应当加重生刑减少死刑。而终身监禁制度的创设就能很好的缩短了贪污受贿罪死立执和死缓之间的空隙,把本应判死立执的部分案件有回旋的余地,划入死刑缓期执行的范围中,完善死刑缓期执行制度,使得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范围有所缩小,扭转死刑过重、生刑过轻的局面。终身监禁在缩小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范围的同时加大了死刑缓期执行的惩罚力度和严厉性,能够使从死刑立即执行到死刑缓期执行暨终身监禁再到一般死刑缓期执行的刑法惩罚力度由重到轻的协调衔接,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更好体现。
其二,根据死刑缓期执行法律后果的标准进行判断,主张将终身监禁的法律性质定性为死刑缓期执行的法律后果是符合该标准的。有的学者提出,该判断标准应当是:在死缓考验期满后再确定,但是,在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同时决定终身监禁,犯罪分子被判终身监禁的标准应当是看在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之前的行为表现。所以,不能将终身监禁的法律性质定性为死刑缓期执行的法律后果。笔者不赞同该主张。依照《刑法修正案(九)》的规定,终身监禁制度仅适用于贪污受贿罪,即是规定在刑法分则之中,这与一般的将法律后果规定在刑法总则之中有所不同,这样特殊的立法方式体现了终身监禁的特殊性。适用终身监禁要经过两个阶段,即判决预期假设阶段和判决实际执行阶段。处于判决预期假设阶段,根据犯罪分子被判死缓之前的具体犯罪情节,确定死缓考验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并终身监禁作为死刑缓期执行的法律后果之一,而替代了刑法总则中的死刑缓期执行考验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的法律后果。判决预先假设会出现终身监禁的后果,但是未必会执行,还需要经过第二个阶段,即判决实际执行阶段。判决实际执行阶段包含两种,即死刑缓期执行两年的考验期的执行和两年期满后的执行。在这个阶段适用终身监禁和适用死刑缓期执行的其他法律后果没有什么区别。
综上所述,为了平衡死刑缓期执行暨终身监禁与刑罚目的之间的冲突,更好的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完成实现法治国家现代化的目标,应当明确终身监禁制度的法律定位,准确的适用终身监禁,在司法实践中才能做出公正合理有效的判决,保证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
参考文献
[1]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 . 刑法修正案( 九 ) 最新问答 [M]. 北京 : 法律出版社 ,2015.
[2]赵秉志:《论中国贪污受贿犯罪死刑的立法控制及其废止——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现代法学》2016年第1期。
[3]陈兴良:《贪污贿賂犯罪司法解释:刑法教义学的阐释》,《法学》2016年第5期;
[4]黄永维、袁登明:《〈刑法修正案(九)>中的终身监禁研究》,《法律适用》2016年第3期。
[5]王志祥:《死刑替代措施:一个需要警惕的刑法理念》,《中国法学》2015年第1期
[6]赵秉志:《中国死刑替代措施要论》,《学术交流》2008年第9期。
[7]黎宏:《终身监禁的法律性质及适用》,《法商研究》2016年第3期。
[8]赵秉志、商浩文:《论死刑改革视野下的终身监禁制度》,《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9]黄丽勤:《贪污、受贿罪终身监禁的司法适用问题》,《兰州学刊》2017年第2期。
[10]黎宏:《终身监禁的法律性质及适用》,《法商研究》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