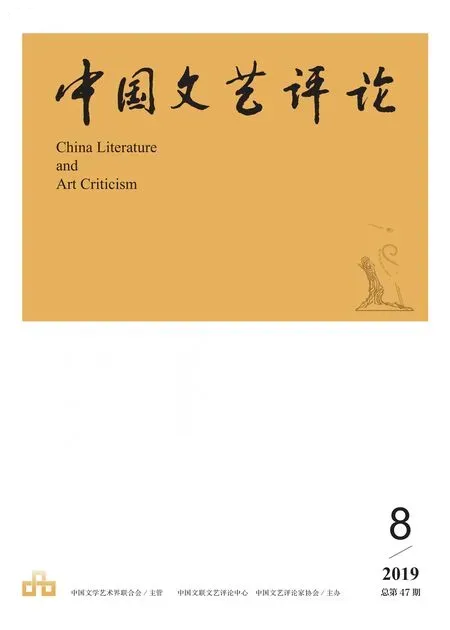经由文学翻译理解当代中国
——日本文学翻译家泉京鹿访谈
采访人:刘成才
刘成才(以下简称“刘”):泉京鹿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繁忙的翻译工作中接受访谈。您是日译中国当代文学在日本最畅销的翻译家,您翻译的余华的《兄弟》、周国平的《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等小说在日本销售得非常好,打破了日译中国当代文学只有高校及科研机构中国文学研究人员阅读的局限,让日本更多的普通读者也阅读并喜欢中国当代文学,您称得上是中国当代文学在日本的翻译与传播最直接的参与者与见证者。
泉京鹿(以下简称“泉”):过奖了!我纯粹出于喜爱翻译中国当代小说,非常荣幸能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我非常乐意就翻译中国当代文学的感受做交流,请多多批评,帮助我更好地进行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工作。
一、喜爱与困惑:翻译中国当代文学的契机
刘:我们先从您的求学经历谈起,这有助于了解您的翻译。您是哪一年考入费利斯大学的,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您大学时的专业是日本文学,为什么会学习汉语呢?
泉:我是1990年考入费利斯大学的,这所大学是日本著名的女学院,甚至有人认为是日本第一女校。费利斯实行的是贵族式教育,主要以文学、美术、音乐、高尔夫等为主,全面培养女生的个人修养。能考入这所大学的女生家庭条件相对较好,日本大学的男生找女朋友喜欢找费利斯的女生,一是因为家庭条件好,更因为费利斯大学的女生个人修养高,生活相对会更幸福。费利斯规定所有学生必须学习第二外语,很多学生选择的是法语、西班牙语等欧洲国家语言,我觉得学习全然陌生的语言会很困难,日语中很多汉字来自汉语,它们在汉语中是什么意思呢?出于这种好奇,我选择了汉语作为第二外语。费利斯选修汉语的学生非常少,没有专职的汉语教师,老师是非常勤讲师。当时给我们上汉语课的是一桥大学的松永正义老师,松永老师是日本著名中国文学学者,他常会让我们和一桥大学的学生一起学习汉语,可能正是因为松永老师我才会喜欢汉语并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吧,尽管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刘:您第一次到中国是什么时间?那时候对中国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泉:我第一次到中国是1991年夏天,当时松永老师组织学生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交流活动,我参加了这个活动,见到了传说中的美丽北京,登上了长城,参观了故宫,还到大同的云冈石窟去参观,第一次直观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更重要的是结交了很多中国朋友,回到日本后,他们用日语给我写信,介绍中国文化,让我对汉语更感兴趣了。大学毕业后我工作了两年,1994年再次到北京大学留学,专门学习汉语。
刘:您从北京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帮助日本NHK电视台做节目,和翻译似乎没有关系,后来是怎么开始翻译第一部译作《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的?
泉:我在帮助日本NHK做节目期间,认识了旅日作家毛丹青老师,毛老师在日本用日文写作,也翻译中国文学作品,认识很多中国作家。200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和毛老师在聚会上遇到了周国平老师,提到周国平老师非常有名的《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毛老师便问我有没有兴趣翻译这本书,但因为我汉语学习得不好,我不敢相信自己有能力翻译。毛老师非常相信我,把我推荐给日本出版社,帮我联系出版事宜,于是才有了《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翻译出版。可以说,毛丹青老师是我走上中国当代文学翻译道路的真正老师,没有他的鼓励与帮助,我极有可能不会从事翻译工作。
刘:《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在日本销量非常好,一部哲学书受到日本读者如此喜欢,说明您的翻译很成功。
泉:不是我的翻译成功,是《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这本书表达的父女亲情打动了日本读者。很多中国朋友听说我要翻译《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都告诉我这本书思想很前卫,很难翻译,但我翻译后发现,这本书表达的父女亲情是中国和日本读者共通的情感,虽然是哲学著作,但周国平老师用口语化的表达让读者理解起来较为容易,所以翻译后在日本出了7000册,相对于一般译作3000册的数量,这已经很高了,出乎我的意料,也让我对翻译有了信心。
刘:此后,您陆续翻译了田原的《双生水莽》、安妮宝贝的《再见,薇薇安》、成君忆的《水煮三国》《水煮西游记》等多部作品,也是因为这些作品代表中国年轻人的流行文化吗?
泉:可以这么说吧。我学习汉语之后,就想知道现在的中国年轻人到底在阅读什么,他们对当代世界的看法是什么样的,所以就到东京的一些大型书店去找类似的中国当代小说。但很遗憾,即使是在神保町这样书店比较集中的地方,也很难找到,日本人更喜欢的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小说,对中国文学喜欢的是古典文学,所以中国文学翻译书在书店只有很少的一部分,销量不好,价格很高,年轻人没能力购买,就更没有机会阅读,中日两国年轻人就缺少了文学这一非常重要的交流渠道。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之外,我还连续十多年在日本报纸《朝日新闻GLOBE》开设“从北京的书店”专栏,主要介绍中国畅销书,经常收到很多读者来信询问介绍的中国畅销书有没有日文版,他们非常想看,想更多地了解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与情感。每次收到来信,我都会有种莫名的使命感,鼓励自己把更多的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日文,让更多不懂汉语的日本普通读者阅读。我相信文学的力量,特别是年轻人间的深入了解,会潜在地改善中日两国的关系。
刘:后来您为什么会翻译余华小说《兄弟》?日本年轻人喜欢阅读《兄弟》吗?
泉:我读到《兄弟》的时候,小说只出版了上部,这是我读的余华的第一部小说,读后非常喜欢,但没有认识余华的机会。后来和毛丹青老师一起参加作家会议的时候,认识了余华,和他聊到《兄弟》,说了自己读后的感想,以及把小说翻译成日文的想法。余华当时在日本名气已经很大,很多小说都已经被日本翻译家饭塚容老师翻译成日文,但当时饭塚容老师非常忙,抽不出时间翻译这部小说,余华就非常信任地把小说交给我翻译。余华老师丝毫没有著名作家的骄傲,对人非常和善,我多次打扰和请教也不厌其烦,一直到翻译结束,我都有点不敢相信能够翻译余华小说,我想,作为中国当代作家代表,余华的人格魅力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影响力不断扩大的原因。《兄弟》在日本首印一万册,很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图书馆排队购买,现在已经购买不到了,网上炒至一万多日元一本,可见日本读者对余华这部小说的喜欢,我想,出版社应该很快会加印的。
二、青年与女性:翻译的选择与成功策略
刘:我注意到您翻译的女性作家较多,这和您作为女性学者的阅读爱好有关系吗?
泉:应该是吧。日本很多中国文学翻译家是大学等研究机构的学者,他们的翻译更多是基于在研究中的学术判断,我不是研究者,我的翻译是基于自己的阅读爱好,选择卫慧、安妮宝贝、田原等女作家,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喜欢她们的小说,可能身为女性,更容易产生共鸣吧。
刘:您和作家之间会经常联系吗?能否谈谈和她们交往中的有趣片段?
泉:翻译带给我最大的幸福是结识了很多有趣的作家朋友,在翻译过程中和她们交往并成为莫逆之交,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带给我的幸运。比如卫慧,2003年出版社安排我和她见面,但聊天时发现我们在工作和情感很多方面兴趣相似,所以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生活中有什么高兴事都一起分享,不开心的事也一起分担,她结婚,生子,定居美国,离异,回上海定居,都第一时间告诉我,这么多年一直保持着很好的私人友谊。和其他女作家,如安妮宝贝、田原等人,也是因为翻译而成为好友。2010年我因为女儿要出生而不得不回到日本,至今我一直都非常后悔离开北京,虽然每年都要去中国旅游一两次,但一直希望能够再次回到北京长期居住,因为那里有很多朋友。
刘:您在翻译中国当代文学的过程中,感觉最困难的是什么?
泉:最困难的是如何让日本普通读者通过文学了解当代中国人的真实生活,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日本普通读者所了解的中国更多是文化意义上的,他们在中学阶段都学习过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经典古诗词,但今天的中国已经有了巨大变化,日本普通读者却没有了解的途径。所以,我在选择要翻译的小说时经常会感到难以选择,不知道哪一个作家的小说翻译成日文后更能引起日本普通读者的共鸣。夸张一点说,我感觉最困难的就是如何让翻译跨越中日两国文化的障碍,让日本普通读者更容易地通过中国当代小说了解当代中国的真实生活,走进中国真实的社会。
刘:您在翻译中是如何克服中日文化差异让日本读者更容易理解与阅读的?
泉:首先,我的翻译主要选择年轻作家的小说,像卫慧、田原、安妮宝贝、郭敬明、九把刀等,我感觉,年轻作家多表现当今中国年轻人的生活,这会让日本年轻读者产生亲切感,接受起来更轻松,只有年轻人互相了解了,中日两国的深层次交流才更有希望。比如2010年我翻译郭敬明的小说《悲伤逆流成河》,是由日本最著名出版社讲谈社引进出版的,他们认为郭敬明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主要是因为他表现了当代中国的魅力,而以郭敬明为代表的年轻一代人的生活是未来中国发展的象征,日本通过政治、经济等所了解到的当代中国,远没有通过小说所了解到的中国真实。2010年10月,日本著名娱乐杂志《AERA》封面人物就是郭敬明,可见日本对中国青年的重视。其次,我在翻译中会尽量从年轻人角度理解小说。我在阅读时经常遇到不知该如何表现的汉语,这时我会把自己当做完全不懂汉语的日本普通读者,向身边的朋友、出版社编辑、作家本人等反复请教,直到把难以理解的汉语意思用最简单的日文表现出来。遇到实在难以翻译的汉语,我就会去小说中描写的现场寻找语言的感觉,我在北京生活时,经常步行参观北京的很多胡同,也曾经去过上海、山西、江苏、云南等很多地方体会当地人的真实生活,这对我融进中国人的生活,体会汉语独特的表达非常有帮助。我感觉,汉语和日文在表现生活的本质上是相通的,应该能够很好地表现对方的生活,让对方的生活变得鲜活起来,如果做不到的话,那更可能是译者的责任。
刘:您认为对翻译家来说,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母语能力还是外语能力?
泉:我感觉应该是母语能力更重要一些。翻译从表面看是语言和文化转化,把汉语转化为日语,它要面对的最终还是日本读者,如何能让日本读者更容易地理解中国当代小说,考验的不是翻译者的汉语能力,而是日语能力。对我来说,中国当代小说是用典雅还是通俗的语言来写的,或者是用方言来写的,这都不重要,我具备基本的汉语阅读能力,能够理解小说就行了,重要的是如何让日本不懂汉语的普通读者理解小说,他们有时候可能不需要多么深刻的阅读,翻译者的任务是带领他们阅读与理解。
刘:所以,您翻译的中国当代小说在日本销量都很好,也因此有人批评您的翻译只选择流行作品,认为畅销作品不一定是好作品,甚至有人批评您的翻译“没有节操”,你如何看待这种批评?
泉:我听说过很多类似批评,刚开始感觉很委屈,自己辛辛苦苦付出了时间和精力还受到批评,很不理解,现在已经不在意了,更多的是当做对自己翻译工作的鞭策。日本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多是由大学等研究机构专业的学者教授担当,他们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翻译对他们来说是工作之外的爱好,所以他们的翻译可以选择更具有学术意义的作家作品,他们翻译的很多中国当代小说刊登在专业的学术期刊与文学期刊上,阅读也局限在研究圈子内,普通读者根本接触不到,更阅读不到。但我刚开始从事翻译的时候,还有在电视台广告公司兼职的工作,后来辞职做专业翻译者,没有收入,生活主要依靠父母支持,2010年我女儿出生后,我在带女儿之余翻译,收入主要依靠我爱人,生活压力非常大。所以,我的翻译就要考虑出版成本与翻译收入,不能辛辛苦苦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最后还要付出经济成本,这样的话,我的翻译也很难持续下去。更重要的是,我也认为畅销作品不一定是好作品,但这个“好”究竟应该由谁来判断,是由少数专家学者还是由更广泛的普通读者来判断?如果一部小说翻译之后没有读者阅读,它的文学价值该如何体现?所以,我认为文学的价值更应该体现在阅读上,能被更广泛的读者阅读,至少它的价值得到了体现。具体到中国当代小说,本来被翻译成日文的已经很少了,读者也很少,现在能被翻译成日文,总比没有被翻译成日文要更有价值一些。
刘:您选择作品的原则是什么?会参考中国重要的文学奖,如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吗?
泉:我选择作家作品大致有两个原则:第一,我非常重视与作家之间的关系。我本科学习日本文学,比较感性一些,重视感情,刚才曾谈到与被翻译的很多作家都成为好友,友谊一直保持到现在,对我来说,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非常重要,翻译就是一种托付,作家基于友谊把小说托付给我,我就有责任把小说翻译得更好,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很多作家对我非常照顾,能够理解翻译的艰辛。第二,翻译的作家作品要在中国非常畅销。我感觉,一部小说如果在中国阅读的人都不多,翻译成日文的话也很难有太多读者,中国当代小说要想在日本影响更广泛一些,必须让更多读者阅读,没有读者,谈不上影响。选择作家作品时也会参考茅盾文学奖之类的,看有哪些小说影响比较大,但更多的还是自己阅读后再决定。
刘:我在东京很多书店调查后发现,中国当代小说在日本出版很难,销量很少,难以保证盈利,而您翻译的小说在日本销量都很好,甚至是中国当代文学在日本销量最好的,您是如何说服日本出版社的?
泉:日本出版业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萧条以后对出版小说非常谨慎,即使是文艺春秋、讲谈社、河出书房等非常大的出版社,要想说服他们出版也很困难,这不仅仅是对中国当代小说,对海外文学也一样。由于日语表达的特殊性,中国当代小说翻译成日语时字数通常会增加1.5到2倍,定价相对很高,普通读者难以购买。例如余华的小说《兄弟》分为上下部,日译本很厚,我在翻译完上部时,就从中国收集了大量数据,告诉出版社这部小说在中国一出版销量就达到了50万册,到翻译结束时已经销售了100万册,小说即将在欧洲国家出版英语、法语等译本,全球很多国家已经决定出版翻译本,通过这些直观数字,说服出版社决定出版《兄弟》。其他小说的翻译与出版与《兄弟》类似,翻译时很辛苦,要付出很多时间与精力,出版过程更辛苦,要付出更多,很多时候,翻译者可能比作家的付出更多。
刘:问一个非常私密的问题,您翻译的收入如何?
泉:这个问题你如果问我爱人的话,他的回答可能会更真实一些。日本翻译的收入都是出版后才结算,翻译期间没有收入,余华的《兄弟》我翻译了两年,在这期间没有任何收入,都是依靠我爱人。即使出版,由于出版的数量很少,为了销量,文学书定价相对较便宜,翻译家几乎没有什么收入。以余华的小说《兄弟》为例,上下册定价将近4000日元,出版一万册,版税为12%,余华能够体谅翻译的艰辛与不易,对我非常照顾,我和他每人的版税为6%,很多书的翻译版税只有4%,你可以算算翻译者的收入是多少,对两年的时间与精力付出来说,翻译是最辛苦且回报最少的。经常有读过我翻译小说的朋友表示很喜欢翻译,当我和他们谈到翻译的收入时,很多人都表示很惊讶,不敢相信。
三、多元化与超越性:翻译与中国当代文学世界性
刘:您曾担任中国外文局《人民中国》杂志日文版专家,还固定每三个月一次在日本报纸《朝日新闻GLOBE》介绍中国畅销书,现在还做这个工作吗?
泉:《人民中国》杂志日文版专家在我回国后就不做了,因为女儿出生后,我要花很多精力照顾女儿和家,没有精力再担任《人民中国》杂志日文版的审校工作。在日本报纸《朝日新闻GLOBE》开辟专栏介绍中国畅销书到现在还一直在做,持续了十多年,在10月7日最新一期专栏中,我就介绍了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以及张皓宸的《听你的》,同时还介绍了在北京书店畅销的一些书。除此之外,最近几年受日本文艺家协会的委托,还为每年出版的《文艺年鉴》撰写“中国文学概观”,2018年介绍有刘震云的《吃瓜时代的儿女们》、鲁敏的《奔月》、严歌苓的《芳华》等很多作家作品,让日本读者对这一年的中国文学有大致的了解。
刘:您阅读关注中国当代作家作品已经二十余年,您感觉这二十多年中国当代文学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泉:我感觉这二十多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变得更加多元了,对人的表现也更加宽容。田原的《双生水莽》中表现年轻人因物质的极大丰富导致精神的极度空虚,他们无法用语言表现精神上的迷茫与空虚,只能在焦躁与惶惑中挣扎,田原曾说她感觉“一直在水的深处,上不了岸”,所以我把小说名字翻译为《水の彼方》(水之彼岸),以更好地表现小说内容,这种描写在田原父辈那一代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还有卫慧的小说里面有很多女孩对情感、对性爱的追求,与1980年代中国当代小说多表现生死、人与体制的矛盾等严肃主题大相径庭,郭敬明的小说《悲伤逆流成河》描写了悲惨阴暗的高中生活,有怀孕、堕胎、学校暴力等,与年长作家所表现的学校生活完全不同,但依然有大量的读者阅读并喜爱。这说明中国当代文学越来越多元化,更说明中国社会也越来越多元化,对情感的多样化也更具有包容性,我坚信随着中国不断发展,一定会涌现出更多优秀作品被其他国家与民族的读者阅读接受。
刘:从翻译家的角度来看,中国当代文学还存在着哪些缺点与不足?
泉:我谈谈在翻译中遇到的两个情况:第一,中国当代作家对弱势群体要抱持更多的善意与理解。中国当代小说中有一些对残障人士的取笑与逗乐,这在日本是不可能出版的,日本有“放送伦理法”保护障碍者的权益,不用残疾人的称呼而用障碍者,马路上专门的标识也注明是障碍者专用。2011年,我受日本白杨社委托翻译中国作家彭学军的儿童小说《腰门》,小说翻译结束后遇到了困境,小说里有一个兔唇女孩叫青榴,作家在小说中对这个女孩非常同情,但日本的“放送伦理法”规定给儿童阅读的书不能有任何歧视成分,即使是同情也会被判定为歧视。日本出版社对版权非常重视,删减必须得到作家同意,我给作家建议把青榴这个女孩的内容删掉,她不是小说主要人物,删掉不影响小说整体性,但作家不同意删掉,最后小说无法出版。我在翻译余华的小说《兄弟》时也遇到这种情况,小说下部第三章写李光头成为福利厂厂长后,带着两个瘸子、三个傻子、四个瞎子和五个聋子到照相馆拍照后去上海到处告诉商店和公司老板哪个是瘸子,哪个是傻子,哪个是瞎子,哪个是聋子,依靠别人同情得到加工纸盒的长期合同,使福利厂扭亏为盈并上交巨额利润,这么写在中国没问题,在日本出版是不可能的,好在余华非常能够体会翻译的不易与中日文化差异,同意删减,小说才能顺利出版。第二,中国当代作家的写作还要具有一定的超越意识,小说应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特定的区域、文化与语言,才能更容易被别的文化与语言的读者接受,产生广泛影响。2017年12月19日,日本媒体《日本经济新闻》在“夕刊”刊登了干场达矢的文章,认为余华小说表现了对“底层普遍性的共鸣”,是“从亚洲出发走向世界”的杰出作家。可见,日本更看重的还是中国当代小说的普遍性意义,余华和阎连科的成功,对中国当代作家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刘:著名汉学家竹内实老师夸奖您的翻译是“翻译界的新尝试,因为男学者都不会这样翻译”,作为专业翻译家,您如何看待与日本中国文学教授翻译的区别?
泉:竹内实老师可能是说男学者的翻译以学术性为主,而我的翻译以通俗易懂为主吧。我和竹内实老师见过很多次,也向他请教过很多翻译上的问题,对我的翻译帮助很大。我也经常阅读日本中国文学教授翻译的中国当代小说,他们有时候可能过于重视学术性,例如,遇到实在难以翻译的词语,日本中国文学教授会使用括号加注释的方法,但这种方法会破坏阅读的连贯性。而我在翻译的时候如果遇到实在难以翻译成日文的,就直接用汉字,好在汉语和日文有共同的汉字在使用,这不会影响日本读者的阅读。当然,我和日本中国文学教授的翻译所面对的读者不同,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也自然不同。
刘:您在翻译时会和日本中国文学教授交流吗?
泉:我和很多日本中国文学教授的关系都很好,除了竹内实老师,还有饭塚容老师,谷川毅老师,藤井省三老师等,他们对我翻译的帮助很大。特别感谢藤井省三老师,我在北京大学留学的时候藤井老师在北大访学,我和日本学生经常去他住所请教中国文学问题,藤井老师虽然是东京大学教授,但对学生非常好,即使和他没有师生关系,他也会当做自己的学生来关心。我在翻译中遇到困难,经常半夜给藤井老师发邮件,他通常都是清晨回复,我翻译的小说出版后,藤井老师都会在报纸或学术期刊上发表书评,虽然不是师生关系,但我一直把自己当做藤井老师的学生。
刘:您的翻译在中国学界影响越来越大,有很多人在研究您的翻译,也有人把您的翻译当做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您如何评价您的翻译?
泉:非常感谢中国陌生的朋友能够关注我的翻译。虽然我翻译了十多本中国当代小说,但每次去中国,在北京的书店里看到很多的日本文学被翻译成汉语的时候,我就会感到惭愧,觉得自己还不够努力,每当读到好的中国小说时,总会想把它翻译成日文介绍给日本读者,但因为精力、经济的原因做的远远不够。我非常感谢这种翻译工作,它让我结识了很多才华横溢的中国作家,非常荣幸和他们成为朋友,翻译也让我的个人生活和人生更加丰富充实,我非常享受翻译的过程。希望中国作家能创作出更多的优秀作品,也希望更多中国当代小说能够早日翻译成日文,走进日本读者的阅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