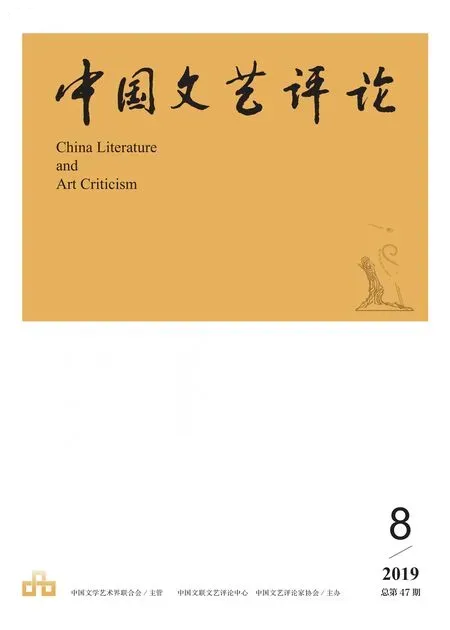以虚写实 以实喻虚
——评原创民族舞剧《天路》
刘 忆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把人间的温暖送到边疆,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漫长,各族儿女欢聚一堂……”雄踞在世界脊梁之上的天路,是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伟大壮举,承载了太多神奇而温暖的故事,是“走进人间天堂”之路。这一新中国成立后可歌可泣的“天路”故事,经由国家大剧院、北京歌剧舞剧院联合制作推出的原创民族舞剧《天路》,荣摘第十六届文华大奖。作为时下主旋律舞剧之一,《天路》通过藏族姑娘央金的“眼睛”见证了上世纪70年代“天路”的修建过程,全剧以男主角卢天的一段生命轨迹为主线,串起了家国爱和天路情,在用舞蹈表现重大现实题材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以独特的艺术探索和实践舞动出新时代的“天路精神”。
一、平民英雄夯实天路基石
无论是文学、电视剧还是好莱坞大片,“大人物”退场、“小人物”登场的故事模式是近年来艺术创作的成功尝试。舞剧方面,将视角集中于“小人物”,展示“大情怀”,从最初的说教式、人物脸谱化和事件单一化的生硬表达逐渐在形式和内容方面进行调整,使主题和情感更加“润物细无声”,将英雄形象落实在平民身上,是编导不断实践探索和主旋律舞蹈创作的倾向。
随着社会文化的前进发展和多元变化,“英雄”这一概念,从最初帝王将相之类的人物如托马斯•卡莱尔的神明英雄、先知英雄、诗人英雄、教士英雄、文人英雄到帝王英雄,其内涵也逐渐宽泛和丰富起来,每个时代和社会形态都有不同的英雄出现,他们既是这个时代的代言人,又是这个时代精神的符号与象征。“中华民族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人们崇拜英雄绝不是崇拜‘英雄’的名号,而是崇拜英雄品质,通过崇拜被称为‘英雄’的人而强化自己身上的英雄品质,从而凭借自身固有及内化了的英雄品质迎战生活中随时可能遇到的艰难险阻”。英雄情怀在战争年代熊熊燃烧,早已融为历史的缩影与时代的精神。在和平年代的今天,我们也同样需要。
在英雄形象的塑造上,舞剧《天路》通过宏大的叙事背景,将英雄精神折射在普通人身上,将平民作为英雄形象的落脚点,着力聚焦男主角卢天的家国情怀,继而讴歌时代的英雄精神,兼具虚构与真实、典型与平凡,更加“接地气”。正如编剧罗斌所设计的,英雄“卢天”的名字别有寓意,倒过来就是“天路”,他所代表的并不是一个人,而是这条“天路”上所有平凡的筑路人,是拥有个性同时也反映时代共性的“这一个”。剧中,作为英雄符号的卢天是青藏铁路二期工程的一位普通铁道兵,他的父亲曾在青藏铁路一期工程建设中不幸牺牲,其母不愿意再失去儿子,要求他退伍参加高考。在母亲的要求和父亲的遗志之间,卢天彷徨踌躇,最终决定留下来和战友们一起筑路。没多久,他接到了退伍通知。正当准备离别时,地震降临,他因赶回塌方的隧道营救战友而壮烈牺牲……作为普通铁道兵的卢天,一方面有年轻人的顽皮、青春期的倔强,另一方面也有男子汉面对抉择时的硬气,是个“熟悉的陌生人”。在舞蹈处理上,编导筛选了人物成长过程中的几组动作进行浓缩,不但符合角色的情感诉求,同时再现了他的成长环境。例如卢天与父母三人的舞段,母亲关切时的前倾“抚额”、看到卢天摔倒时的“揪心”、生气时反复出现的“指”、卢天“捂耳朵”的反抗以及他与母亲身体相背的回避体语,既描绘出一个家庭的温馨,又勾勒出卢天成长过程中叛逆的一面。在作品情节的构架上,既有英雄的伟大与崇高,也不乏“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的琐碎,贴近现实的舞段增加了观众对人物想象的真实感和亲切感,将卢天的英雄品质和人物性格结合起来,使之立体化而又生动,接近艺术真实的本质,使角色更具人格魅力。
从舞蹈身体语言层面来看,舞剧后半段着力表达卢天的英雄之举——用生命之躯铺就了天路,为舞剧赋予了更崇高的象征和意义。这种叙事,既是个体的叙事,同时也属于民族和国家的叙事。比如当卢天面对母亲的要求纠结去留时,看到了战友们挥汗如雨地奋勇筑路,作为个体的卢天自觉服从了群体的意志,决定回到筑路队中和大家一起早日修成铁路。又如当他退伍准备离别时,地震降临,他毅然放下行囊赶回去营救战友,群体意志又一次高于个体意志。编导通过平民英雄的个人叙事,深入挖掘其个体身体言说背后对“家国情怀”的崇高信仰,也唤起观众对这一历史真实事件的敬意与“天路精神”群体的敬仰。
二、道具口琴奏响天路之音
关于现实题材舞剧创作的困难,于平认为“一方面,在于现实题材是发生在离我们较近的事件,没有‘深扎’的毅力和‘潜心’的情怀难以看清真相、发掘新意;另一方面,在于现实题材中的日常生活形态对于舞蹈表达是一种全新的经验,需要在观众的‘日常理解’和舞蹈编导的‘诗性表达’中找到平衡点,建立新通道。”口琴,作为普通物品和日常道具,与平民英雄卢天的形象一致,是其身份的标识之一,强化了英雄的平民身份,实现了观众的“日常理解”。编剧和编导巧妙地将口琴作为天路精神的一条暗线,象征天路精神的继承与发扬,起到了推进剧情、交代人物关系、强化汉藏感情和承转的作用。口琴多次出现、琴声反复响起与舞蹈肢体语言进行有机结合,并将其融入作品结构,贯穿全剧,实现了舞蹈编导的“诗性表达”。序中,藏族姐弟在“石堆”旁遇到了青藏铁路三期工程建设者,触景生情之余,弟弟手捧口琴,双手微颤,一种强烈的情感涌上心头。突然,他跑向远处,身体微倾吹响口琴,借由琴声打破时空界限,仿佛回到了上世纪70年代的修建现场,男主角卢天由此出场。其后,卢天面对退伍高考与继续筑路的矛盾,坐在铁轨上蹙紧眉头吹响口琴,琴声抒发了母命与卢天匹夫之责的两难思绪。一段卢天和父母的三人舞自然进入,时而是父亲在一线持枪训练的矫健身姿,时而是母亲独自守在家中的期盼和落寞,时而又是一家三口在一起的日常琐粹与温馨,所有的一切为后面的小情大爱埋下了伏笔。
从语言学角度来看,“口琴”在剧中既有换喻又有隐喻,具有“双喻”性。父亲牺牲后,口琴作为留给卢天的遗物,既是父亲形象的换喻,也是天路精神的隐喻。如悼念婴儿后,卢天将口琴贴在胸口,好似与父亲隔空对话,心中五味杂陈。又如卢天决定留下来继续筑路的舞段,口琴与舞台后方火车头上坐着的父亲形成空间的跨越与交错。阴阳虽两隔,但卢天与父亲在精神上借由口琴得到了合奏与共鸣,完成了天路使命的传递与承接。
如果说“口琴”在前几幕还是连接父子理想志愿的媒介,那么从第四幕弟弟索朗吹响口琴开始,“口琴”连接的内容就得到了拓展与升华。此时的口琴,不仅象征着卢天和父亲,更与姐姐央金准备送给卢天的藏靴一起形成两种象征符号,喻示了汉藏一家亲和军民一家情的主题思想。卢天壮烈牺牲后,青藏铁路三期工程的建设者从索朗手中接过口琴沉思端详……自此,“口琴”完成了父亲——卢天——索朗的转化,继而推进至青藏铁路三期工程整体建设者,这之间的连接如火炬传递,象征着几代人不忘初心、坚持不懈、前赴后继的天路精神,强化了汉藏军民的深厚情谊,将舞剧推向了情感的沸点。
三、汉藏同心交织天路之情
舞剧《天路》是一个既厚重又宏大的现实题材作品,无论是对舞蹈还是对音乐而言,都是一项极大的挑战。总编导王舸和编剧罗斌在舞蹈肢体创作和文本的叙事中,尽量用轻松的方式去触碰厚重的故事情节,用宏大的背景与先抑后扬交织的叙事情感铺陈该剧的艺术底色。
在舞剧的前四幕中,整体的叙述情感是有所克制的。即便是几个生死离别的舞段,编导都处理得相对冷静与收敛,期间,根据剧情发展穿插了喜庆祥和的“春种”、诙谐逗趣的“相遇”、热情奔放的“帽子舞”、众志成城的“拥军”、浪漫炽烈的“情愫”等特色舞段,既平衡了舞剧整体的叙述情感,又增加了舞蹈语言的丰富性和作品的生活趣味性。
如卢天父亲牺牲的舞段,除了舞台后区铁道兵在高原奋勇跋涉外,卢天和母亲在舞台前区的动作和速度都相对节制,情感释放较缓。编导在此为人物设计了一个“挥手”的慢动作,通过躯干的前倾与手臂的缓慢下落,用慢镜头似的处理方式外化了人物内心对亲人的呼唤与沉痛地怀念。在几组大幅度的双臂拥抱、上身后仰的动作后,母子二人从直立快速转至半蹲,背对观众双手前伸,这一背转后的压抑、拒绝和回避,将之前的痛苦以安静的方式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好似在空旷的雪域间无尽地寻找与等待。
从父亲牺牲——母子互诉悲苦——卢天独自望着口琴缅怀父亲,前后不足四分钟的时长,没有摇天撼地地痛哭嘶吼,也没有卢天独自凭吊哀苦的冗长。仅一个转身,便自然衔接到了弟弟索朗“偷口琴”的舞段。黑暗中,索朗悄悄躲在卢天身后,在几次试图偷琴失败后,他故作声响惊吓卢天并趁其不注意时将口琴偷走……编导运用夸张的手部动作“偷”、压惊时的“拍”和用力地“闻”等生活化动作,加大戏剧化效果,营造出一种轻松滑稽的主题氛围,充满了生活趣味,使之前的哀伤与痛苦得到了暂时的缓解与平和地过渡。
又如婴儿夭折的舞段,编导也尽量避开悲伤情绪的大面积渲染,以此为台阶,层层推进剧情发展,全面铺开卢天的“心路”。再如卢天牺牲的舞段,央金姐弟疯狂掘地之后,以静制动。弟弟索朗掏出口琴,发出一声呐喊,进而过渡至卢天母亲在儿子营地的回忆凭吊。舞剧中三次生命的别离,都不同程度地淡化了个体的悲苦,从叙述情感上着重凸显了舍小家为大家、先国后家的崇高精神。
从央金姐弟点燃台前的酥油灯开始,至舞剧尾声同名歌曲《天路》的唱响,全剧在近100分钟的情感集聚后,终于在最后的10分钟进行了叙述情感的反弹与彻底释放。舞台上,英魂重现,汉藏人民高歌欢庆,亲吻铁轨,敬献哈达。舞台下,青藏铁路工程的参与者、见证者和无数时代的同行者们在舞剧《天路》中得到了情感上的认同、心灵上的抚慰和精神上的共鸣,升华了主题,将全剧推向高潮。
四、虚实并置共筑天路之梦
青藏铁路是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穿越“生命禁区”的伟大壮举,不仅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更是连接汉藏人民的“连心路”。舞剧《天路》创作团队巧妙地通过艺术的手法,在天路所承载的现实意义和文化意义之上,将虚实之路在剧情、舞段和音乐的联结中同时展开并深化,最终超越“路”的本质意义,赋予了舞剧《天路》之“路”的多重含义。
第一,天路是现实中的青藏铁路。青藏铁路全长1972公里,连续冻土里程达550公里,最高海拔5072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对藏族人民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全面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在将近120分钟的作品里,舞台前方一直横陈着一条铁轨,与每一幕出现的枕木、隧道、火车头等铁路元素交织相映。作为现实中青藏铁路的模拟与再现,这条“路”既是舞台空间,又是舞台背景,交代了故事发生的地点与场景。

图1 民族舞剧《天路》
第二,天路是以男主角卢天为典型代表的铁道兵们的“心路”。前文所述,卢天是有血有肉、立体化的英雄形象,对于母亲的召唤和父亲的遗志,他也如普通人一样有内心的彷徨和纠结。在他的内心,有婴儿夭折后的痛苦与无力感;有与藏族姑娘央金间的美好情愫;有被告知退伍后的落寞与不舍;有在得知地震后毅然放下行囊奔赴营救时的坚定……具体在舞蹈呈现上,“纠结”舞段多出现交叉式的手臂动作,表现内心激烈的思想斗争;“悼念”舞段多以圆的动作展开,突出他内心的彷徨和无助;“情愫”双人舞中,“两个身体”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借助“围巾”拉近距离,逐渐由手的“相对”、头部的“相偎”、躯干的“相拥”,进而发展为背对背上下“相靠”的身体表达。空间处理上,通过三度空间动作造型的相互转换,将两人之间羞涩又纯洁的美好情愫展现得恰到好处;“牺牲”舞段中,通过“拖”“拉”“拽”等主题动作的不断重复,塑造其营救战友时义无反顾的英勇形象。每一个“心路”舞段都言简意赅,勾勒有序,既是卢天的“心路”历程,也是几代铁道兵们守护“天路”的缩影。

图2 民族舞剧《天路》
第三,天路是连接汉藏情谊和军民鱼水情的“连心路”。舞剧前两幕,主要以汉藏人民间个体的交流往来为主,从第三幕开始,编导迅速地将个体情感升华至群体情感的交融与共鸣。如藏区同胞慰问营地铁道兵的舞段、藏族女孩自发为铁道兵洗衣的舞段、军民携手共筑天路的舞段、汉藏人民共庆青藏铁路通车的舞段,编导均用藏族舞蹈“谐”“卓”等动作元素,以群舞的形式递次展开,各舞段间相互顺应承接,情感上环环相扣,烘托出汉藏军民之间浓浓的鱼水情。于卢天和其父亲而言,这条天路是他们生命历程中的最后一路,他们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洒在了天路之上,与藏族同胞心连心、共同守护。
此外,天路还是一条舞蹈艺术的“连心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反映汉藏军民鱼水情的舞蹈较为突出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1964年第三届全军文艺会演中的《洗衣歌》,一个是第七届全军文艺会演中的《酥油飘香》。由李俊琛编导、西藏军区政治部歌舞团创作演出的《洗衣歌》,通过藏族姑娘略施小计帮助解放军洗衣服的一个富有生活情趣的片段,表现了汉藏团结与军民友谊。“洗衣歌的成功,是历史的产物,是时代的精神,是汉、藏民族团结友爱的结晶。“文革”时期,唯有《洗衣歌》被周总理保护下来,成为流行时间长、地域广和普及率最高的舞蹈之一。”如果说《洗衣歌》中的军民情还停留在翻身农奴把歌唱的阶级情感上,那么由达娃拉姆编导、同是西藏军区政治部歌舞团创作演出的《酥油飘香》则是这种情谊的延伸与拓展,体现了新的军民关系。《洗衣歌》的时代,“西藏人民刚刚从黑暗的奴隶制的锁链中解放出来,他们的面容是舒展的,精神是愉悦的,对共产党、解放军充满了感激之情。”三十多年后,《酥油飘香》时代的“西藏人民不仅精神上早已获得解放,而且在物质文化生活上也得到了空前的满足”,他们对共产党、解放军的感情早已从感谢转化为汉藏军民深厚的鱼水情。
距《洗衣歌》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舞剧《天路》再现了当年经典的“洗衣”舞段,并在此基础上扩充阐释,强化了“洗”的动作性和戏剧性,最后通过将衣服“洗破”的夸张表达,进一步深化藏族同胞与驻地解放军的情深谊长。“洗衣舞”在当代的再阐释和运用,实则用舞蹈身体语言连起了传统藏族经典舞蹈艺术与现代舞蹈艺术风格之路,将之前的军民鱼水情与当代的军民一家亲形成有机结合,具有统一的舞蹈风格与精神旨归。
第四,天路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超越之“路”。在虚实之路的意义之上,舞剧《天路》还进行了超越与延展,扩大了天路之“路”的外延与内涵。这里的“路”具体有两层含义:一是解决各种问题的方法。青藏铁路气候恶劣、环境险峻、地质复杂,具有高原缺氧、冻土病害和生态脆弱三大世界性难题,修建困难极大。为了使青藏铁路早日进藏,以卢天父亲、卢天、老东北、小四川等为代表的筑路人自强不息,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共同攻克了一个个难题,终于实现了几代人的夙愿。二是心中所追求的目标。青藏铁路不仅是铁道兵和藏民的“连心路”,也不仅仅是雪域高原迈向现代化的“腾飞路”,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坎坷路”“奋斗路”。如今,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快,改革开放迎来新的局面,“一带一路”建设显现出重大发展,中华儿女拥有统一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目标,与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同舟共济,为建设促进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的“天路”作出新的贡献。
结语
作为反映主旋律的现实题材作品,舞剧《天路》所塑造的“平民英雄”形象“接地气、冒热气、有正气”,既表现了人物作为个体的平凡普通与情感诉求,又展现了个体在国家与信仰、爱与梦想之间的理想选择和崇高精神,具有潜移默化的感染力。道具“口琴”,一物双喻,在作品中既联结了结构与剧情,又联结了生死与民族、生活与精神,实现了观众“日常理解”与编导“诗性表达”的平衡,深化了汉藏军民的鱼水情深,促进剧情的自然推动与发展。通过虚实之路的并置与超越,将现实的天路意义放置于家国语境中不断延伸,从天路情转向家国情,将天路之路喻为中国富强之路和“中国梦”之路。全剧舞段形式多样、结构紧凑,有浓郁的藏族舞蹈风格,也有军旅舞蹈的创作特点,与叙述情感的先抑后扬形成完整统一,用舞蹈肢体语言解读了新时代下的“天路精神”,用艺术的形式讲述了现实背景下中国人奋斗的故事,是当下现实题材舞剧创作的一次有益探索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