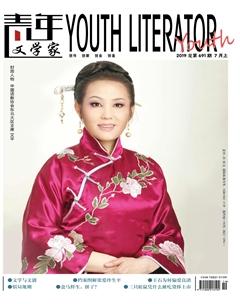世界文学维度下,青年作家写什么
第三届上海一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世界文学和青年写作”在复旦大学举行。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上海和南京两座城市有着密切的“文学双城”传统。由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办的第三届上海一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世界文学和青年写作”在复旦大学举行。
2017年,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与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金理共同发起了上海一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工作坊邀请杰出的青年作家、出版人和译者等,与上海南京双城为主的青年批评家共同交流前沿性文学艺术问题。
世界文学是一面镜子
今年工作坊的主题是“世界文学和青年写作”。召集人金理说,他对于这个主题的思考,缘自一场十年前“80后”文学研讨会。当时上海译文社的副社长赵武平谈到一个现象,说在策划国外"80后”作品集时发现国外的“80后”还在探索一些形而上的东西,表达终極关怀。
“他意思是他们写作蛮独立的,也推测可能是因为很多公共图书馆、基金会能够给他们一些资助。所以他们写作的时候不像国内青年人比较功利地要面向市场。”
这番话让金理深受触动,他直言世界文学是一面镜子。“有了这面镜子我们可以对很多方面,包括阅读、创作、出版、文学生态等多角度进行对照,可以照出我们自身的长与短。”
在工作坊现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葡语系副教授范晔说起拉美文学世界的“Boom”一代和“Paf”一代。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初,拉美文学的繁荣与辉煌造成了世界性的“冲击”,以至于有人用了“Boom”(爆炸)一词来形容当时盛况。那一时期拉美的代表作家包括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卡洛斯·富恩斯特、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等等。
而“Paf”一代呢?“我之前在诗歌节碰到一个智利年轻诗人,85年的,比我还小。他送我一本诗集,诗集名就叫Paf,用了拟声词。”范晔说,“我觉得他们这一代诗人有一个特点,我称之为无焦虑写作,或者叫无护照写作。”
“我们知道拉美作家一直以来,特别是马尔克斯这些人在写作中有非常明显的身份焦虑。‘我们的美洲、‘我是拉美人这些东西很明显地在他们的作品中沉浮、不断闪现。但是现在的年轻拉美作家好像没有身份焦虑,也不太纠结自己到底是什么人的后代。当年对文学爆炸一代那么重要的问题是古巴革命,今天代替古巴革命位置的是数码革命。所以Paf一代比起Boom一代确实有很大变化。”
世界文学维度下的青年写作
工作坊另一位召集人何平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离开世界文学的维度无法展开。“以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为例,几乎所有19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入写作的作家都有重回世界文学写作的过程,比如余华、苏童、格非、马原这些先锋作家,经历的则是面对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震惊感。后来他们回忆各自的个人写作史,对从写作的蒙昧时代、至暗时刻,到忽然被现代主义文学照亮记忆深刻。”
如今,青年作家成为当代文学现场中的重要力量。今年4月,《中华文学选刊》曾策划了当代青年作家问卷调查,向目前活跃于文学期刊、网络社区及类型文学领域的35岁以下青年作家发去问卷,共收到117位青年作家的回复。
何平说:“我们要思考的是,在今天这个时代,青年写作者和世界文学究竟是怎样新的关系方式?青年作家和更早的前辈作家们有何不同?他们同时代的国外青年写作是什么样子?”
群岛图书出版人彭伦长期从事外国文学的引进出版,从去年开始也代理中国作家的翻译版权,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
“出版其实是信息情报的收集和过滤。国际出版界有立体信息网,比如美国有新青年作家在《纽约客》发表了一篇很火的短篇小说,这个消息很快会在国际出版网传播开来。当好几家美国出版社去争夺这位新人的版权时,世界各国出版社都会前去打听的。”
彭伦说,但中国现在比较欠缺的是信息发布的通道,其实哪怕是《中华文学选刊》的当代青年作家问卷调查,对外国出版商也是非常好玩的信息。
“现在国家对版权输出很重视,这方面也设立了不少资助项目。但是你很难说效果有多好。我们经常看到消息说,某个作家的书在这个那个国家翻译出版,但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我们都不知道。”彭伦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我们输出作品的版权,应该接触世界各国有声誉的、认真做文学的出版社,通过他们让作品进入市场。因为他们选择一个作家和一部作品,考虑的首先是文本质量和作品的商业潜力,而不是说,你能给我很多政府资助,我就把作品本身质量和翻译质量扔在一边。”
“青年写作”与“成熟写作”
对于“青年写作”这样的提法,《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黄德海思考是否可以换为“成熟写作”?也就是不刻意区分年龄,按照作品的成熟度进行评价。
“我们一直鼓励青年的姿态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带来矫揉造作的作风,因为它不一样。而一个成熟的写作会有意地收敛作风。这些年我们对青年的刻意推举太多了,也就容易造成写作没有障碍、缓慢进步、思考不深入,而是按照杂志路数发表,最后变成我们参与了我们自己都非常讨厌的同质化。我们一直说要反对同质化,但我们一直在用鼓励求新求变的方式来鼓励这种事。”
“我们现在看年轻写作者有点样子的,很快就会消失。因此不要给他们不应该得到的虚荣,这样会把人带入火坑。因为不停地会有新的年轻人出现,一旦社会关注点降低了,他会觉得时代对不起他,他会焦躁、忧郁、生活不踏实,这是不好的。”黄德海希望,当人们在推青年写作的时候,那是成熟的写作。
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作家黄昱宁看来,国外作家的成熟周期“不像国内那么急”。“比如新概念一结束就必须出好多书。他们不是这样,整体的多样性还是比较好的。”
她提及目前引起欧美主流文坛极大关注的爱尔兰“90后”作家萨莉·鲁尼(SallyRooney)。萨莉·鲁尼的第二部作品《普通人》就获得科斯塔年度最佳小说奖,从而成为这一奖项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
“最近我们在推鲁尼的《聊天记录》。”黄昱宁说,世界文坛对于纯文学如何与互联网世界对话也有焦虑。“鲁尼的语言看上去非常时髦。她有一个主要的主题一一戳破消费社会的真相,有一种文本对阶层冲突的敏感。很令人惊讶,实际上反倒‘80后、‘70后不那么关心、不那么强调的问题,她又抓起来了,而这是一个19世纪的问题。”
“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主流文坛对这个人那样有兴趣,会那么关注她后面的走向。我们既看到了她与这个时代接通的东西,又看到了与小说发展史一直有密切关系的这一条脉络。”
如何发掘写作新的可能性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教授黄荭也认为作家不要分“老中青”,分“好作家”和“不好的作家”就够了。
“法国是文学生产大国,文学传统一直有很好的承继和发展。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国别文学的疆界被打破,
‘法国文学的概念越来越被外延更宽广的‘法语文学所替代。”黄荭以贝尔纳韦尔贝尔(Bernard Werber)为例,谈到法语文学的一些新气象。
从中学会考结束,17岁的韦尔贝尔就开始写“蚂蚁”,历时12年终于在1991年发表了《蚂蚁》,之后继续推出以蚂蚁为题材的“地球内部居民”系列小说《蚂蚁时代》和《蚂蚁革命》。蚂蚁三部曲跟通常动不动就是火箭、机器人和外星人乱飞的科幻小说不太一樣:通过描绘地球上另一物种的生活来反思人类,探讨人类在钢筋水泥森林里生存的其他可能性。
“蚂蚁系列”之后,韦尔贝尔又写了“天使系列”、“诸神系列”、“科学探险系列”、“第三人类系列”。在写系列长篇的间隙,他也写了像《大树》这样的充满奇思怪想和预言意味的短篇故事集。
“某种程度上《大树》(法语书名叫《可能之树》)有点像21世纪的新世说新语,里面有很多科幻情节的架构,又不乏哲学和伦理道德上转念一想的荒诞和警醒,这也是为什么他用‘哲幻小说来定义自己的创作类型。”
“韦尔贝尔说《大树》中小故事的灵感常常来源于一次散步,一次和朋友聊天,一个梦境……为了保持快速虚构故事的能力,让他从白天大部头小说的写作中解脱出来,放飞一下自我,探索存在和写作的可能性。”黄荭说,“我觉得这给我们年轻作家一个启示,当你埋头写长篇时,你其实可以在间隙写一些能解放自我的小东西,给想象力松绑。”
“此外蚂蚁是韦尔贝尔从小的爱好,后来他也去过塞内加尔跟踪非洲黑蚁做过科学研究,为了创作甚至在家也养了一窝蚂蚁,正因为观察研究得细致,创作的时候有如泉涌。我想中国年轻作家从自身和现实出发,深入挖掘,然后找到一个超越日常和现实的‘跳板,可能会发掘某一类写作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