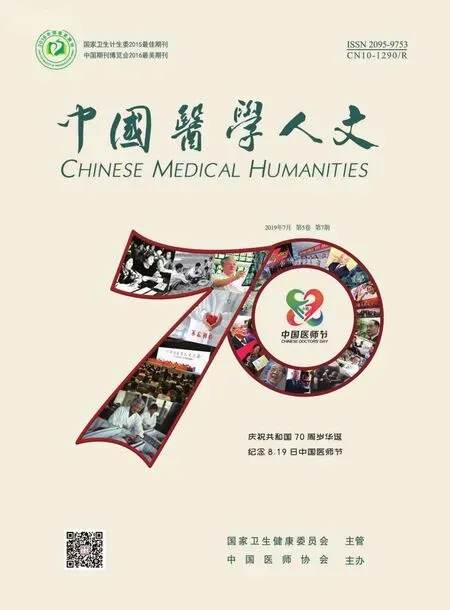记忆才让草
文/张启科
五年前的一个上午,门诊。
我依旧穿着那身神圣雪白的大褂,一个接一个接诊不同的患者,面对一张张被仪器拆分成数据的化验单,我用一种职业练就的平静,分别化解他们眼中滚烫焦灼的目光。

在一个贫血病人起身离开后,门口出现了一对互相搀扶的中年男女。他们全然标准的藏民装束,男的皮肤黝黑,发如蓬草,女的力不能支,像一滩泥贴在对方的身上。两个人只有牙齿看起来是那么耀眼。作为血液科医生,我清楚地知道,来我们科就诊或转诊的病人,不是病入膏肓,就是濒临绝望。当我开始问询她的病史时,女的一脸茫然,我明白了,她不懂汉语。从男的蹩脚的几句汉语中,我明白了,她叫才让草,他们是一对夫妇。得病后,她在当地尝试了好多种治疗方法,包括藏医传统的中草药以及虔诚的求助于神灵,但都没有好转的迹象。凭着多年的临床经验以及化验结果分析,我知道她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我以最快的速度为他们联系了床位,并且用他们能看懂的工整的汉字标示清楚,让他们能尽快地找到主管医生。他一边扶着爱人,一边向我致谢。已是阳春三月,天气已渐转暖,两个人还穿着藏民传统的棉衣,走起路显得步履更加蹒跚和艰难。由于藏民特有的民族习惯,他们很少洗澡,手和脸几乎看不到正常肤色,病房里的人见到后都拒绝她的入住。我们苦口婆心的向每一个床位的患者说明,但都不奏效。她听不懂汉语,但是从双方互相交流时的面部表情,似乎明白了其他患者的意思,夫妇俩执意要求在走廊外面加床。
根据化验等检查很快确诊她为白血病。庆幸的是她患的是预后最好的那种类型: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当我用最易懂的汉语告诉她爱人的病情时,他似乎明白了我说的话,双手合十,谦恭的用一连串藏汉交融的话说着什么,我听的最清楚的两个字就是:谢谢!谢谢!接着,他从棉衣的内里口袋,掏出了用手绢包起来的一沓钱。示意我他要赶快去缴费。好像缴了钱,就有了希望。透过这个钱包,我仿佛看到了一个男子,在草原上辛苦劳作的佝偻身影。对于治疗白血病,这些钱只是杯水车薪,显然远远不够。我抑制住内心的一种莫名的酸楚,叮嘱他拿好钱,去办理住院手续。
不知是上天的眷顾,还是她先天身体素质好,整个治疗过程竟然没有感染发热,也没有出血症状,他对她更是悉心照顾。化疗结束后,要度过骨髓抑制期,支持这些治疗的费用也是昂贵的。我知道他住院交的费用也所剩无几了。果然,他提出坚决出院,带爱人回家休养。我很无奈,只是反复强调出院后应该注意的所有事项。
一晃三年过去了。依照我作为医生的推断,才让草早就被病魔吞噬了生命。由于经济的原因,她毕竟没有进行规范的治疗,而是作为一个病情危重的患者强行出院的。
也是一个普通的门诊。我依旧重复着我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工作。猛然间进来一个藏族男子,说是找我。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已重重的跪在了地上。额头磕在水泥地上砰砰直响。我顿时懵住了,面对一个藏族男人宗教般的神圣礼仪,我感到十分的愧怍。当医生多年来,我和我的同仁们头顶着这个职业所赋予的无上荣光,竭尽全力地秉持着职业理想和做人操守,用生命抒写着满腔的精诚。但同时我们又承受着好多人的误解和对这个职业的曲意解读。什么红包,什么黑幕,医生遭杀戮,门诊变灵堂……凡此种种的闹剧此起彼伏地上演。面对这个藏族男人以头触地的大礼,向我所代表的职业致敬,我的眼睛湿润了……不错,他就是我数年前接诊的患者,才让草的爱人。我没有问才让草是否健在,也无需再问。从他满脸灿烂的笑容里,我已知道了答案。还是那身装束,还是那样的黝黑,还是那样的发如蓬草。他说她现在非常健康,当地化验一切指标正常。由于经济原因,我给她开了一些口服的药物,嘱咐她继续复诊。临走时仍旧是藏民特有的双手合十,弓腰道谢。
才让草是我接诊的病人中最普通的一个。他们夫妇生活在生存条件极度恶劣的雪域高原。他们保有原生态的质朴,甚至没有走出过草原,更不了解现代文明下物欲横流的社会形态,却把自己纯洁的感恩之心化作了朝圣般的礼仪,让我感受到了作为一个医者的高贵。从他们身上,我收获的不仅仅是感动,更多的是一种责任。我和我所有省医的同仁将一如既往的恪守职业道德,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努力实现大医精诚的职业理想,将所有才让草们的希望义无反顾地扛在自己的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