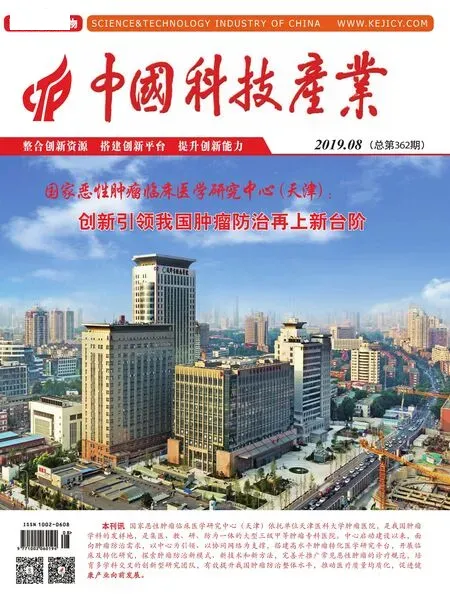“心脏病学之父”陈灏珠:突破创新, 让生命的血脉畅通
◎ 本刊记者 冯翔慧

上海闹市中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大清早已人流如梭。95 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心血管医学专家陈灏珠,银发白眉,温文儒雅,在内科领域特别是心血管病的临床方面造诣很深,被誉为我国心血管病介入性诊治法奠基人之一和“心脏病学之父”。在心血管病方面,他率先作冠状动脉造影和腔内超声检查;率先用电起搏和电复律治疗快速心律失常达国际先进;率先用活血化瘀法治疗冠心病并阐明其原理;在国内外首先应用超大剂量异丙肾上腺素救治奎尼丁引起的致命性快速室性心律失常成功。
从医70 年来,陈灏珠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 项、部省级科技进步和教学成果等一等奖8 项;发表论文358 篇,编著《心脏导管术的临床应用》《丹参治疗冠心病等的研究》等11 部。缜密的临床思维、精辟的讲课、精彩的学术报告以及丰富的科研成果,为所有与他一起工作的同志所熟悉、敬佩。
在流亡中度过中学和大学
1924 年,陈灏珠在香港出生,父亲常年在外奔波。“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母亲给了我很大影响。” 他记得,小时候背诗文,不识字的母亲会在一旁听着。即使他背错了母亲也不知道,但她的认真执着深深影响了陈灏珠。
15 岁那年,母亲患高血压突然去世,陈灏珠第一次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他说:“这也是我走上学医之路的原因之一,希望尽可能延长人的生命。”
1941 年,日军的战火蔓延至香港。陈灏珠回忆,那时在家每天都能听到炮火声。“日子过得很紧,每人每月只能按配额买9 斤8 两米,不得不用树叶、蕃薯藤等充饥。我真的体会到什么是国破家亡。”
在随后的两年,父亲带着几个孩子,从香港逃往家乡——广东新会,不久又逃往韶关。他们晚上乘船,白天步行,翻越山路,一路要躲过日军多道封锁线。
1943 年,陈灏珠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从韶关琼崖中学粤北分校毕业,随后进了中正医学院,从此踏上从医之路。
那时,学校因战火被迫搬迁至江西永新县。在日军封锁下,他们买不到教材,但艰苦条件并没有影响教学质量。学生每晚在桐油灯下,把老师用英语讲授的笔记当作教材温习。
随着日军侵华的深入,学校再度搬迁,最后到了福建长汀县。在崇山峻岭的险途中,大家徒步跋涉了几个月,有的同学从此再无音讯。抗战胜利后,当学校迁回南昌时,原本同班的100 多位同学只剩下30 人。
70 多年后,陈灏珠回忆起这段流亡的日子,感叹的是在苦难条件中学到的东西:一是练成快速记笔记的本领,二是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外语基础,三是练就了强健的体魄,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不向困难低头的精神。
医学领域的创新关乎生命,要完全为了病人着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的这一年,陈灏珠成为国立上海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现为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一名内科医生。
成为内科医生的陈灏珠把所有精力都扑在了工作上,开始系统科学地投入到了心血管领域的研究中, 1968年和心外科石美鑫教授合作完成中国第一例埋藏式永久性心脏起搏器安置手术;1973 年,陈灏珠完成了中国第一例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手术;1976年,在国内外首次使用超大剂量异丙肾上腺素治疗奎尼丁晕厥。
陈灏珠院士的妻子韩慧华在采访中说:“他做医生,尽管是职业,但是他是作为一辈子奋斗、一定要干一辈子的事业来对待的。所以他每天都要学习,他说医生不学,不进则退,许多医学问题还不能解决,一定要靠大家来努力。”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冠心病少见,中国医学界对冠心病认识不深,对当今所用表达心脏肌肉严重缺血而坏死的“心肌梗死” 这一病名,仍沿用“冠状动脉血栓形成” 来称谓,但冠状动脉血栓形成后并不都引起心肌梗死,因此用以代表心肌梗死并不恰当。1954 年,年仅30 岁的他在陶寿淇教授的指导下,发表了论述“心肌梗死” 的文章。“心肌梗死” 成为我国心脏病学界公认的诊断称谓。陈灏珠说,当时,人们很忌讳把“死” 放在疾病名称中,这一提法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医学领域的创新关乎生命,要完全为了病人着想。” 陈灏珠抱着这样的信念,从过去只用听诊器、心电图、X 线诊断的方式,转而选择一种新的介入诊断法——将一根管子顺着病人的血管插入心脏,到病变现场一探究竟。这大大提高了先天性心脏病和风湿性心脏病患者的诊断质量。
此后,陈灏珠又成功开创了一个又一个“第一”:第一例埋藏式永久性心脏起搏器安置手术,第一例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手术,第一例血管腔内超声检查……如今这些已成为心血管疾病治疗领域应用最广泛的技术。
作为一种常用的心律失常治疗药物,奎尼丁一直在临床被广泛使用。但奎尼丁本身会引起恶性快速室性心律失常,引起晕厥抽搐甚至死亡,“奎尼丁晕厥” 也成为医生的梦魇。
1976 年5 月,陈灏珠收治了一位28 岁的年轻母亲。该名患者接受了心脏二尖瓣瓣膜分离手术后,突发心房颤动。在服用奎尼丁后,病人逐步恢复了正常心跳。不料,1 小时后,患者产生恶心、呕吐等症状,进而神志丧失,陈灏珠当即判断,患者出现了“奎尼丁晕厥” 反应。
在随后的10 小时中,病人先后发作29 次,晕厥的间隔也越来越短。面对这样棘手的案例,陈灏珠翻阅了病案记录,最后认定大剂量注射异丙肾上腺素可发挥作用。
果然,其用量达到正常剂量的15 倍时,患者病情逐渐趋稳。此次抢救创造了逆转“奎尼丁晕厥” 的世界奇迹。
医学未解决的问题需要年轻人努力
“虽然想不到,国家今天能这么富强,但这些年来,凡是国家和人民需要,我都要上去。” 陈灏珠感慨道。
陈灏珠珍藏着一枚小银盾,上面写着“病员的哥哥” 五个字,这与他69 年前的一段经历有关。
1950 年,驻上海和江苏一带的解放军中,不少人患上血吸虫病。陈灏珠响应华东军政委员会和上海市政府号召,到浙江嘉兴为官兵进行防治。
在驻军的一年里,除了为病员观察病情,他还主动为呕吐的患者清理。痊愈的战士归队时,把这枚小银盾送给了他。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陈灏珠加入了抗美援朝医疗队,到齐齐哈尔治疗伤员。那里的冬天最冷达零下40℃。他们外出时戴着大口罩,从鼻子里呼出的气体会凝在睫毛上,形成一道冰霜。“当时条件有限,无论是心胸外科手术、骨科手术,还是结核病治疗,我都要干。” 陈灏珠说。
在陈灏珠的从医生涯中,最让他产生国家荣誉感的是治疗外国专家的一次经历。1975 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巴茨博士在参观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时突发心肌梗死,生命危在旦夕。陈灏珠受命担任抢救组组长。他婉言谢绝了美方派医师来华主持抢救的要求,与同事们一起经过七昼夜的治疗和监护,终于使病人脱离了危险。1976 年,美国权威医学杂志《内科文献》详细报道了此事。
“我从事医、教、研工作已经70年。我经历过解放前外敌欺辱、民不聊生的时代,也经历了新中国的艰苦奋斗、沧桑巨变,深刻体会到只有把自身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的精神才有归属,奋斗才有方向,梦想才能实现!” 陈灏珠激动地说。
如今,他虽然没有工作在临床第一线,但在2007 年捐赠100 万元,创立“复旦大学陈灏珠院士医学发展基金”,用于支持医学人才培养和医疗精准扶贫,近年来受到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广泛关注和支持。
据介绍,陈老直接培养的学生共有78 位,还有数不胜数的进修生,其中许多人已成为国内顶尖的心脏病学专家及各地医疗骨干。
“未来的世界是年轻人的,医学未解决的问题需要年轻人努力。” 陈灏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