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中国的伦理治理*
雷瑞鹏,翟晓梅,朱 伟,邱仁宗
(1 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2 华中科技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4;3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命伦理学中心,北京 100730;4 复旦大学应用伦理学中心,上海 200433;5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2018年11月,在中国香港举行的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前夕,当我们走下飞机时,并不知道自己正步入恰在上演一场人间戏剧的中心。就在几个小时前,贺建奎在优酷视频网站上发表声明,声称他已经帮助一对夫妻制造了基因编辑婴儿。等我们一打开手机,手机就开始了剧烈振动。
我们中的两个人(邱仁宗和翟晓梅)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4点,不停忙着接电话,帮助中国的学术机构和政府机构回应这一事件,同时还修改了当天晚些时候在峰会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自那以后的几个月里,中国的科学家和监管机构经历了一段自我反省的时期。我们、我们的同事们以及我们的政府机构,如国家科技部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都在反思这起事件对中国科研文化和监管产生的影响。我们还考虑了需要采取什么样的长期战略来加强国家对科学研究的伦理学治理。
在我们看来,中国正处于十字路口。政府必须做出实质性的改变,以保护其他人免受不计后果的人体试验的潜在影响。这些措施包括对国内数百家提供体外受精的诊所进行更密切的监控以及将生命伦理学纳入各级教育之中。
1 震惊和困惑
2018年11月27-28日,当峰会的与会者们聚集在香港大学礼堂时,他们感到十分困惑。几乎没有人听说过当时还是深圳南方科技大学生物物理学家的贺建奎。从中国记者们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来判断,他们也措手不及,且很难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或有什么利害关系。
与美国和欧洲不同,中国很少有关于基因编辑的公开辩论。大多数人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修饰生殖细胞(精子或卵子)与其他(体细胞)细胞之间的区别,更不必说由改变未来世代基因所引起的更深层次的问题——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
贺建奎的工作违反了国际规范。而且违反了中国2003年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条例,该条例禁止将转基因人类胚胎移植入人的子宫[1]。此外,由于基因编辑可能出错,贺建奎的行动可能会危及婴儿的健康,以及他们潜在后代的健康。这与早在公元前600年就确立的中国传统医学观背道而驰。当中国哲学家孔子提出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学说时,许多医生遵循了他的学说,认为医学是“仁”的艺术(医乃仁术)。
2 为何会发生这种事?
峰会前两周,贺建奎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生命伦理学双年度年会,他参加了我们其中一位(雷瑞鹏)主持的一场关于如何避免正在作临床试验的基因编辑过早应用的专题会议。在那次会议上,他对自己的研究只字未提,而是等到香港峰会前夕才宣布基因组经过编辑的双胞胎女孩诞生,说到了问题的核心(见“在调查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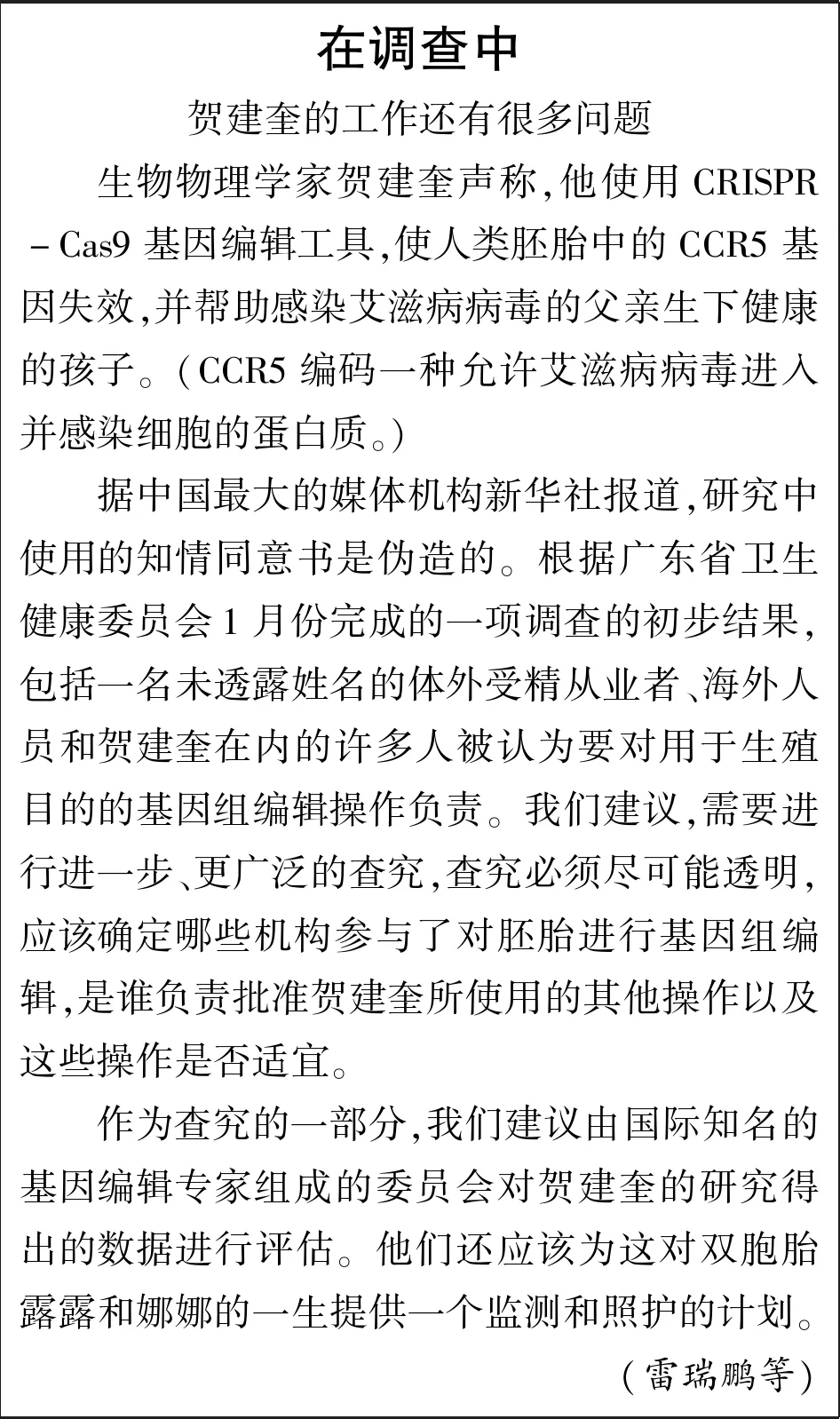
在调查中贺建奎的工作还有很多问题生物物理学家贺建奎声称,他使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工具,使人类胚胎中的CCR5基因失效,并帮助感染艾滋病病毒的父亲生下健康的孩子。(CCR5编码一种允许艾滋病病毒进入并感染细胞的蛋白质。)据中国最大的媒体机构新华社报道,研究中使用的知情同意书是伪造的。根据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1月份完成的一项调查的初步结果,包括一名未透露姓名的体外受精从业者、海外人员和贺建奎在内的许多人被认为要对用于生殖目的的基因组编辑操作负责。我们建议,需要进行进一步、更广泛的查究,查究必须尽可能透明,应该确定哪些机构参与了对胚胎进行基因组编辑,是谁负责批准贺建奎所使用的其他操作以及这些操作是否适宜。作为查究的一部分,我们建议由国际知名的基因编辑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对贺建奎的研究得出的数据进行评估。他们还应该为这对双胞胎露露和娜娜的一生提供一个监测和照护的计划。(雷瑞鹏等)
过去十年中,中国政府在学术界和工业界越来越多地投资于转化医学。这种对可销售产品的推动,营造了一种深受“急功近利”(渴望快速成功和短期获利)困扰的科学文化氛围。然而,将设备或方法应用于临床并非总有坚实的基础研究作为支撑[2]。
此外,无论是在亚洲还是在世界,那些能够宣称自己是第一个发现什么的研究人员,在同行评审、聘用决策和资助方面,都会收获比例不相称的奖励。以在石家庄的河北科技大学分子生物学家韩春雨为例,他在2016年与人合作在《自然生物技术》(NatureBiotechnology)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描述了一种名为NgAgo的酶如何能够像广泛使用的CRISPR-Cas9基因编辑工具一样编辑基因组[3-4]。这篇论文虽在2017年被撤回,但在首次发表后不久,韩春雨即被任命为河北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会长,他所在的大学也计划投资2.24亿元人民币(3300万美元)建设一个基因编辑研究中心,韩春雨的团队是该中心的核心[5]。
在我们看来,中国的研究人员越来越多地受到名利驱使,而不是出于对科学发现的真正渴望或是为了帮助人民和社会的愿望。
在说明贺建奎为何能够成功推进他的研究时,同样重要的是研究伦理治理方面的薄弱——中国长期以来努力发展科学和技术的阿喀琉斯之踵(意为致命弱点——译者注)。
在过去十年里,贺建奎并不是第一个从事不符合伦理研究的人。例如,在2012年政府禁止干细胞疗法应用于临床实践之前,数百家中国医院向中外患者提供未经证实的干细胞疗法[6-7]。在2012年的另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研究了6-8岁的儿童是否可以从转基因“黄金大米”中获得与从菠菜或胡萝卜素胶囊中同样多的胡萝卜素(维生素A的前体)。研究人员告知孩子们的父母,他们正在测试孩子们对一种营养物质的摄取,但是没有提到转基因稻米[8]。2017年,一项计划在中国进行的试验是打算将一个从颈部以下瘫痪的患者的头颅移植到一个不久前去世的捐赠者的身体上,这项试验几乎要进行,后被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取消[9]。
在干细胞疗法方面,直到2015年7月,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他们的联合指南之前,中国一直缺乏相关规定[10]。在此之前,急于利用这种疗法赚钱的人很快就感受到了利润。在贺建奎的案例中,对全面监管的投资不足可能更应该受到谴责。在一个幅员辽阔、发展迅速的国家,用于监管的资源仍然是个问题。我们认为,这种投资之有限,也因为人们根深蒂固地认为科学永远是正确的或者科学知识应该优先于其他一切。
在中国,对包括例如体外受精诊所在内的医疗卫生专业人员伦理培训的重要性,缺乏认识。许多伦理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尤其是那些与杭州、广州和深圳等规模较大城市的医院有关的伦理委员会一些成员——更不用说那些规模较小的城市了——可能无法严格评估新兴技术,因为他们既缺乏伦理培训,也缺乏科学知识。此外,包括医学伦理学在内的人文学科教育,对于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以及科研人员来说都是不够的。
3 现在怎么办?
我们认为,以下六个步骤可能有助于降低在中国发生进一步不符合伦理或非法使用新兴技术的可能性。
监管。政府应与科学家和生命伦理学家合作,制定更明确的规则和条例,以管理可能容易被滥用的有前景的技术的使用。这些技术包括基因编辑、干细胞、线粒体移植、神经技术、合成生物学、纳米技术和异种移植(在不同物种成员之间移植器官或组织)。相应的行为规范应该由专业协会制定和实施,如中华医学会及其附属的医学遗传学学会和中国遗传学学会。
考虑到科学家在市场压力下潜在的利益冲突,他们的自我监管可能是不够的。因此,自上而下的监管至关重要。在我们看来,对违规者的惩罚应该是严厉的——比如失去资助、许可证或被解雇。此外,为了对研究进行有效治理,应该由国务院(中国的中央政府)负责。目前的做法(由多个政府部门负责监督)是碎片化的,且因工作人员缺乏能力或遇到阻力而受到阻碍。2018年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了《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11]。
注册。建立专门用于涉及此类技术临床试验的国家登记注册机构,这将拥有更大的透明度。在试验开始之前,科学家可在那里登记伦理审查和批准的记录,并列出所有参与试验的科学家和机构的名称。同样,政府可建立准入制度,只有经过合适培训的人才有资格担任伦理审查委员会委员。
监测。例如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这样的机构必须对中国所有基因编辑中心和体外受精诊所进行监测,以确定临床试验的进行情况。它们应当评估伦理批准和其他程序(特别是与知情同意有关的程序)是否充分;卵子、胚胎的使用是否符合人类辅助生殖的规定;以及是否有其他经过CRISPR编辑的胚胎被移植入人的子宫。生命伦理学(研究伦理学和临床伦理学)的培训也应该成为基因编辑中心和体外受精诊所所有医疗卫生专业人员的必修课程,不管这些人目前是否正在进行临床试验。原则上,由政府或非营利基金会支持的研讨会和课程,可以向医生和研究人员收取一定的费用。
提供信息。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医学科学院等机构可以发布每一种新兴技术的相关规则和规定。它还可以就合适的知情同意程序和该领域的最新科学发展提供咨询意见。这将为有兴趣参与试验的人们提供资源,并为研究人员在如果察觉到可能违反伦理指南的情况时提供一个联络点。
教育。在政府支持下,大学和研究机构应加强生命伦理学(包括临床伦理学、研究伦理学和公共卫生伦理学)以及科学/医学专业精神的教育和培训。各级科学、医学和人文学科的学生以及从技术人员到教授等科研人员,都应该成为这种教育和培训的目标。
相关的部级机构(特别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科技部和中国科学院)也应该提高公众对与新兴技术相关的科学和伦理含义的认识,并促进针对每一种技术的公开对话。为帮助记者掌握此类技术的细微差别和复杂性而进行的媒体培训,也应该是这一努力的一部分。
杜绝歧视。最后,中国应该加大力度,消除对残疾人的偏见和少数中国学者坚持的优生学思想[12]。有个别学者声称,残疾人是“劣生”(意思是低人一等或社会的负担)。他们认为,残疾人不应该被允许有孩子,甚至在必要时应该强制绝育。199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禁止在就业以及其他方面歧视残疾人。显然,我们必须做得更多。
生命伦理学在中国建立仅30年左右。值得记住的是,不符合伦理的研究实践在西方伦理治理的早期很普遍。以臭名昭著的塔斯吉基研究为例,在该项研究中,美国公共卫生服务署追踪了1932~1972年间399名患有梅毒的黑人男子,但没有对他们进行治疗。正如这项研究的披露促成了1978年的贝尔蒙报告(该报告保护参与研究或临床试验的人类受试者)一样[12],“基因编辑婴儿”丑闻也必然会促成中国对科学和伦理治理进行全面检查[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