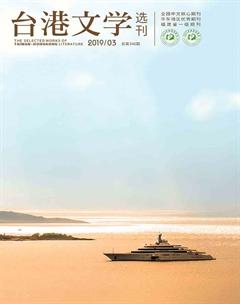老派少女购物路线
洪爱珠

妈妈病笃。倒数十日,她愈是寡食少语长睡偶醒,往生命静止方向深水潜游。彼时我每日问她想吃什么,然后设法张罗来,博她一点病中日光。妈妈谈食物的时候,较能谈笑,于是以此唤她回神,多望一眼我们这些今世家人。
人在尽头,返身回望,妈妈一生吃食富裕,而倒数时刻,念想的反而是素朴的儿时食物。咸冬瓜蒸肉饼有时,那是已故外婆的家常菜;白粥酱菜有时,有时只是一碟肉松甚至肉燥风味泡面。而这日她说,想吃炸春卷。
炸春卷自然不能是买来的。我妈病着但绝不糊涂,没有什么比外带回家,被蒸气弄得软塌油糊的春卷皮更坏。最好的办法,便是买得润饼皮,裹春蔬及花生糖粉,油炸后立刻呈到她面前。而时序初春,清明未至,润饼皮在本地市场里不易得,此时唯能往城里去,倚靠我家三代女子的心灵故乡:大稻埕、迪化街、永乐市场。
陪病两年,在频繁的门诊化疗手术急诊中,日常脱轨,活成夜长昼短,苍白无风恒温状态。然而一抵迪化街,日光慷慨,晒褪病房阴凉。感官放大,整个街区的生活气味聚拢上来。青草药材的、热食摊贩的、香菇干贝虾米鱿鱼的鲜腥味奔放,不远处霞海城隍庙的香火,也嗅得一点。呼吸满腔复杂气味,就觉得人扎实活着。
其中每一股气味,我都能单独辨识,都是神奇勾引。回到与外婆的大手小手的儿童时期,和妈妈的母女放肆逛街时期,这是我家祖孙三代老派台湾妹,最喜爱的台北聚落。落俗一点便称这类心情,叫出嫁女儿回娘家,知根知底熟门熟路。青春是真空永恒状态,是女子心中的自由小鸟。因此返抵娘家,回到城北河边的大稻埕,我们就都成少女,步履轻盈—脸发光。
而娘家并非虚构,三人之中,我外婆阿兰,是真正以大稻埕为娘家。
于闽人聚落里富庶的太平町延平北路长大,在大桥小学迎接台湾光复的女孩阿兰,小学毕业后,便在正值巅峰的永乐座戏院,担任售票员直到结婚。日后外婆转述永乐座时期,一代青衣祭酒顾正秋巡演的盛况,眼底仍有流转的星闪。
阿兰后来远嫁淡水河对岸,观音山脚下的郊外之郊。形容自己进门时,足踏漆亮高跟鞋,一脚踩进屋内,不料仍是泥地,台北小姐的农村拼搏史自此开始。而老派淑女未曾放下往日讲究,踏出房门,必全妆示人并抹朱红唇膏,以马甲束裤将自己扎紧,才穿进订制洋装,系上细黑皮带。
旧年对女子要求苛刻,美而无用不成,她还必须能干。因此外婆与妈妈皆极能做菜,乡里驰名。外公做外销生意,员工近百家人数十,盛时每天摆开八大张圆桌吃饭。更有连绵宴席,来宾自欧陆、中东至东南亚。宴以备料三日的华丽闽菜,与自家酿酒。如今听起来排场太过夸张,若闻江湖传说。
外婆购物,那是头家娘式气派。日常采购,多以近家的芦洲大庙市场为基地,鱼肉水果挑的是月历照片似的、饱硕漂亮的上货,量多便交代一声,让商家送到家里。但凡节庆或宴客,外婆就必亲身回到大稻埕与永乐市场。
大稻埕百年以来一直是南北货及高档食材集散地,过去许多办桌师傅亦聚此处,很有人才与食材一筐打尽的概念。对此妈妈亦很迷信,宴客所需的华丽食材,鲍参翅肚蜇头竹笙,最厚的椴木香菇和干贝,甜汤用的雪蛤红枣及奶白油润的宜兰沙地花生,都要专趟来买。母女二人自有信任的老铺,和一套精明的选物标准。
身为孙辈里第一个孩子,外婆到哪都带上我,宠以海量的爱与食物,而我回报她白白胖胖及念念不忘。妈妈与我,则一面叠印外婆脚步,加以近年发现的店铺,组织成老派购物路线。水边时光慢,老城区迪化街的旧建筑,那些杨德昌电影《青梅竹马》里,夜行车灯抚亮的街屋立面华饰,近年修复后原质再现,吸引潮流店铺和观光人潮。但只要老铺犹在,民生气息仍厚,就不至于弄得人面目全非。我以老铺为据点,三代记忆为经纬,有凭有据地走跳此区。
到永乐市场及迪化街,我们惯从延平北路这侧进出,此隧道般的入口,左右各据一家糖铺,售各色老派零食。外婆嗜甜,会买甘纳豆,和我喜欢的蛋酥花生,一种花生裹了鸡蛋面糊再油炸的零嘴。如与妈妈去,则买蚕豆瓜子等咸食。
穿出隧道右转,喝民乐街的凉茶。我们购物,未必记得商号名字,全凭位置或人脸辨识。譬如民乐街的两家百年凉茶铺“滋生”与“姚德和”,过往门面装修得一模一样,通常认其中有位老太太掌店的那家。理由是她白发苍苍,肤质却婴孩般绵白细致,怎么叫人不迷信该号凉茶有排毒神效。近几年老太太退休,顿失指向,改成两家交替着喝。
迪化街中药老铺恁多,并极富商誉。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生,中药少用,但若要得上好香料香包、胡椒肉桂,则往妈妈指名的“生记药行”。在“生记”帖药,过程即是疗愈经验。相较有些铺子,装修太堂皇招呼太激动,“生记”的人与布置,都简净雍穆。仅问一枚羊肉炉卤包,师傅仍逐一打开药柜木抽,取材料以砝码现称。不似满街骑楼下的成货,光照潮湿难免质变。药材在纸面上配妥,倒进棉布袋里扎好,眨眼间,纸张便封成包裹。
在迪化街买南北货在于逛,且眼色要好。因为各有所长,一家买完所有食材几乎是不可能,倒是可以先排除一些在门口,大量堆放蜜饯坚果和乌鱼子的店家。其果干颜色越艳的,越不可信。此区老字号,多少有些骄傲自矜。贵价的上货,不会曝展在外,必须经过询问,店家才从雪柜取出那些燕窝鱼翅,未经漂白的天然竹笙,兼解释食材来历。顾客识货而店家识人,外婆妈妈都长得富态贵气,有问有答。我这种菜鸟要是单独去,被忽略也是时常有的。
至于糕饼。如面龟、糕润、咸光饼和椪饼,可往延平北路上的“龙月堂糕饼铺”或“十字轩”。龙月堂创店与我外婆生辰同年,我收藏这种只有自己知道的联系,每回买饼,就默数店家岁月,为之由衷祝福。
龙月堂的绿豆糕和盐梅糕这类小姐点心,制得极细,以印着红字的油纸包装,里头每一枚绿豆糕,仅指甲片大小,化口沙碎精致非常。椪饼是中空饼,饼底有薄糖膏,是杏仁茶或面茶这类热甜汤的搭档,买了就要小心携带,因为破缺的椪饼,看来格外使人伤心。“十字轩”旁的“加福起士蛋糕”,卖得最好自然是招牌的起酥皮蛋糕,但其实椪饼也烘得特薄,买回家把饼拆碎,冲一碗妈妈熬的花生汤,深冬里取暖。
这些店家,亦常态性供应咸光饼和收涎饼。这类中间有个圆洞,可以穿红线绑在婴儿脖颈上的饼,在台北市已少见。但话说回来,现世要生个孩子来收涎,才是真难,纯买点饼来佐茶,容易一些。
大小女生凑在一块,认真购物,自然还包含吃喝。此区米面,有永乐市场周围数家米苔目,油葱虾米汤头清鲜,一碗粉白韭绿,外婆很喜欢。妈妈则多往安西街的老店“卖面炎仔”吃切仔米粉,切烧肉或猪肝。
此外,外婆与妈妈都对归绥街上的“意面王”本店,根深蒂固地喜爱。虽说意面王的干面、馄饨和切菜不错,但我疑心她二人的关键从不在面,在于饭后的那碟刨冰。
“意面王”在家族的口述历史中,开业时便是糖水专业,后来才卖起面,因此在面店点冰品其实内行,若能一字不差地点名如同通关密码的“红麦布牛”四字,更能展现出一股熟客的洗练潇洒。“红麦布牛”是综合浇料的缩写,指红豆、麦角、布丁、牛乳,麦角和布丁这两种浇料,是我个人判断糖水店的标准,采煮得甜糯润滑的麦角而非心韧且带药气的薏仁,采柔软味浓的鸡蛋布丁,而非大品牌的胶冻布丁,那是店家骨气与基础审美。
行经大稻埕许多年,在百年建筑群里穿梭、老铺里吃饭、买儿时食物,将自己藏匿于飞速时代里的皱褶缝隙,以為可以瞒过时间,但事情从来不是如此。
没忘记今日来,是为妈妈买润饼皮的。
进永乐市场一楼早市,抵“林良号”。圆脸爽朗的阿婆和不太说话的阿公兄妹,八十年来手工制润饼皮。“林良号”制饼,是古老节奏与时光之诗。手掌着湿面团,在烘台上抹出一张丝白薄饼,再足尖点地似的飞甩几下,使其均厚。待由湿至干,徒手将之数百数千的揭起。饼极薄而透光,重叠成分分秒秒时时刻刻,时间的具体证据。默默在侧观看一阵,此刻内心里若干尘埃,都暂时缓缓地降下。
问阿婆买一小落饼,她手里忙,仍亲切待我。以闽南语谈上几句,言及外婆和妈妈。聊到后来,阿婆温柔小小声地问:“汝阿嬷勾底勒无,人有好无(注:你外婆还在不,人都好吧)?”善意纯粹,只是因此揭开怀旧对话底下,我最黑深无底的空荒。“无底勒啊(注:不在了)。”答。外婆走了十年,以为会陪我许久的妈妈,刻下也正在分秒转身。恍惚间她们松手,长长的百年的大街上,四顾仅余我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