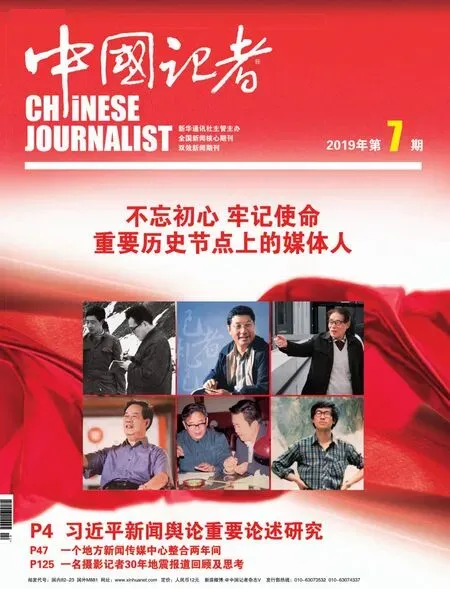北京形象国际传播的媒体表达
——以部分中外主流媒体历史文化遗产报道为例
□ 文/吴奇志
内容提要 历史文化遗产是媒体构建和传播北京形象的重要维度。本文通过案例分析部分中外主流媒体对北京文化遗产报道的观察视角、事实选择和观点表达策略,探讨相关报道的优势与不足,提出我国媒体借助文化遗产对外传播北京形象的对策建议。
城市文化是城市形象的根基,而历史文化遗产作为城市文化延续和传承的重要载体,以其唯一性和排他性彰显着城市的形象和魅力。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历史上各朝代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等可移动文物;以及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1]
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历史文化遗产是北京形象的直接体现,是媒体构建和传播北京形象的重要维度。本文以部分中外主流媒体对北京文化遗产的报道为例,分析其观察视角、事实选择和观点表达策略,探讨中外媒体的报道优势和不足,提出我国媒体借助文化遗产对外传播北京形象的思考。
一、自我审视:报道文化遗产的本土视角
有着3000多年建城史和860多年建都史的文化名城北京,除拥有长城、故宫、颐和园、天坛等世界文化遗产外,位于中心城区、以胡同四合院为主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内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是最能代表文化古都的城市符号,引起国内外媒体关注。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北京疏解整治行动和对文物保护和修缮的开展,老城区焕发新貌。我国主流媒体创新叙事表达,呈现保护修缮成果,再现老城区文化传统,体现出借助“金名片”建构和传播北京文化形象的自觉意识。以刊载于《中国日报》2016年6月11日的深度报道《古老街区的未来》(Building a Future for Ancient Neighborhoods)为例,文章围绕北京历史街区保护面临的挑战这一主题,选取了大量事实:历史遗迹(如建于元朝的组织妙应寺白塔,鲁迅博物馆,曹雪芹、梁思成等名人故居)的现象,胡同传统住宅的居住条件,以及来自政府官员、非政府组织和普通百姓的各方观点等,并以上述事实为依据,援引专家和居民的话表达了如下观点:传统建筑是北京的精髓,胡同提升了整个城市的价值,财产权是胡同保护问题的核心,支持与反对拆迁的观点并存,保护胡同的最好办法是改善居住者生活,整修胡同使各级政府面临挑战。这篇文章的报道策略体现在:一是关注普通百姓。文章开篇即描述了在阜成门内大街白塔寺地区生活50多年的何先生的日常生活和他对于胡同生活的体验,展现了老街坊的传统生活观念。二是以事实为线索,强调和突出历史遗迹保护工作的复杂性。三是注重呈现多元声音,兼顾政府、非政府和居民各方观点,体现了报道的客观性。
综观其他相关报道可见,我国主流媒体在利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北京形象中表现出以下特点:一是观察视角丰富,充分发挥本土媒体的优势,挖掘北京历史文化资源,取材于多种文化遗产,如古建筑、名人故居、胡同等,阐释北京传统文化和民俗文化。二是报道手法摆脱了以往历史文化选题报道中存在的以对景观本身的繁琐描述、解说和阐释为主的传统操作方式,致力于展示文化遗产与当下普通百姓生活的密切联系。三是注重从理念层面塑造北京形象,而不是局限于对文化遗迹物质空间的叙述。比如,通过呈现保护和修缮效果,彰显政府和居民的文物保护观念,借市民参与民俗节事活动的感受体现人们回归传统文化的愿望。四是引用权威信息来源,突出报道的客观性。

北京齐白石故居。(吴惟/摄)
相关报道也反映出我国媒体在对外传播北京形象中面临的两大课题:一是议题设置略显单调,同类选题的报道过于集中,同质化现象较为突出。一些胡同的报道也大多是对整治行动的回应,给人以宣传战役应景之作的印象,宣传味比较浓厚。而基于个人化思考,以个人眼光主动选择文化报道要素和方式的差异化报道还不多见。二是多数报道以事件为线索。比如,许多名人故居的报道由头大多为名人或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日,或者名人生日或忌日。其结果是,相关事件的深厚历史渊源容易使国外受众产生与城市的疏离感,难以带来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和体验。
二、他者解读:观察文化遗迹的域外眼光
有学者在研究考察了英国媒体中的北京形象后认为,英国《泰晤士报》在2000年至2015年刊登的774篇涉京报道中有23篇反映北京城市状况的“北京—城市主题”报道。而正面报道集中在文化和科教,主要反映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研究者因此建议“凭借北京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海外宣传推广北京城市形象”。[2]的确,外国受众一般会对古老城市文明尤其是历史遗迹、人文景观存在认知偏向。北京城市历史与风貌需要故宫、天安门、胡同这样一批地域性很强的建筑来传承。[3]北京胡同作为北京的人文符号,历来受到外媒关注。在有些媒体看来,北京胡同即是真正的北京。2009年9月13日刊登在《纽约时报》的文章《漫步北京胡同中,小商贩的叫卖声令人想起过去》表现出对北京老城区独特生活环境的浓厚兴趣。2011年10月9日《华盛顿邮报》一篇题为《北京发生的故事》的报道称:“在后海许多传统的胡同被保留了下来……居民在尽力拥抱现代的同时,也保留了过去,北京仍保留了旧中国的元素。”另外,北京老城保护与改造的冲突性议题也是引起境外媒体关注的主要原因。[4]
除胡同之外,外媒也将视角集中在北京其他物质文化遗产,因其最能代表北京形象,是海外受众熟悉的文化符号。《纽约时报》2017年5月7日刊登的深度报道《我的北京:神圣之城》(My Beijing:The Sacred City)就体现了类似的报道偏向。这篇报道讲述了北京两处历史遗迹——日坛和白云观在近30多年中发生的变化,并由此得出北京正致力于扶持传统和重现传统价值观的判断。文章用对比手法记录了30年间公园及市民文化生活的变迁,对遗迹本身的描写强化或者说契合了国际受众对古都文化符号的熟悉感;而对市民文化生活的同步呈现则有助于从居民的观念层面引导受众对北京的认知。
如关于日坛的变化,文章写道:1984年,“那座祭坛前不久刚刚重建过,但许多建筑物破旧失修,整个庭院似乎已被遗弃了”;2000年前后,“日坛公园在中心地带重建祭坛、一座小山、一个小湖以及一条主路”;关于游人文化生活的变化,文章观察到:20年前,“中国还不太发达,人们不愿意在锻炼身体上耗费时间,就是工作、回家、休息而已。公园是特殊情况下才去的。绕着公园走一公里可能只遇见几个人,通常是附近大使馆里的外交官”。10年前,“现在许多中国人都想锻炼,所以如今公园里到处都是慢跑者,他们穿着黑色氨纶运动服,冲过身穿油腻罩衣的餐饮工作者身边”,从市民的闲暇生活方式(健身)反映人们的生活态度(健康意识)。
因此,表面看,文章的观察视野仅限于公园本身和市民的种种社会文化活动等事实,实则在于通过对大量事实的选择与取舍,以隐性方式表达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变化:以政府投资修复历史遗迹的事实表明中国人的文物保护意识增强;以传统美德的宣传推广活动说明政府提倡发扬中华传统美德;通过观察道教的复兴透露出居民渴望回归传统和借助宗教探寻生活意义的想法等。既强化了主题,又拉近了与受众的距离。正如美国公共广播电台(NPR)驻中国记者孔安所强调的,他所在的媒体关注点以思想文化为主,“中国最有意思的变化不是在物质上,而是在观念上、文化上、思想上……”[5]
总体看来,《纽约时报》的相关报道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关注中国的变化,尤其是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将叙事重点放在解读城市建设和执政理念、以及居民文化活动和生活态度的改变。二是基于观点表达的主观性内容居多,文章多次直接表达观点,而没有采取外媒惯用的、借援引他人观点间接表达自我观点的客观性做法。此外,文章也体现出与其他外媒涉京报道相同的特点,如从政治角度理解和报道北京,过于强调其作为中国政治符号的意义,对北京地域文化特色的认知存在局限性,以及难以避免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对冲突性话题的偏好。
三、借助文化遗产对外传播北京形象的对策建议
上述外媒对北京历史文化遗产的表达特征,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北京形象在国际社会的传播和认知现状。我国媒体对外传播北京形象的目标之一是通过对外呈现其对北京文化的理解、认知与感受,帮助国外受众在认识北京人文景观的同时,感受北京的城市精神,最终被北京文化所吸引。而借助文化遗产的对外报道呈现北京形象既涉及文化保护、文化再生产等课题,又涉及对北京历史文化底蕴的挖掘和传递,这对传播主体提出了更高要求。鉴于此,本文尝试就北京形象的国际传播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以历史眼光审视城市变迁。古建筑等文化遗产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信息的载体,展现了历史发展轨迹,同时也折射出其所在城市的发展进程,与整个社会发展历程联系在一起。对文化遗产的长期观察引导记者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了解一座城市,决定着媒体对北京形象的表达和认识深度。正如有学者所说:“动态的社会演变和静态的北京文化遗产一同造就了近现代北京的城市景观、文化氛围和精神内涵,也决定着作者对于城市文化的观察体验和城市形象的表达书写。”[6]
第二,以观念为主线,实现与受众思想观念的对接。在北京形象的对外报道中,媒体通常能够做到关注普通百姓,并将居民的社会行为(文化活动)等事实嵌入到景观描写当中,有意识地通过呈现居民的思想观念将报道引向深入。在报道中应以观念为主线,让观念决定事实的取舍。至于观念的选择,在跨文化传播中,当所传达的北京市民的生活观念是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都认同的最基本的人类价值观,即人们对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相同或相近的态度或看法,如健康意识、文物保护理念、环保理念等世界人民的共通理念时,[7]会更容易实现与国外受众思想观念的对接。挖掘并表达北京传统文化蕴含的、与人类社会共通的思想观念是对外传播北京形象的关键。当外国人真正意识到中国文化含有他们所需要的思想时,北京形象才能在国际社会顺畅传播。
第三,以问题意识驱动城市形象表达。媒体在文化遗产的报道中通常带有一种“保护”心态,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媒体的表达,使我们更关注文化保护的立场和观念,而忽略对文化遗产背后孕育的传统文化思想的挖掘。美国记者伊恩·约翰逊(Ian Johnson)曾在接受采访时自称“写作是为了弄清一些问题”,从他采写的《我的北京:神圣之城》中可以感受到“弄清问题”的动力。文章开篇就抛出北京文化是否会随着人们原有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消失的问题,随后借助对一系列事实的观察与描述寻求答案,并在此过程中完成了对北京形象的表达与解读。这启发我们,如果不是出于刻意传播北京形象的需要,而是从研究旨趣出发,以弄清问题为目的了解和认识这座城市,反而能使受众循着“弄清问题”的推理过程认识北京,如此塑造的北京形象或许更加丰富多元。至于问题的选择,可以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但也未必局限于城市建设范畴,城市形象内涵的丰富性使许多问题与城市形象息息相关。
第四,以本土视角对外传播北京形象。媒体报道渗透着传播者的思想观念。表面看《我的北京:神圣之城》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但其实质是由西方文化主导,其内核仍然是西方价值观。由于外国人一般难以真正进入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其对北京的认知就不免存在局限性。为此,我国外宣媒体应发挥自身优势,以本土文化为主体,创新叙事表达。有学者指出,由于人与城间的文化同构,人与城间文化气质的契合,中国人的北京感受、北京印象是从人与城市的文化一体感中自然地发生的,这一语道出我们对外传播北京形象的优势所在。况且,我们有的是机会去挖掘丰富的实践素材和接触报道对象,从日常生活中把握城市文化精神,通过传递居民文化观念实现城市形象的国际传播。
【注释】
[1]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6/content_185117.htm.
[2]王宁,张璐,曹斐.英国媒体中的北京形象:基于《泰晤士报》2000-2015年的框架分析[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7(4):1-6.
[3]曲茹,邵云.北京城市形象及文化符号的受众认知分析——以在京外国留学生为例[J].对外传播,2015(4):48-50.
[4]张颖.从美国主流媒体关于“北京胡同”的报道看北京形象的国际认知[J].对外传播2015(10):50-52.
[5]瞿旭晟,张志安.驻华外国记者的报道理念与模式[J].新闻实践2009(11):54-56.
[6]刘勇,张弛.中国现代作者笔下北京形象的嬗变[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46-49.
[7]黎海波.对外传播中的共同价值观问题初探[J].对外传播,2008(2):36-39.
——围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