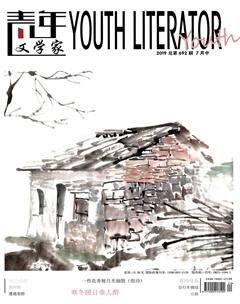残梦中的破碎山河
石桥枫
摘 要:格非是一位真正不断超越自我的先锋作家,从构建博尔赫斯式的迷幻花园到传承本土小说传统,他赋予了笔下小说传统的美感和民族灵魂。格非在坚持知识分子的理性立场同时,兼有文人的感性情怀,《山河入梦》便用迷蒙的意境和感伤的情调为我们刻画了一幅中国式的梦。
关键词:意象;古典;红楼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0-0-02
如果说早期的格非是一位以学习西方、专注于“怎么写”的叙事游戏的作家,那么他的江南三部曲就已然转向了以中国传统式的美感和神韵表现现实社会的精神困境。《山河入夢》是其中之一,这部小说用迷蒙的意境和感伤的情调塑造出了一个中国式的梦,而这一梦境又不断被现实消解,梦中山河也由此破碎。格非在本书中运用了许多典型意象,以历史为背景营造出古典的氛围,且继承了《红楼梦》的写作技巧和表达,显得叙事紧密、语言平实质朴。
一、典型意象
格非在书中塑造了“紫云英”、“梦”这两个典型意象。“紫云英”是核心,在整个故事的走向和主题的阐释上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格非谈写作经历时曾说,“写《山河入梦》时,我想到了阳光下无边无际的紫云英花地……”[1]紫云英为二年生草本植物,生命力顽强。在文本更深一层的意义中,女主人公姚佩佩便是紫云英的象征,她称自己为“被浮云的阴影遮住的苦楝树下的紫云英”[2]。她幼时父母遭难,众亲戚一口咬定是她的“佩菊”一名引起的祸端,由此她不仅要时时刻刻掩盖住自己的过往,还要遭受寄人篱下的苦楚。男主人公谭功达在梅城浴室发现了姚佩佩,进而把她调入县政府工作。他如父亲般的关爱让女孩心里产生了报恩的柔情,并将他视为能够驱散紫云英花地阴影的阳光。但女主人公的心思因谭功达被撤职检查而无情打断,谭功达更是在悔恨和消沉中娶了张金芳,错过了姚佩佩的邀约。同时,姚佩佩经常用紫云英花地的阴影来给自己占卜算命,“我或许生下来就是有罪的呢!……”[3]她似乎从一开始就从紫云英的阴影里窥见了自己的宿命,她在现实中不断的追求阳光、对宿命做出的挣扎和反抗都是无用的:从界牌逃到莲塘,再到普济,她只是走了一个圆圈,最终回到梅城被枪决。其次,“梦”这一意象在小说中的运用同样典型。开篇第一章,姚佩佩说她梦见阎王爷在清明节派鬼去抓她,为首的小鬼和刚才截车的人长得一模一样。谭功达哈哈大笑,“你又没犯什么罪,人家抓你做什么?”但姚佩佩却反问道,“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犯罪?”这个梦在小说的开头看起来很荒诞,甚至有误导读者思路的趋势,但文至结尾就有恍然大悟之感,姚佩佩的命运确实和开头的梦境一样,犯了杀人罪四处逃亡,而车被截的地点界牌,就是她逃亡途中最重要的一环。
格非用这两个超现实空间的叙事与现实空间进行对比,昭示出了人物的宿命和反抗的无力感。此时的意象是一种理智与感情的复杂体验,被作者攫取和加工后成为展开故事叙述的起点,也成为了读者循迹解读文本的钥匙。
二、历史背景下对古典资源的运用
格非笔下所运用的历史背景有意地回避了“正史”,他更喜欢加入自身对历史的感悟和理解,在民间传统和个人体验等方面挖掘历史的“真相”。《山河入梦》的故事发生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但作者并没有重点描绘历史事件或者重现历史走向,而仅仅把历史当做背景,描绘个体的命运和个人在剧变的时代中对乌托邦的追求和沉沦。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都表现出《红楼梦》对其的影响,而在《山河入梦》一书中尤为明显。首先,对《红楼梦》中叙事技巧的借鉴。格非将追求乌托邦这一主题贯穿整个文本,“如果完全没有乌托邦的东西,没有一个人对未来社会对自己的命运没有任何想象性的东西,那就非常可怕”[4]。又运用《红楼梦》的家族叙事,通过一个家族中第二代人的日常琐碎之事及其社会关系网,来展示当时的社会图景和不同道路的探索。主人公谭功达是梅城一位拥有乌托邦梦想的县长,他随农业代表团去过外国之后,便不顾连年饥荒和县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大力修水库、漠视百姓基本需求转而建起了公园、在水库被冲垮时仍惦念着无用的沼气池。此外格非在叙事中还效仿了《红楼梦》圆形的叙事结构,以同一件事开头并以其做结尾,并用视角的不断变化来丰富叙事技巧。小说故事是从姚佩佩跟从谭功达到普济水库视察开始的,谭功达的膝盖上放着一张手绘的梅城县行政区域规划图,他还不时用一支红铅笔圈圈点点。而在文本的最后,姚佩佩留下的信件中再次提到这件事,原来地图边缘的空白处,谭功达用红铅笔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她的名字。看似是主人公无意寄出的信,其实是作者有意而为之的笔法,使得文本首尾呼应,故事更为完整。第二,对《红楼梦》中悲剧意识的承袭。《红楼梦》写了一个大家族由盛而衰的悲剧故事,而在格非的小说中,悲剧正是他所展现的一个重要方面。千百年来人类的斗争都是为赢得一个安定的生存环境,梦想都是能够创建一个和谐社会,所以人类社会上很早就出现了像“桃花源”、“天下大同”等乌托邦情结。在《山河入梦》中,谭功达一直是在为建立理想社会而努力,甚至呈现了各种构筑版本,但均以失败告终,正如他自己所说,“你只要想去做这个桃花源,可能就会有问题。用阿多诺的话来说,产生了强制、暴力和集权。”[5]他个人不满于日益庸俗化和利益化的现实境遇,想要去构筑一个乌托邦理想社会,他不惜因此耗尽才华抛弃荣誉,甚至可以付出生命。但他最终发现,不仅这个构筑纠集着太多的矛盾、同样充满了遗憾和罪恶:花家舍的人与人之间冷漠,没有隐私,小韶的哥哥因输掉一场篮球赛受到各方面压力而发疯……他绝望的发现,理想社会的追寻和构建并不是个人所能完成的,人类自私与贪婪的本性让一切都变成了空想。第三,对《红楼梦》中“宝黛型”痴男怨女式爱情观的继承。谭功达和姚佩佩相见一开始就带有“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情调,“她那尖尖的指甲从谭功达手背上划过,印痕却留在了他心里。”[6]谭功达本身就带有宝玉的痴,他身为一县之长却不懂官场,他心地善良、天性烂漫,看到漂亮女孩子会发愣,汤碧云甚至说他是“花痴”病,格非笔下的谭功达便是建设年代的贾宝玉。姚佩佩的美和凄苦和黛玉一样让人心碎,她和黛玉一般原本家境优渥而后双亲皆亡,生活的变故让她们变得对人世小心翼翼。同时,姚佩佩和黛玉的爱也如出一辙。她的爱情十分含蓄,眼看着谭功达与白小娴相亲又无可奈何,只能偷偷在她照片上用胸针扎一个洞,得知谭功达给自己在集市上买了泥娃娃十分开心却又担心他会把坏掉的送给自己,她在逃亡的路上依旧把谭功达当做自己最信任的人,她的爱真挚深沉,凄美动人。
格非在《山河入梦》中可以说是直接地向《红楼梦》进行了靠近,恰如书中姚佩佩的一席话,“再好的大观园,也会变成一片瓦砾,被大雪覆盖白茫茫一片。”他对古典资源和氛围进行了开拓性运用和塑造,用细腻的叙事、典雅的语言和循环如春秋的内在结构为读者展现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学盛宴。
纵观格非在《山河入梦》一书中所运用的手法、塑造的人物,不难看出他已经在利用传统的古典资源,在典雅细腻的书写中关注着中国一代又一代人对乌托邦的“追梦史”。他笔下的女性人物丰满动人,虽然《山河入梦》中继承乌托邦主题的是男性,但女性在小说中占据了绝大的篇幅和重量。格非“男性视角”下的女性书写大致在书中分为三类——以姚佩佩和白小娴为代表的反抗者、以汤碧云为代表的权色制度下的牺牲者和以冯寡妇为代表的历史的凋零者。这三类女性形象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她们或悲凉或恍惚的身世都汇聚着格非对人类命运的反思。“就小说而言,写作应是一种发现,一种勘探,更应是一种谛听。”[7]山河入梦,梦的是理想的山河,让理想山河破碎的是铁铮铮的现实。山河入梦,破碎山河里带着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之梦,对破碎山河的理想梦坚持继承下来的是知识分子的信念和向往。
注释:
[1]格非:《最有意思的是在心里生长》,《长篇小说选刊》2007年第2期.
[2]格非:《山河入梦》,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10页.
[3]同上,第184页.
[4]《格非:不能把历史当作晾在那儿的风景》,中国青年报2007年1月.
[5]《格非:总有一群柔弱的人在支撑着昂贵的理想》,《野草》2006年第6期.
[6]格非:《山河入梦》,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4页.
[7]格非:《小说艺术面面观》,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