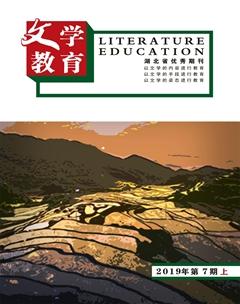无力的皈依:《大漠孤行》中的主体困境
内容摘要:作为美国自然作家爱德华·艾比的代表作之一,《大漠孤行》深刻地体现出作家在面对自然时复杂而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作家渴望融入自然,用自我意识渲染荒野的静谧与壮美;另一方面,作家必须尊重自然的自在性,同自然保持距离。这种悖论式的心态典型地体现了自然书写中人类主体所面临的“归化”或“异化”自然的困境。
关键词:爱德华·艾比 《大漠孤行》 主体困境
作为美国20世纪最著名的自然作家之一的爱德华·艾比(Edward Abbey),其《大漠孤行》(Desert Solitaire)(1968)蕴含了关于文明与自然的最为深刻和真实的反思,不仅被誉为美国文学的“次经典”(minor classic),而且极大地启迪了之后的美国自然保护运动。对于该作品中的生态思想,国内外诸多批评者们已经进行了深入、全面的探讨,揭示了艾比“对唯发展主义的批判和对环境行动主义的倡导”,以及作家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倡导生态整体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理念,还有他对于最终实现人与自然万物自由平等地和谐共处,“彻底融入自然”的渴望。[1][2]101
在论述作品中体现的环境伦理时,批评者们普遍认为艾比所持的是一种人与自然之间应实现“对立-妥协-平衡”的观念,即人与自然的相处模式应该是在对立之下尽力做出妥协,并找到一种人的生存与自然的维系之间的平衡。[3]在《大漠孤行》中,爱德华·艾比的确认为这是一种理想的相处模式。在作品末尾叙述人将离开沙漠前总结道:“秘密在于平衡。有节制的极端主义。对于两个世界(自然和文明——笔者注)都物尽其用。”[4]298他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和梭罗不同,既要在荒野中寻求心灵的宁静,又要在文明中享受生活的舒适和伴侣的慰藉。自然和文明也要在人的有节制的生活中达成一种平衡。
然而,当叙述人在做出这一结论时,却难以掩饰心中对于自然和文明之关系的种种困顿之感,这种困惑在作品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正如有评论者指出:“在整部书中,我们处处可以感到作者的困惑和难以摆脱的自相矛盾。这来自人类对自然和对文明的双重需求。”[5]217事实上,叙述人发表平衡观的见解是在最后一章,其标题就是“基石与矛盾”。而在全书的第一章中,作者就告诉了读者这“基石与矛盾”之所在:“我梦想着一种坚硬而残酷的神秘主义,在其中赤裸裸的自我同非人类世界融为一体,然而却仍能在某种程度上生存下来,不受影响,保持独立,且截然分开。基石与矛盾。”[4]6在这里,艾比精确地点出了其自然书写中内含着的一个矛盾:自我与作为他者的自然之间的矛盾,或者说主体(ego)的认知与生态(eco)的客观存在之间的悖论。
这一矛盾奠定了《大漠孤行》的叙述基调,也是叙述人在其长达半年的大漠生活中在思想上和行动上表现出的多次犹疑和摇摆的根源。可以说,在其作品中,“艾比从未逃出过这些矛盾,也没能解决它们,而是试图把这些矛盾展现出来,以作为自己挣扎的证据。他一方面要同这个神圣的地方融合,同时又保留住足够的自己来记录和限定这个过程。”[6]而这些矛盾背后所折射出的是自然书写中的主体困境。
一.自然书写中的主体困境
自然书写作为一种文类描述的是主体或自我对自然进行观察、探索和思考的过程,而其作用是通过这一过程“发现某种自我,并且更重要的是,发现一个‘真正的、‘真实的世界”,继而将所发现的信息传达给读者。[7]自然书写所发现的自我或者世界通常是与文明相对的,和荒野相连的,也就是说,用荒野中的自我来弥补在文明中迷失的人格,用自然的真实来对抗资本化、工业化的社会。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自然作家们采取的策略是异化自然,或者说是将自然他者化、陌生化,也就是突出自然的纯洁性、神秘性、独特性以冲击读者的感官,让他们达成自然重于一切的启示。
然而与此同时,书写本身就无法避免主体意识的投射,更何况自然写作的内容就是“描述作者由文明世界走进自然环境的那种身体和精神的体验”,其所追求的效果又是人的自然意识的觉醒,或者是向读者发出尊重、保护自然的劝喻和呼唤。[5]1这决定了自然写作在探索、再现自然的时候会注重弥合自然与主体的分隔,强调人类与荒野的联结,反映在美学层面就是归化自然,或者说将自然自我化、熟悉化,也就是突出自然的可知性、联结性,甚至要赋予自然一种人格化的色彩,以更好地向读者传达自然意识的意义所在。
这一矛盾性决定了在自然书写中主体会陷入一个无法摆脱的困境:一方面作为身处荒野中的人类努力保持同自然万物的距离,不张扬自身的主体性,不试图介入和主宰自然中的其他组成部分,甚至愿意同他们建立一种主体间性关系,即承认“每一个物种都具有主体性,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都有自己的主动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方式,有自己独特的显现方式,而且每个物种都是一个独立的统一体”,进而“形成自己的主体与他者的主体之间的主体间际交流”。[2]1但另一方面,人类主体又必须面对的事实是自己是荒野中惟一的思想者和言說者,对自然他者的描述和思考必然会对它们施以意识和主观建构,这样自然书写中的主体就成为了超越性的主体,扭曲了其不干扰自然自在的本意。此外,人在与自然交互的过程中,又因为有更大的主观意志力和行动力而往往占据着上风,与其他自然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失去了其所追求的平等性。这些构成了自然文学中主体的困境。
以深入荒凉、广袤的美国西部大漠独居和探险而闻名的自然作家爱德华·艾比以极为坦诚的态度对待这一困境,更是在《大漠孤行》中真实地记录了身处荒野之中主体所遭受的困惑与两难。梳理和分析该作品中主体所面对的困境,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艾比作品的深刻性和丰富之处,也能够就人与自然应构建何种生态关系带来更多的启发。
二.融入或远离之徘徊
在《大漠孤行》中,叙述人作为公园管理员,只身来到犹他州东南部的拱石国家保护区(Arches National Monument),在荒凉的沙漠和峡谷之间度过了四月到九月的半年时间。在这半年里,他要么沉浸在宁静的沙乡中,要么穿梭在峡谷的激流间,大部分时间都是孤身一人,直接面对赤裸裸的自然。身处大漠荒野中的叙述人一直怀有一种融入自然的强烈渴望,他努力找寻同自然万物的联接,希冀同自然中的其他物种平等自由地共处、交往,并惬意自如地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在大地上游走、生存。然而与此同时,他也警惕自己介入自然的危险,不断告诫自己要保持同自然中其他生物之间的距离,因为保护自然的最佳途径就是要远离自然,让自然万物在不受人类干涉的情况下自在地生长繁衍。全书自始至终叙述主体都在这两种倾向之间犹疑、徘徊,所产生的裂隙留给读者以强烈的印象。
在初入大漠的第一个清晨,独居的叙述人目睹了初升的旭日映红了远处的雪山和近处的沙丘的壮观景象,他欣然说道:“我们相互问候,太阳和我,隔着九千三百万英里的黑暗的空虚”,而且“我并不孤独。三只渡鸦在平石边盘旋…要是我懂得它们的语言就好了。我宁愿同地球上的鸟儿交流思想……”。[4]7这种希求与自然万物为友的思想使人不禁联想到了瓦尔登湖畔的梭罗。在之后的体验中,叙述人也不断地寻求靠近自然,与自然中的其他生物甚至是无生命物体交流。他试着与响尾蛇和平共处,想与住地附近的一棵杜松找到联结,向往着拥抱群山和天空,愿意“直接地、赤裸裸地向宇宙敞开意识的怀抱”。[4]259看到跑走的小鹿,他喊道:“回来!我想同你聊聊!”[4]36在沙漠的黑夜里行走,他打开手电,却意识到“它把人和周围的世界分开了。如果我打开电筒,我的眼睛适应了它,那么我就只能看到我前面的一小片有光的地方;我就被隔离了”。[4]14这种被隔离的担忧和对融入自然的追求在《大漠孤行》中极为强烈。
正是因为叙述人意识到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生生相息,自然万物组成了“一个井然有序的行动和过程的体系”,他才希望接近自然,在荒漠的怀抱中徜徉和自由地栖居。[4]113对于他来说,接近自然给予了他一种“怀旧感”,走进荒野就如同回到了“我们都源于其中的大地母体”。[4]189人类长期以来已经丢失了这种对母体的依赖感,但这种渴望“依然存在,遥远,同时亲切,它埋藏在我们的血液和神经中,超越我们,不受束缚”。[4]190这种视自然为家园,盼望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观念契合了生态思想家们所主张的生态整体论思想,即认为“人不是与自然分离的个体,而是自然整体中的一部分”,自我的实现“一个不断扩大与自然认同的过程, 其前提就是生命的平等和对生命的尊重”。[8]64
带着这样的理念,沉浸在沙乡中的叙述人也享受到了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巨大满足感和身心被自然的亲切与宁静所充溢的幸福感。这在全书叙事的高潮部分“沿河而下”这一章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这一章记述了叙述人和一位友人沿着科罗拉多河漂流而下,探索即将被水库淹没的峡谷地区的经历。他们在河滩上做早餐的时候发现食物和水里都掺杂了泥沙,然而叙述人却毫不介意,因为“沙子成为了我们存在的一部分,我们就像呼吸一样认其为理所当然之物了”。[4]186峡谷中漂流数日之后,两人是如此地陶醉在自然的静谧与神奇之中,竟然已经不能区分出自我同自然的界限了,已然同峡谷融为一体,达到“物我合一”的境界了:
“‘谁是拉尔夫·纽库姆(同伴名——笔者注)?我说:‘他是谁?
‘是啊,他说:‘谁又是谁?什么又是什么?
‘对啊。我说。
我们正在融合,分子交织在一起。就是所谓的主体间性——我们都染上了河流和峡谷的颜色,我们的皮肤和背阴处的河水一样是红褐色的,我们的衣服覆盖着泥沙,我们的赤脚上板结着淤泥,像蜥蜴的皮一样硬,我们的胡须被漂白成沙子的颜色——甚至还能透过我们的眼睑看到的一点眼球也变成了珊瑚似的浅红色,那是沙丘的颜色。而我想,我们闻起来也像鲶鱼的味道吧。”[4]209
在另一个地方,面对无垠的荒漠,他也抒发了同样的感慨,甚至想象自己从人类羽化成为了自然界的其他事物:
我感到自己陷入到了这景色之中,像一块石头,一棵树,抑或是一片小小的、模糊的、静止的轮廓一样,被固定在了这个地方,披上了沙漠一样的颜色,带着想象的翅膀,通过飞鸟的眼睛俯瞰着自己,看到一个人类的身影变得越来越小。随着鸟儿高飞,进入到那夜色之中,这风景也开始后退,变得越来越小。[4]243
可以说这种对与自然俨然交融境界的追求是支撑叙述人不断深入荒野探险的动力所在。作者也似乎通过对于这种境界的描写激发读者对于自然的崇敬与向往,这也是《大漠孤行》拥有的巨大魅力之所在。
然而,叙述人在找寻与自然的联结的时候也清醒地觉察到,所谓的融合和联结,不过是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已,无论自己如何思考或行动,自然都静存于彼处,不会受自己所动,这也使他反思自己融入自然的冲动过于虚无缥缈,进而“通过反讽、幽默和对事实或理性的强调抵制自己身上的浪漫主义倾向”。[9]39因此,在强烈期望着融入自然的同时,在作品中叙述人面对自然也是迟疑的,或是现实的,他意识到自己的荒野探险破坏了自然本有的宁静,而尊敬和保护自然最好的方式是远离它,而非靠近。就像许多生态思想所劝诫的那样:“人类的生活应最小而非最大地影响其他物种和地球。”[8]64
作家艾比曾说:“万物除了他们自身之外,再不意味着其他”。[9]42在《大漠孤行》中,叙述人也一再强调这种自然的自在性,经常在靠近或接触自然之后立即笔调转向,强调自己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不正当性或可笑之处,向读者暗示:远离自然才是应该的选择。当叙述人匍匐在地上观察能够同自己和平相处的响尾蛇同另一条蛇交媾之时,他立即认为自己是一个“无耻的偷窥者”。[4]22他试图同驻地附近的一棵杜松产生联结,却“失败了”,因为“我一直无法发现杜松的本真”,“直觉,同情,移情,都无法指引我找到这个生命的内心”。[4]30-31在小鹿并没有感受到我的善意并奔逃消失后,他问自己:“我为什么还要再打扰他们?”[4]36他认识到,自在的自然或许更多地只是物质性的存在,试图融入自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他认为荒野是一个“拒斥他”的地方,是“人类不需要涉足进入”的避难所。[4]254
这种既渴望接近自然、融入自然,又意识到自然之不可接近性和自在封闭性因而还是远离自然为好的矛盾心态一直延续到了全书的末尾。在叙述人即将要结束管理员的工作,离开保护区的时候,既对陪伴自己半年的拱石、杜松和沙丘恋恋不舍,称它们为“我自己的,我的孩子們,我所拥有的,我因为爱的权利而拥有的,因为神圣的权利而拥有的”,充溢着与沙漠的一切找寻到联结而又即将失去的感伤,又同时头脑冷静地意识到:“这片恬静而原始的处女地会因我的离开和没有游人而充满感激,会为此长纾一口气…当我们都最终离开时,这片地方和这里的物种都能够回到他们古老的状态中去,不经受人的匆忙、焦急而沉郁的意识的观察和搅扰。”[4]300可以说,叙述人在大漠中始终期冀着靠近,却又清醒地同自然保持着距离,他的徘徊代表着众多自然爱好者的纠结和矛盾复杂的心态。
三.自我与自然之挣扎
透过《大漠孤行》可以清楚地发现,在靠近或远离自然之徘徊的背后,是作者更深层次的认识论上的矛盾,即面对自然,是以自我为中心,用自我的认知体系去统摄自然中的万物,找寻自然对于自我的意义,最终实现自我中荒野维度的发现和自我意识的唤醒,还是以自然为中心,意识到任何用人类的认知去归纳和内化自然的做法既是对自然都是一种压迫,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自然有其无比丰富性和深刻性,超越人类的认知,因而尊重自然意味着承认自然的客观存在性和不可知性,以及人类及其意识都是自然的一部分。这一自我(ego)中心或自然(eco)中心的矛盾像两股暗流,始终汹涌在文本之中。正如有评论者所说:“主导自我之外的存在和臣服(或从属)于它的渴望同时存在,构成了本书的基本张力”。[10]
在艾比的另一部作品《向着家园的旅程:为美国西部辩护》中,他曾说《大漠孤行》“是个人的历史而非自然的历史”,是对他“旅行和探险经历的叙事性记述”。[11]20可以说,《大漠孤行》记录的是自我的荒野冒险史,书中的叙述人也是从自我出发,以他的主观视角去探索、描述和思考自然,并试图将自然统摄到他的思想和情感体系中来。在到达大漠的第一个早上,面对天高风清、巨石苍茫的美景,他不禁拥有一种强烈自我占有欲和统治欲:“我想知晓一切、拥有一切,亲密地、深邃地、完整地拥抱这美景”。[4]6他认为,人在荒野之中总会用自己的主观观念去统摄自然万物,比如对待形态万千的拱石,虔诚的西部人看到的是造物主的伟大,地质学的学生发现的则是自然的统一,“你或许看到的是一个象征、符号、事实或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或者是一个包含所有事情的意义”。[4]41拱石对于深入荒野中的人来说,其价值是“激起人们的感官,让思想惊奇地跳出习惯的藩篱,迫使我们重新唤起对于伟大的意识”。[4]41在大漠之中游荡的人在叙述人看来不仅是一位旅行者、探险者,更是一个自我的发现者和“生命的勘探员”,去找寻“真理的显现”,即自然能够给人类提供的财富。[4]49这种对自然对于自我的意义的强调正是以自我为中心去发现自然,统摄自然的自然观的表现,也契合了自然书写的传统,因为“毕竟荒野是强化人类意识的契机,促使他们对照着非我来定位自我。荒野也是内省的跳板。而且最伟大的文字,那些能够照亮处于中心位置、并能感受到自我中心地位的生命的文字,强化了这一过程。”[12]
此外,《大漠孤行》中对于荒野的描述和展现总是充满着浓厚的主观色彩,叙述人总是用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去观照自然万物,理解他们,甚至介入他们的存在,“艾比强大的自我几乎在每一章都有所展现”。[13]尽管叙述人在全书开始信誓旦旦地说要“抑制住内心对于自然人格化的冲动”,但在他接下来的叙述中这种冲动却常常主导着他。这在叙述人对沙漠植物的描述中体现得最为强烈。在他的眼中,岩蔷薇是“最可爱的花儿,像一个美丽的小女孩一样欢乐、甜蜜”,刺梨花“对蜜蜂的进入抱着性感的温柔”,仙人掌“矮小,卑微,默默无闻”,而丝兰“美丽却怪异”,这些植物在大风缺水的沙漠严酷环境中显得“勇敢无畏、生机勃勃”,在沙漠的“开阔和自由中,爱绽放得最为灿烂”。[4]26-29这种对自然的人格化渲染在对于岩石、峡谷、流水、风、秃鹫等等的描述中都显露无疑,是自我中心化的自然书写的外在表现,在文本中牢固树立了主体的中心地位。还有评论者指出,在作品诸多场景中都出现了篝火,对自然的描述都圍绕着篝火展开,意味着作为生火之人的叙述人自我意识的中心地位,从叙述人第一天晚上生起篝火到他离开前看着同一地点的篝火渐渐熄灭,象征着自我意识来到荒野并最终远离,而“‘仪式性的篝火是全书的中心点”。[11]22
然而,对于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然书写,艾比也有着警惕性的反思,因为他意识到“人类世界的艺术和想象永远无法和真实的自然世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相匹敌”。[14]93在全书的开始,艾比就在序言中承认他的作品“不能涉及或展现构成存在本质之真实的统一联系模式”,因为他自己“关于真正的存在本质一无所知,也未曾见到过”。[4]xi自然具有单一的物质实在性和内在价值,其深度和广度是人类的认知无法把握的。在大漠中深居的叙述人也充分地感受到在永恒广袤的自然面前人类的思想和痕迹都是微不足道的,人也不能凭借个人意识这种“毫不重要甚至可以说是虚无缥缈的现象”来透彻地理解这个世界。[4]144他感叹道:“人们在世间匆匆,城市兴起衰落,整个文明出现消失——然而地球仍在,改变微乎其微…人是一个梦,思想不过是虚幻而已,只有石头是真实的。石头与太阳”。[4]219沙漠中的斜阳,舞动的卷风,燃烧的灌木丛,自然的万物对于人意味着什么?“什么都不是。它们就是它们,不需要什么意义。大漠躺在身下,远远超越了任何人类可能的质化。因而,它是崇高。”[4]219在另一处,他又进一步说道:“大漠无言…它处在那儿,是赤裸裸的存在,罕见、空旷、庄严,完全没有价值,不招徕爱而是沉思”。[4]270此外,“大漠具有某种品质,这种品质是人类的感觉无法内化的,而且至今为止也没能去内化它”。[4]272
这种观点和人类在荒野中寻找意义和价值的思想可以说是针锋相对的。自然有其纯粹的自在性,任何用人的思想去统驭它的尝试都是徒劳的,因而真正的尊重自然就要以生态为中心作为其认识和行动的出发点,意识到自然是不能去定义、去理解、去归化的。因此,当叙述人在荒野中探险时,他总是时刻提醒自己,不要用自己的意识过多地玷染自然,尊重自然还是要尊重自然的自在性。在听到远处鸽群的叫声时,他起初陷入了对于鸽子发出的“悲悼”而“哀怨”的鸣叫的想象之中,认为那是“被分隔的心灵在努力重拾失去的联系”,然而紧接着就反思道:“毫无疑问要拒绝这种类比。把对人类的同伴更适合的关心施加给鸽子是愚蠢的和不公平的,既然鸽子有它们自己的严肃的关怀”。[4]18-19拱石的壮观和瑰丽都不应是喜爱自然的原因,沙漠的缺水和狂风也不应是讨厌自然的理由,自然有自己的存在逻辑,它的温柔或严酷都是其客观的存在,并不迎合人类的悲喜。他也拒绝为自然景观命名:“为什么要命名它们?虚荣。虚荣,只是虚荣而已:对命名的渴望同占有欲一样糟糕。让它们独自存在——它们就还会留存几千年,没有任何来自于我们的荣耀。”[4]288
在全书的多处,无论是在攀登覆雪的高山,还是在幽邃的溪谷洞穴中,叙述人都不断地拒斥自己内心将主观意识强加于自然之上的冲动,转而强调自己在荒野中的探险是要“直面赤裸的存在,本原的,基础的…不带任何人为赋予的品质”。[4]6艾比在其日记中曾说,自然的吸引力就在于其“未经人类意识的投射,未被艺术、科学或神话所阐释,表面上没有人类的任何痕迹,同人类的室内世界没有明显的关联”。[14]185而正是自然拥有这样的品质才能让处身荒野之中的人直面赤裸的存在,明白自然的神奇和伟大之处,从而发自内心地去尊重和热爱自然。也就是说,正是自然世界的自在性使其对于人类具有独特的魅力和价值。
从靠近或远离之徘徊到自我或生态之挣扎,《大漠孤行》中的主体在认识和行动上都遇到了强烈的矛盾和困境。这一困境决定了艾比作品中的自然书写具有很大的复杂性,也使得其文本更加丰富和真实。正如其传记作者所总结的:“双面性是艾比作品的关键特征。”[15]这种困境不仅是像爱德华·艾比这样热爱自然之人的困境,也是自然书写和生态学思想的困境。对于这一困境进行深入地思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大漠孤行》的思想,也能够对于自然书写这一文学门类与生态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1]王俊暐.“像大地一样思考”——论艾比的生态思想及其启示意义[J].鄱阳湖学刊,2011(5):92-101.
[2]王诺.生态与心态:当代欧美文学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朱新福.美国文学上荒野描写的生态意义述略[J].外国语文,2009(3):1-5.
[4]Edward Abbey.Desert Solitaire: A Season in the Wilderness[M].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1968.
[5]程虹.寻归荒野(增订版)[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6]Jonathan Levin. Coordinates and Connections:Self, Language, and World in Edward Abbey and William Least Heat-Moon[J].Contemporary Literature, 2000 (2):214-251.
[7]Mark Mossman. The Rhetoric of a Nature Writer: Subversion, Persuasion, and Ambiguity in the Writings of Edward Abbey[J]. 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 1997 (4):79-85.
[8]李金云.深生态学:一种后结构时代的启蒙辩证法[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62-64.
[9]John R. Knott. Edward Abbey and the Romance of Wilderness[A]. Thomas J. Schoenberg and Lawrence J. Trudence.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 Vol. 160[C]. Detroit: Thomson Gale, 2005:38-48.
[10]Scott Slovic.Seeking Awareness in American Nature Writing: Henry Thoreau, Annie Dilliard, Edward Abbey, Wendell Berry, Barry Lopez[M].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1992.
[11]Paul Bryant. The Structure and Unity of Desert Solitaire[A]. Thomas J. Schoenberg and Lawrence J. Trudence.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 Vol.160[C]. Detroit: Thomson Gale,2005:20-28.
[12]Bruce Berger. The Telling Distance: Conversations with the American Desert[M]. Portland: Breitenbush Books, 1990:6.
[13]Don Scheese. Desert Solitaire: Counter-Friction to 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A]. Thomas J. Schoenberg and Lawrence J. Trudence.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 Vol.160[C].Detroit: Thomson Gale, 2005:11-20.
[14]Edward Abbey. Confessions of a Barbarian[M]. Ed. David Peters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94.
[15]James M. Cahalan. Edward Abbey: A Life[M].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2001:274.
(作者介紹:黄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外语教学部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