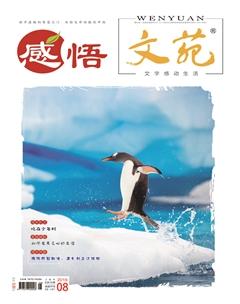父老
权蓉

我们爱口头上说自己“老了”,但细究起来,是没有这回事的。骨子里都是青春盎然、活力四射,心里住着个小毛孩。在外和别人打交道时一副沉稳模样,回家招猫、逗狗、撒娇、抠脚的比比皆是。
而我们的父母,还陪着去听演唱会,还在抖音上反串表演圈粉,还给我们零花钱。看那些煽情广告——父母老了,孤独地等儿女的电话还来气,说这都没有朋友吗,自己没有社交?
这样的他们,怎么会老呢?
是在某一天,我们察觉到了原来父母是有老这回事的。
其实那天和平常一样,只不过你多看了一眼——
可能是染发剂,可能是某个药瓶,可能是换鞋角落里多出来的扶手,可能是锐减的菜量,可能是变软的米饭,可能是记了许多密码的小本子,可能是手机上硕大的字体,可能是多穿的外套,可能是你买了却闲置的智能家电……
细细一究,就扯出了“老”这根伏线。
关于老,我们瞬间就能数出很多——
叶芝说: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意昏沉,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慢慢读……
朱生豪说:不要愁老之将至,你老了一定很可爱。而且,假如你老了十岁,我当然也同样老了十岁,世界也老了十岁,上帝也老了十岁,一切都是一样。
杜拉斯说: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
……
数着数着才发现,这不是老,不是老的处境,而是年轻的欢歌。
头白了,睡意昏沉,炉火旁打盹,眼花得慢慢读不下去书;一切都老了十岁,看起来守恒,可自己的身体精力不再一样;老了后向自己走来的男人,不自我介绍就不知道他是谁家的谁。
可能《枕草子》里那句才的确是老的注解,清少纳言说:大家不在意的事情,人家的母亲的年老。
人家的母亲的年老——我们不解她雷打不动地去跳广场舞,怒她早高峰跟着上班族挤车出行,责她公共场合说话太大声,疑她摔倒在车前碰瓷年轻人,厌她总转那些乱七八糟的养生,疼她因小失大被骗去参加低价团的采购旅行,漠视她说的邻里往来亲戚情分……
这些母亲,可能在我们自己家里,可能在朋友家里,可能在报纸的头条上(有的被冤发声解释了,有的确有其事坐实了),可能在反对者签名的投票栏里。
最终,她们和年轻人,和人家家里年老的父亲,都一齐烩进人海这口锅中浮沉去了。
人的活法不一样,所以人的老也不一样。
有的父母不到六十,已吵嚷着让儿女尽孝;有的父母年逾古稀,还四处奔忙谋份出息;有的没老倚老卖老;有的已老却老骥伏枥;有的年轻时温柔,年老变成了暴君;有的年轻时暴君,年老变成了佛心。
自然,亦有始终暴君,或始终温柔的。
可无论如何,不能忽略的是,他们都在渐渐更老了。
那天偶然看到一档节目,里面唱了一首父亲写给儿子的歌。
其中一句是:让你太像我,我很抱歉(you're so much like me,I'm sorry)。
这来自父亲的告解,让太多人湿了眼眶。
我们在成长中,也和父母有了某种程度的和解,但如此袒露心声的,可惜并没有太多。他们更多的是,想在乎又别扭,想洒脱又固执。
我们聊到察觉父母什么时候变老,有很多答案——
母亲来问自己某件事怎么处理;父亲突然递过一支烟或者碰了一杯酒;默默计算你一个月打电话的次数并计较那个电话是打给谁的;夸赞别家某个他们的同龄人的衣着;总说病了去医院检查却又什么事儿也没有;被骗了钱回家不敢告诉家人但她们老年团的都知道;比儿女收入、比孙辈成绩;给他们报了全科体检到了时间却又不愿意去……
正视人的必经历程,这些也就会有更好的处理方式。
小时候被问“一斤棉花一斤铁,谁重”,你说铁重,被父亲一顿教训。
你长大了,有一天又有一个类似“一斤棉花一斤铁,谁重”的问题,父亲答,棉花重。
那一刻,你没有嘲笑,也沒有说“一样重”这个答案,铁和棉花都不重要。
你只是觉得,父亲老了,人生这条路,你要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