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我的学问和人生
整理_曹东勃

邓正来(1956—2013),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翻译家,社会科学学术组织者,曾任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2008年之后创办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讲这个题目,完全源于我个人生活经验。
人生讲什么?讲气象、讲境界。人不正则无气象,无气象则无大学问。如果一个人日常生活都在偷鸡摸狗,不可能做出大学问来。
学术讲什么?追比先贤。不是追比你的同学,你的老师,要追比千百年来的历代先贤。
我的生活脉络
我是1978年的大学生,在四川外语学院读书,1982年考入北京外交学院,但我硕士还没读完就当了学术个体户。2003年,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张文显教授邀请我加入。
我和你们一样年轻过,你们不仅仅是一个个人,也是社会中的人,是现实中的人。你们必须考虑个人同这个教育体制、这个学术体制、这个社会体制之间的关系。在考虑这些关系的过程中,我们要考虑如何在这样一种体制中养成独立品格。
大家一定要记住,品格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建构,浩然正气是养出来的,没有独立之品格,一定是fashionable,是时尚的,跟风的,今天刮东风你就说东风,明天刮西风你就说西风,后天是和谐社会你就和谐社会。
人的品格不是到了我这把年纪才能培养出来的,而是从小就做起的。没有独立品格,就没有自由意志,没有自由意志,就没有个人的学问。
我的学术研究脉络
我1987年翻译了博登海默的《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一书,后又读了很多政治哲学方面的书,逐渐扩展到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
1991年开始,我逐渐在四个领域中做了些研究:首先是提出了“市民社会与国家”这一研究范式。90年代以前,我们有一种“从上往下”的思维定势。国家好个人才好,有了明君国家才能好,于是一届届地企盼明君。我们恰恰忽略了另一条路径,一个自下而上的进程,忽略了我们自身的存在、价值、意义和影响。
第二,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自主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本质意义上是一个舶来品,西风东渐的产物。我们在引进介绍的过程中却丢失了自己,忘记了我们本可以进行学术的生产和再生产的。今天的教科书中充斥着对西方理论框架的照搬、误用和滥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要强调学术自主性。
第三,自苏格兰启蒙学者、斯密、休谟至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研究。从事自由主义研究,除了我个人的经历之外,也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有关。自由主义绝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在西方有三大脉络,柏拉图到卢梭的唯理论的自由主义,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的非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还有传统中间道路的英美自由主义。如不认真研究,我们其实并不清楚这些区别,因而就出现各种行为大相径庭的人士都竞相自称自由主义的混乱局面。
第四是法学的研究。这四个领域各不相关,都围绕一个核心问题,这也是鄙人之所以能够继续活下去的一个重要动力源,即社会秩序的性质及其建构的合法性问题。这与人生何干?这源于我生命中的困惑。
我出生在上海,读小学时,当时老师灌输给我的“道理”是:在万恶的旧社会,人民承受着无穷的奴役,瘦小的孩子还没成人就要悲惨地去给大肚子资本家做童工干活,受尽剥削和虐待。但1970年,我14岁,也去当了童工。我当时的疑惑是,为什么人民站立起来的新中国里,我还是逃不掉当童工的命运?
后来我到四川当工人,每星期天都到资料室偷书看。有一次被看守的一个老右派抓住了,听了我的解释,他告诫我下次直接从前门进来就好了,实际上是帮助我“偷”。
这些成长经历,迫使我逐渐产生了一些朦胧的理论追问:“是谁规定了这样的权力把我——和现在的你们一样拥有独立思想和自由意志的人投掷并捆缚在这样一种社会秩序中?”
这个问题再提升一步,是谁规定了这样的权力把我和我的同时代人投掷并捆缚在这样一种社会秩序中?是谁规定了这样的权力把几亿中国人投掷并捆缚在这样一种社会秩序中?是谁规定了这样的权力不仅把几亿中国人而且把他们的下一代人也强制性地投掷并捆缚在这样一种社会秩序中?
我们绝不是在谈论一个概念性的问题,不是虚无的问题。真正的学术关切、学术问题一定是与生活息息相关,从来没有一位大师会出于生活无关的动机而做出让人尊敬的成果,从来没有。柏拉图写《理想国》,是对当时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和城邦制度的无可容忍以及由此所激发的现实批判。
你们都是读书人,在做学问,如果你们所思考的问题与自身的生活不相关,一定不会留下来,一定是过眼云烟。学术一定对现实有着责任,对生命要有担当,否则是做不下去的。
我的学术活动脉络
我只参加过三个比较重大的学术活动。
一是“学在民间”运动。任何真正的学术一定不在官方,一定在民间、在个人,学术一定是个人在自由状态下思考而成。
二是学术规范化运动。《政治学研究》《中国法学》等国内期刊,在1995年以前几乎都没有注释。一篇一万余字的论文居然除了马恩全集之外再无其他注释与参考文献。当时学术界好多人还不知道国外的匿名评审制,还不清楚学术价值需要同行、同道的评议,还在为教育部颁发的奖项而沾沾自喜。
大家都知道西南联大,知道陈寅恪、费孝通、陈岱孙,但当时叱诧风云的教授中没有他们,当时国民党奖励的教授一大把,那些人的学问并没留下来,只是过眼云烟。为什么政府奖励的学术留不下来,因为留下来的都是同行、同道严格评议的产物,而政府扶持的东西很难通过这样的考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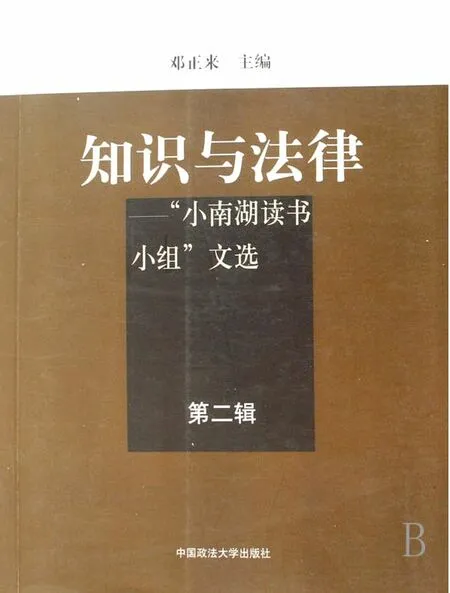
邓正来教授认为,在大学里,读书就是大学生必须守住的最大本分
三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体系学术传统的重建运动。中国社会科学是舶来品,目前教科书般的照搬,进步意义在于普及,平面上的一种拓展,但缺乏纵深的推进,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诸位,未来的世界是你们的,千万不要为高分而高兴,高分等于零,对于认识、了解乃至改变这个世界没任何帮助。我们每一个读书人都有一个天然的使命,维护和建构祖国的学术传统、知识传统,在此基础上将新的学术生产和再生产进行下去。

2008年邓正来加盟复旦大学,创办了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我的教学方法
我有两类学生,一是通过考试报到门下的。还有一类是私塾弟子,从本科生到博导都有。
我给学生上三门课。第一门叫《原典精读》,读西方原典、原著。课堂上不准交头接耳,不准商量,可以查字典,只有这样你才知道自己真正不懂的地方在哪里。
我上课什么学生都可以来听,有老师好心劝我不能这样,应该点名。我问为什么?言道,如果下学期才上你的课的学生现在都旁听过了,怎么办?诸位明白此公的意思了吧?这就是我们目前大学教学中的一大问题,很多老学究们今年是这些内容,明年还是这些内容,一本发黄的讲义十年不变。
我这门课要求他们一句一句地阐释原意,第二个同学如果不同意可提出见解,如果同意则继续进行,最后由我点评。这门课不是翻译课,但它训练的是一种品格,一种“一个字都不能混”的品格。inasense,在某种意义上,邓正来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我们必须搞清楚这些文字上的细节。
读原典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分析大师是如何提出他的问题、如何明确化地展开他的研究思路、如何得出他的结论的。总之是大师的知识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我们要掌握这个过程。
第二门课叫《大师思想讨论课》。我要求一个学生只研究一个人的思想,三年硕士、四年博士,都做一个人,把他搞清楚,大师是怎样生产知识的。
这个课的目的何在?我是要启示学生,每个大师的思想都不是孤立的,绝非自说自话,学术、学科之间并不是一个个孤岛,而是存在紧密的勾连,有脉络、有层次、有体系。我要让学生从小、从一进校门开始,就站在高山上,在巨人的肩膀上向前看,在前人的辉煌成就基础上成长自己的思想。没有这样的传承与了解,进行无知者无畏的评判,那是毫无意义的。
第三门课叫《小南湖读书小组》。我带他们读知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哲学。为什么这样安排?同学们,你们这一代法学学生太可怜了,你们的知识基础太窄了。
学校里教很多课,有一样却不教,对于知识生产机器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反思和批判的学问,也就是知识社会学。这非常可悲。这门课,每次一个主报告人,其余人参加讨论和提问。
大学正是读书时
大学是什么?大学是university。University是什么?University是研究和关心universal的地方。大学不是旅馆、不是酒店,不是让你如过客一般来去匆匆,不带走一片云彩。你们是将人生中最华彩、绚烂的四年时间、三年时间停驻在这里,来关心和思考那些普世性的问题和人类之命运的。老师教不好是老师的原因,学校管不好是学校的原因,但你们自身首先也要有一个自省和反思,你们自己也必须意识到自己的这种责任和担当。
我要求学生有两条,必须学会生活、有一个好的身体,必须学会做学问、有一个好的头脑,而这两者其实是完全并行不悖融为一体的。
我的学生中也自发组建了一个“散步学派”。我要求每月至少散步两次,后来我建议边聊天边散步,每次就聊《论语》一句。我觉得中国人近年来不断地反文化保守主义,最后反得连自己的文化底蕴也不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被逐渐鄙夷和流失,这是你们这代人的悲哀。(有大量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