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高处的小女孩
许福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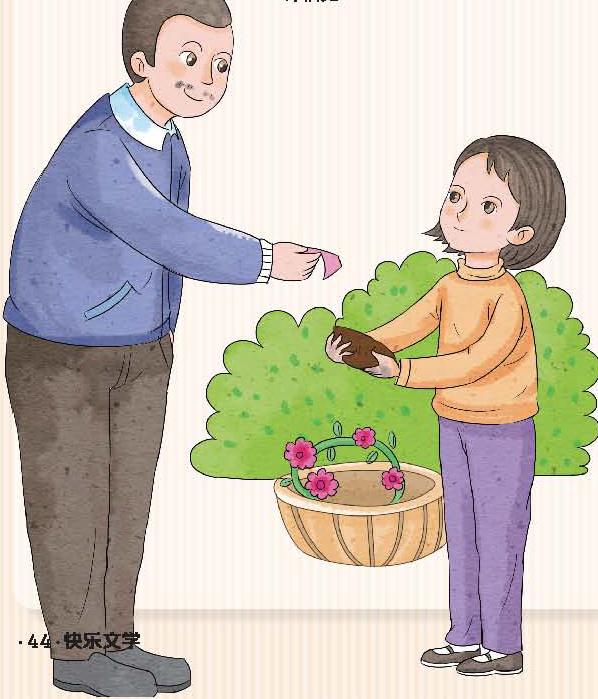
在蒙蒙细雨中,婺源的油菜花开得漫山遍野。黄灿灿的梯田,如一幅幅被游人抖开的巨大横幅,一级级由山脚传递到山顶白云缭绕处。黄花把山野挤爆了,人流又把黄花挤爆了。
我手举雨伞,小心注意脚下湿漉漉的青石,拾级而上。赏花的人们兴致很浓,将弯弯曲曲的石径挤成布满蘑菇花伞的人流。
雨势稍停,人们将伞收起。你会惊奇地发现,很多年轻的女士们,头戴着油菜鲜花编织的花环。从高处望下去,条条山路上蜿蜒地涌动着头戴花环的人流。
山路两侧,有帐篷或临建小屋卖小饼烤薯。阿嫂阿婆们,臂弯套着一串一串的花环,热情地探身拦着过往游人兜售花环:“花环,鲜花环,嫩花环,十元一个。”
花环编织得并不细致,却很别致。青青的柔软嫩茎缠绕拧绑成一圈儿,一朵朵小花开放着四片花瓣。有的米黄,有的柳黄,有的鹅黄,还间杂着火焰红、春水绿和彩虹蓝。一株一株的伞状小花,看上去并不起眼,但排成阵势,几百亩上千亩铺陈开去,那满目黄花足以让你叹为观止。花环虽小,却蕴含丰富,光彩映人,花香拂面还引来嗡嗡蜜蜂。人面花环,相衬生辉。
快到山顶的时候,我有点饿了。眼睛寻过去,前边路旁拐角一块黑色山石上,有一个孤零零的小姑娘在张望,她似乎在卖什么吃食。我走上前去。
这个小姑娘确实小,也就八九岁的样子。一绺枯黄湿发黏贴在她的小脸庞上,眼睛黑而大。她面前放着一只古董般的木笼,底部是黑灰的木炭,却看不到火色,上层放着灰黑的红薯。旁边有一个竹篮,上面有几块红薯和一个花环。她用一块不大的塑料布來遮挡木笼,以致雨水打湿了她的瘦肩头和窄额头。
我指着笼上的一块红薯问:“多少钱一块?”
“五块钱。” 小姑娘怯生生地伸出五根手指。她的手指黝黑,手背粗糙,那是常做农活的证明。
“可山脚下是四块钱。”我故意说。导游说过,旅游景区是可以砍价的地方。
“您给四块也成。”她态度很诚恳。
于是,我掏出一张五元票递给她。小姑娘用双手捧上一块红薯,然后从衣兜里掏出一张一元票,也用双手捧上。
我慌了,忙说:“逗你玩呢!你要十块我也会给的。”
小姑娘见我不要,又将那一元钱很郑重地放回去,仰起脸大声说:“谢谢叔叔!”一脸地感激。
这一声“谢谢”谢得我心酸,这一声“叔叔”叫得我心虚。我向山下望去,山脚的房子只比火柴盒大些,人流也影影绰绰。我身边这个小人儿,定是天麻麻亮就起身,背着木笼,挎着红薯篮子,披着塑料布,冒着细雨,吃力地一步步登上湿漉漉的石阶,攀登到高处,为的就是每块红薯多卖一块钱。一块钱,在这小姑娘心中是如此重要。
山顶毕竟游人少一些,也冷清一些。我和她攀谈起来:“你挣的钱干什么用?”
“上学。”
“你上几年级了?”
“我没上学,供我哥哥上学。”
“你哥哥几年级?”
“我哥哥也没上学,钱攒够了再上学。”
“你今年几岁?” 我心里顿时发紧,猜想她的实际年龄。
“我十岁,我哥哥十二岁。” 小姑娘说得很坦然。
我立刻想起我的小外孙女糖糖,她今年六岁,上幼儿园大班,到九月份,该就近上小学一年级了。于是我问:“你哥要是上学,学校一定很远吧?”
“也不远。您看,就在那白云升起的地方。”
我顺着她的手指望过去,云深不知处。
我指着遍地黄花:“小姑娘,你看,那么多游人都头戴花环,那么多阿婆编花环卖花环。你也可以采摘编了卖钱呀,花期这么短,可别错过呀。”
“不。”小姑娘口里只吐出一个字,却很坚决,脸上的表情很严肃,显得心思重重。
“为什么?”我有些不解。
这时,她从竹篮里拿起一个花环,显然是被人戴过遗弃的。花朵已萎谢,叶子已萎蔫,嫩梗已萎缩。她脸泛红,将花环举到我眼前,说道:“把鲜活的菜花折了,还能结籽吗?花越好看,就越该折吗?花不会喊疼,可是会流泪的。你们大人这是怎么了?” 她用粗手背抹抹眼睛。
油菜花环,浸出绿色微红的汁液,那就是花的泪水。如果尝一尝,定然是苦涩的。
是的。人们将美丽葱翠的花环戴在头上照相留念,将一瞬变成永恒。随后弃之,踩在脚下。我看到多少花环被投进垃圾箱,以为本是菜花应有的下场与归宿。只有我眼前这个卖红薯的小姑娘,能听到油菜花环在哭泣,她触摸到了油菜花的疼痛。
我无言以对。
我定了定神,对小姑娘说:“你看,雨丝又飘起来了,你又穿得这么单薄,衣服也湿了。你还有多少块红薯,我全包了,你赶紧回家吧。”
“不。”小姑娘又只说出一个字,仍很坚决,脸上的表情仍然严肃。
“为什么?”我依然不解。
“您是不饿了,可有人饿了咋办?我不能将红薯卖给一个不饿的人。我妈说过,饭给饥人。”
“饭给饥人。”这四个字,让我心头一震。
这时,我的小外孙女糖糖跑过来,连连嚷着:“我饿了,我饿了。”
炭火已灭,温热不再。红薯是有的,但是凉的。这时,小姑娘从怀中掏出一个塑料包,层层打开,是一块红薯。她双手捧起,睫毛闪动着:“小妹,给!”
这块红薯,带着小姑娘的体温与温情。
下山的时候,糖糖频频回头,问:“小姐姐呢?”
我指向那澄澈光亮的地方,那里有站在高处的小女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