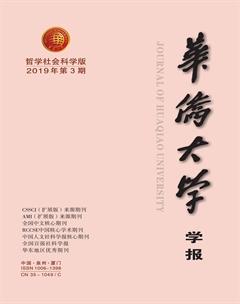流域综合管理法治的历史逻辑与现实启示
摘 要:
从分散立法到综合立法,从行政区域管理到流域共同体治理,从一般性司法到司法专门化的发展反映出流域综合管理法治演进的基本规律。就我国而言,推进流域综合管理法治建设需要在立法、执法、司法等方面着力。在立法层面,克服功能性立法、部门立法弊端应制定“水基本法”,涵盖地表水、地下水、过渡性水域、沿海水域等水体,统合水资源开发利用、环境保护、防洪防汛、灌溉航运等功能要求;在管理层面,应以流域为单元设置管理机构,下设流域委员会和流域管理局,并鼓励公众实质性参与;在司法层面,化解跨行政区域水事纠纷应在行政裁决机制基础上增设司法处置路径,省域内水纠纷案件选择省会城市或者流经地级市中院进行集中管辖,跨省际水纠纷案件则应发挥海事法院跨区域管辖优势实行专门管辖。
关键词:流域综合管理;综合立法;流域共同体;司法专门化
作者简介:李奇伟,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环境与资源保护法(E-mail:87133631@qq.com;湖南 长沙 41008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区域环境保护府际协作法律机制研究”( 16BFX135);湖南省法学会研究课题“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研究”(18HNFX-D-006);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洞庭湖湿地生态保护补偿法律制度研究”(18A004)
中图分类号:D922.2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9)03-0092-10
流域综合管理(Integrated Watershed Management)是指为实现流域可持续发展,以整个流域为单位,在政府、企业、公众共同参与下采取经济、技术、行政等多种手段对流域生态系统内诸要素实施的系统管理。经过若干年的发展,流域综合管理理念逐渐为人们所接受,成为“以公平方式在保证重要生态系统可持续性不受损前提下,协调开发管理水、土等流域资源”庞靖鹏、张旺、王海锋:《对流域综合管理和水资源综合管理概念的探讨》,《中国水利》2009年第15期,第21—23页。的重要措施。实施流域综合管理不仅需要经济技术手段的进步、政策资金的投入,亦需要在法治基础上明确主体权义、规范主体行为,使整个综合管理过程循法而治。从国外情况看,从1884年奥地利制定实施世界第一部《荒溪治理法》,到开启流域统一开发管理先河的1933年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法》,再到日本《河川法》、德国《水平衡管理法》和大量国际流域协定都表明,流域综合管理法治是实现流域善治的制度基础。基于此,本文将围绕流域综合管理法治展开,从历时性视角铺陈分析流域综合管理法治的发展演进历程、基本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改进和完善
我国流域综合管理法治的具体建议。
一 流域综合管理法治的发展演进历程
从发展历程看,流域综合管理法治经历了从无序到有序、从侧重综合开发利用到生态优先、从注重行政管制到公共治理的嬗变过程。根据不同时期流域综合管理法治的发展特征和侧重点,可以将其界分为:水资源综合开发利用阶段、水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阶段、流域治理一体化阶段,分别对應着不同的规制目标、管理体制与法治措施,从历时性的视角呈现了流域综合管理法治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演进过程。
(一)20世纪中叶以前:水资源综合利用管理法治的提出
在20世纪中叶以前,人类对待流域的态度以资源利用主义为主。那一时期的主导思想是征服河川径流、对水资源进行开发、使水资源为人类所用。就像英国首相丘吉尔所设想的那样:“让河流尽其荣耀奉献全部,不让一滴水流入大海”。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现代技术,如混凝土、蒸汽机、电力、挖掘机等的使用强力塑造了山川河流,高坝使得人们可以“征服自然”、控制洪水、航运、发电和灌溉土地,长距离的电力输送能够将水力发电产生的大量电力供给远距离用户使用。可以说,工业化开掘出流域的多功能价值,创造了新的社会需求,反过来,“流域开发被证实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和本质要求”Franois Molle. River—basin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The social life of a concept. Geoforum,2009,(40),pp.484-494.。在流域开发与区域经济发展互动之下,如何系统的运用河流经济潜力、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水资源成为那一时期流域治理面临的现实问题。
从法治层面看,化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依法实施水资源综合开发管理,统合流域管理机构、明确主体权利与义务、规范流域开发活动,以实现全流域的梯级开发、水工程的统一布局和供水、防洪、航运、灌溉、水电功能的融合。1884年,奥地利颁布《荒溪治理法》,该法是世界上最早关于小流域综合治理的法律文件;1896年,日本通过流域管理基本法《河川法》;1921年,法国设立流域管理机构CNR,为超出流域范围之外的巴黎提供电力;1926年,西班牙制定政策要求在重点流域逐步建立准自治的流域管理机构,并将其目标定位于“制定一个综合的、协调的、系统的规划以实现流域内水资源的高效利用”李原园、马超德:《国外流域综合规划技术》,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9年,第3—10页。;1945年,英国制定《水法》,规定47个集水区域管理机构应该为各个河流管理委员会所替代。
当然,在这一阶段水资源综合利用管理法治的突出成就是美国于1933年制定的《田纳西流域法案》以及据此建立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TVA)。在罗斯福看来,这是“一项将多个州纳入田纳西河流域的土地利用实验,是一项规模尺度上史无前例的区域规划项目”,“设想中的大型规划‘不但为我们自己制定,还要考虑下一代,要将工业、农业、林业、防洪统筹考虑,要把所有因素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李原园、马超德:《国外流域综合规划技术》,第3—10页。。在流域综合开发理念指引下,《田纳西流域法案》授权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拥有征用土地、水坝建设、出售出租不动产、生产销售化肥等广泛权力,并通过统筹防洪、航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有力促进了田纳西流域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20世纪60—80年代中期:水资源保护法律规范的融入
在20世纪50—60年代,水资源开发利用热潮达到了顶峰。随之而来的,是与过度开发相伴而生的严重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1962年,蕾切尔·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1966年鲍尔丁发表《未来飞船地球之经济学》,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布《增长的极限》报告以及同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成为呼吁生态环境保护的先声,环保思潮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种潮流。在人们环保意识觉醒之下,当看到身边的河流污染问题,如水俣病、骨痛病等水污染事件,整个社会开始反思过去不合理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方式,思考如何在开展持续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同时维持良好的生态环境。
在这种情况下,水资源综合管理法治开始积极转向,水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成为立法的重要内容,流域机构管理职责也开始从开发利用转向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并重。从美国情况看,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制定了一系列环境保护立法,包括:1963年《清洁空气法》(the Clean Air Act);1965年《水资源规划法》(Water Resources Planning Act)、《固体废物防治法》(Solid Waste Disposal Control Act);1967《空气质量法》(the Air Quality Act);1969年《国家环境政策法》(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1972年《水污染防治法》(Federal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Act);1976年《资源保护与恢复法案》(Resource Recovery and Conservation Act)等,李奇伟:《城市污染场地治理法律制度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年,第21页。为流域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提供了法律保障。其中,1965年《水资源规划法》设立了美国水资源委员会和6个流域管理委员会,并要求以区域经济发展、生态环境质量和社会福利为目标进行水土资源综合规划。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在这一阶段也通过控制火电厂建设、推进核电站项目、修建固体废弃物管理示范工程、恢复森林植被等措施进行流域污染治理,逐步改善了水生态环境。
欧洲国家和日本的情况也大体相似。1964年,日本对《河川法》进行大幅修订,将河川环境整治与防洪、水利开发一起列入立法目的,1964年日本《河川法》第一条规定:“为防止河川发生洪水和高水位灾害,合理利用河川资源,实施河川综合管理,使河川保持正常功能,并兼顾河川环境整体整治与保育,达成有助于国土保全与开发、保障公众安全、提高公众社会福利之目的,特制定本法。”并且将河川以一定标准进行分级,实施以水系为单元的综合管理;1964年,法国颁布《水法》,在突出水污染环境治理目标的同时,按照水系设立了六大流域委员会和流域水资源管理局,以统一规划和管理流域资源;1973年,英国议会通过《水法》,成立了泰晤士河水务管理局。之后又大幅改革流域管理机构,将英格兰和威尔士原有的29个河流管理局和157个地方管理局合并为10个,对流域内的水利资源开发、防洪、航运、水污染防治等各项事务实行统一管理。上述举措反映出这一阶段流域综合管理法治对环境问题的关注,通过立法和机构整合进一步强化了作为整体性治理单元的流域的重要性。也应该看到,这一阶段的主要措施是“通过处理点源污染来解决污染问题,对环境恶化的响应主要停留在国家层面上,由专家或机构来推动”李原园、马超德:《国外流域综合规划技术》, 2009年,第3—10页。,而未提供一个多层次系统解决方案,这就为流域综合管理法治的进一步发展预留了空间。
(三)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流域综合管理法治的确立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及深入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及生态系统理论契合的流域一体化治理逐渐成为流域综合管理的发展方向。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指出:“应对水资源实施综合规划和管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二十一世纪议程》,1992年6月14日。这种综合应既考虑水质又考虑水量,并涵盖地表水和地下水等各种类型的水体。1993年,世界银行《水资源管理文件》中强调,水资源管理由机构框架(法律、规制和组织的作用)、管理工具(命令控制和金融财政手段)以及基础设施的发展、维修和运转等要素组成。水资源管理应建立在都柏林三原则(the Dublin Principles)基础上,即生态原则、机构原则和工具原则。Solanes M, Gonzalez—Villarreal F. The Dublin principles for water as reflected in a comparative assessment of institutional and legal arrangements for integrate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Stockholm: Global Water Partnership, 1999,p.6.之后,2000年召開的“第十届水大会”把流域资源一体化管理作为四大议题之一。201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给予所有人水和保持良好环境卫生并实施可持续管理”列入可持续发展目标,并提出包括保障饮用水、享有环境卫生、进行水资源综合管理在内的6个具体任务。
在流域一体化治理理念影响和指导下,各国流域管理法治逐渐向可持续的流域生态系统整体法治方向转变。一方面,流域综合管理法治将其调整对象从单纯的水质水量扩展到整个流域生态系统,“将江河、湿地以及与流域有关的各个区域综合起来进行考虑,推动流域整体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陈进:《长江流域综合管理模式探讨》,《人民长江》2013年第10期,第116—120页。20世纪90年代,美国提出整合性流域管理策略,基于生态系统概念对地下水、地表水、湿地、空气等进行统筹规划和保护。2000年,欧盟《水框架指令》规定:“在考虑欧盟现行有关规定基础上,各成员国应实施综合管理规划以保证水体能够达到良好目标。”2009年,德国《水平衡管理法》指出,该法的立法目的在于“基于水体可持续性进行管理,保护人类、其他生物赖以生存的空间。”另一方面,过去为人所忽视的一些问题,如地下水的过度开发、污染物的扩散、部门之间的竞争、水的非消耗性利用、利益相关者诉求等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李原园、马超德:《国外流域综合规划技术》, 2009年,第3—10页。特别是在公众参与方面,决策者不再局限于单极化的行政部门或者只依赖专家知识予以解决,而是逐步构建起政府、企业、公众互动交流平台,使综合利用与保护决策更加合理。
二 流域综合管理法治发展的基本逻辑
流域综合管理法治从侧重“综合开发利用”到“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并重”再到“流域一体化治理”的转换,大体上描述了流域综合管理法治的发展演进历程。虽然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各自独特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环境差异可能呈现出不同的样式或者跨越其中某一阶段,但通过对流域综合管理法治演进历程的梳理,可以抽象出流域综合管理法治发展的基本规律。
(一)在立法形式上,从分散立法到综合立法
流域综合管理对涉水法治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要调节水量、水质,也要关注整个流域生态系统平衡;不仅要调整地表淡水,也要规范地下水体,甚至流域范围内的湿地、沿海水域等;不仅要注重水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也要考虑防洪防汛、水土流失、灌溉、航运等流域综合功能。这也意味着面对流域综合管理要求,现代水法体系应对此作出革新性的调整和回应,打破传统单一化、分散型的水事立法状况。具体来看,从分散立法到综合立法呈现出两种典型形态:
第一种形态是特定流域管理法。例如,美国《田纳西流域法案》《下科罗拉多河管理法》,日本《琵琶湖综合开发特别措施法》,西班牙《塔霍一赛古拉河联合用水法》等。通过“一河一策”立法加强法制针对性,并将涉及该流域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规范综合性的予以规定;
第二种形态是水基本法。主要在欧盟国家内推动,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欧盟陆续制定了一系列与水相关的指令,欧盟一系列与水相关的指令主要包括:《洗浴用水指令》(76/160/EEC)、《饮用水指令》(98/83/EC)、《城市污水处理指令》(91/271/ EEC)、《下水道淤泥指令》(86/278/EEC)、《硝酸盐指令》(91/676/EEC)、《栖息地指令》(92/43/EEC)等。涉及水量分配、水质保护、栖息地保护等多个方面。从政策执行效果看,一方面,指令与指令间立法目的、调整对象不同,难免出现不协调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情况;另一方面,單个指令对行为的规制只涉及某个方面,而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离不开政策的统合。例如,1991年《城市污染处理指令》通过严格的排污许可证和排污收费制度规范了企业的排污行为,却无法规制农业废水和城镇生活用水排放。如此一来,流域内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好转,从而影响了政策执行效果。在这种情况下,2000年欧盟通过废除7个指令并将30多个补丁型欧盟水法规整合,形成了《水框架指令》,为欧洲范围内所有水域的可持续规划管理提供了共通方法。[英]马丁·格里菲斯:《欧盟水框架指令手册》,水利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交流中心译,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8年,第4页。该指令的立法目的着眼于水生态系统整体的保护和改善,其适用范围扩展至所有水体,包括内陆地表水、过渡性水域、沿海水域和地下水等,成为促进欧盟成员国水法革新的重要推动力量。在欧盟成员国中,德国于2009、2011、2013年数次对《水平衡管理法》进行修订,将适用范围扩大到地表水体、沿海水体、地下水。荷兰则于2008年将《水管理法》《地下水法》《地表水污染防治法》《防洪法》《海水污染法》《土地围垦与滩涂法》《公共工程管理法》等八项与流域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整合为一部法律——《水法》,实现了对境内流域生态系统的全方位法律保护。
(二)在执法体制方面,从行政区域管理到流域共同体治理
“为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并为社会创造最大福利价值,关键在于建构合理的政策法规框架,并依据这些政策法规构建有效率的流域管理机构,使相关管理决策能顺利实施。”[德]L.S.安德森、M.格里菲斯:《欧盟水框架指令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席嘉瑨、孙远编译,《水利水电快报》2009年第9期,第78—94页。这就要求流域综合管理法治在执法体制规定上作出修正,从原来相互分割的行政区域管理体制转变为以流域为单位的流域共同体治理体制,在每个流域区设置适当的行政安排,并积极吸纳企业和公众的共同参与。具体来看,流域共同体治理,特别是流域整体性管理机构设置主要存在以下两种形态:
第一种形态是法定型流域管理机构。法定型流域管理机构依法设立,其组织定位、基本职权、运行方式等都由法律明文规定,因此,其职权范围较清晰,管理活动都处在法律规范之中。当然,根据授权程度不同,法定型流域管理机构也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田纳西流域管理局为代表的充分授权型。众所周知,田纳西流域管理局依据1933年《田纳西流域法案》设立,其性质属于联邦政府行政管理机构,拥有从征用土地、经济开发到环境保护的广泛权力,类似于管理田纳西流域各项事务的“特区政府”;另一种是法国、荷兰、西班牙等国家设置的不充分授权型流域管理机构。这些机构也是依法成立,但管理权力有限,其对流域的管理需要结合其他实体机构展开。例如,西班牙《水法》规定,跨区域流域机构——水文联合会的职责是“编制流域管理规划并负责监督和评估规划;公共水资源的管理和监督;共同利益或影响一个以上自治区的用水管理与监督;流域机构承担和自己投资的工程的规划、建设和利用”水利部国际合作与科技司、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西班牙的水》,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7年,第42页。等;法国《水法》规定,水管理机构由国家、流域和地方三级构成。流域一级又设置流域委员会和流域水资源管理局,不同层级的流域管理机构需要相互配合才能较好的实施监管,其管理权限远小于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
第二种形态是协定型流域管理机构。协定型流域管理机构依据合作协议确定机构设置,规定机构权限,在跨区域甚至国际流域管理中起着重要作用。例如,澳大利亚墨累—达令流域横跨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南澳大利亚等多个州,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指引下,这些州通过平等协商于1914年签署了墨累河水协议,1987年、1993年又对此协议进行了修订,最终形成了流域部级理事会、流域委员会、社区咨询委员会等管理机构;莱茵河则流经欧洲的法国、荷兰、德国、卢森堡等9个国家,从1815年起,这些国家陆续签订了39个协定确立了莱茵河国际治理框架,1950年保护莱茵河国际委员会成立,对于莱茵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德]J.F.栋泽尔:《欧盟水框架指令下法国水资源管理的创新》,李慧、孙远编译,《水利水电快报》2009年第9期,第41—46页。
(三)在司法保障方面,从一般性司法到司法专门化
为了适应流域综合管理要求,除了立法和执法方面的变化,在流域司法层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对跨行政区域水纠纷进行处理或者对涉水事务实施专门管辖的“水法庭”在一些国家逐步建立起来。
前一种情形以印度最为典型。1956年,印度制定《邦际水纠纷法》。该法规定当邦政府间发生水事纠纷且该纠纷难以协商解决时可以请求中央政府成立水事纠纷法庭,对该纠纷进行裁决。该裁决将是最终决定,对纠纷各方具有约束力。到1997年,印度共成立了5个州际水纠纷法庭,分别是克里希纳水纠纷法庭、讷尔默达河水纠纷法庭、拉维河水纠纷法庭、比亚斯河水纠纷法庭和高韦河水纠纷法庭。这5个法庭已经有4个法庭作出了裁决。例如,讷尔默达河水纠纷法庭于1969年成立,1979年12月完成最终裁定。该裁决详细规定了纳尔默达流域4个州的水资源分配方案,确定了萨达尔萨罗瓦大坝建筑高度,并指定吉吉拉特州负责水坝过程建设。[墨]比斯瓦斯:《发展中国家水总体规划》,王新才译,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 1999年,第138页。
后者则在更多国家出现,它“独立于国家民事、刑事司法体系之外,作为一种特殊法庭发挥作用。”[墨]比斯瓦斯:《发展中国家水总体规划》,王新才译,第138页。从功能上看,此种类型的“水法庭”主要起到两方面作用。一方面,作为司法审查机关接受公众对政府机构作出的有关决定的投诉。例如,1991年修订后的以色列《水法》设立了水法庭,该法庭接受对水行政长官命令、保护带划定、施工生产执照、供水费用、管制用水、配额补偿等方面决定的投诉;发展中国家如南非,在1998年依据《水法》设立了水法庭,其主要职责在于听取对权力机构所作决定提出的上诉以及因被剥夺水使用权而提出的补偿申请。公众可以就流域管理机构、水主管机构提出的水资源分配计划、用水权转让、补偿费用等事项向水法庭投诉;另一方面,作为水事许可机构发放许可证。例如,1961年,芬兰依据《水法》成立了水法庭,该法庭负责颁发水许可证、审查许可证发放后的实施情况,并对违规事件进行处理。[英]雅罗、[英]格里菲斯、[英]博文:《欧洲水质管理制度与实践手册》,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编译,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12年,第100页。1983年,瑞典设置了初级与地区两级水法庭,该法庭主要受理与水上作业、水设施和水工程许可有关的案件,强化对许可证发放、变更、撤销的监督。李集合、李军波:《环境法适用的理论、实践与欧盟经验》,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第271页。
三 对我国流域综合管理法治建设的现实启示
上述分析表明,世界范围内流域综合管理法治的发展演进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综合趋向,流域一体化治理理念正逐步融入立法、执法、司法之中,成为形塑流域法治的指导思想。就我国而言,由于面临严峻的流域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形势,加之流域环境治理仍然存在诸多体制机制问题,因此,我国也迫切需要通过加强流域综合管理法治建设,提升流域管理水平,改善流域生态环境,推动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一)基于一体化治理理念推进流域综合管理立法
从立法现状看,虽然我国已经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水事法律,包括《水土保持法》《水法》《渔业法》《水污染防治法》《防洪法》等,但也应该看到,这些立法在制定理念和体系结构上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在体系结构上,功能性立法、部门立法的印记较为明显。整个水法体系都围绕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防洪、水土保持等各项流域功能要素展开,由不同水事主管部门推进,如此一来,部门主导、分割立法使水法体系内部张力不断,弱化了其协同治理效应;另一方面,在立法理念上,整体统筹考虑、生态优先原则尚未确立。《水法》与《水污染防治法》两法并立,水资源开发与水生态环境保护被割裂开来、水量和水质调控分离,更为严重的是,在流域生态利益与经济发展利益冲突时,生态利益未被置于优先考虑地位,从而造成环保与开发关系上的错位。基于此,为了形成内在协调、规范有序的水法体系应当基于一体化治理理念推进流域综合管理立法,在立法模式、规制认识、规制理念等方面作出相应调整。
首先,在立法模式选择上,制定“水基本法”与“特定流域管理法”应并行不悖。从国外情况看,从分散立法到综合立法的转变反映了现代水法革新的方向。欧盟体系内德国、法国、荷兰等国家相继朝着制定统一性水法目标迈进,逐步实现了水法体系的整合。从我国现实立法需求看,分别从水资源的某一特性或价值出发进行分散立法,由于缺乏对流域生态系统的整体考虑显然无法起到流域综合管理效果。因此,在分散立法与统一立法模式选择上,统一立法更为合理,也更有说服力。那么,如何进行统一立法?学者们持有不同观点。一些学者支持制定“特定流域管理法”,如制定《长江保护法》《黄河保护法》等;另一些学者支持制定“流域综合管理法”,认为应将流域管理中的共性问题通过立法予以确认。吕忠梅等学者支持“特定流域管理法”的观点,曹明德、王曦等学者支持“流域综合管理法”的观点。参见吕忠梅、陈虹:《关于长江立法的思考》,《环境保护》2016年第18期,第32—38页;曹明德、黎作恒:《<黄河法>立法刍议》,《法学评论》 2005年第1期,第143—149页;王曦、胡苑:《流域立法三问》,《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年第4期,第137—139页。其实,这两种观点相互之间并不矛盾。“水基本法”作用在于为流域综合治理提供管理框架、原则,“特定流域管理法”则是对“水基本法”的实施贯彻,并可以有针对性的就具有地方特色的流域治理问题提出法治解决方案。因此,在立法模式选择上,一方面应制定“水基本法”,整合现有《水法》《防洪法》《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等的相关规范,使部门分割立法的现状得到有效解决;另一方面,也需要针对重点流域、濕地制定特定流域湿地管理法以实现重点保护。李奇伟:《从科层管理到共同体治理:长江经济带流域综合管理的模式转换与法制保障》,《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60—68页。
其次,在规制认识上,应基于流域综合体整体展开立法。流域综合管理的对象不是割裂的水质或者水量,而是基于流域生态系统的整体。“不应单从人类利益角度考虑,而应将‘水体理解为生态系统共同体成员的生存空间,对陆地、水体及沿海水域一并进行考虑。”沈百鑫:《比较法视野下的水法立法目的——我国水法与欧盟<水框架指令>及德国<水平衡管理法>》,《水利发展研究》2014年第3期,第27—35页。从立法修正内容上看,它要求新《水法》立法目的应如《欧盟水框架指令》所规定的,是为了保护“水生态系统及直接依赖于水生态系统的陆地生态系统和湿地”;基本法律范畴应是“水体”,而不是“水”“水资源”“水工程”;适用范围应扩展至包括内陆地表水、过渡性水域、沿海水域和地下水等各种水域,实现对流域生态系统要素的全覆盖。
再次,在规制理念上,应强调生态优先原则。水法的法律调整其本质是多元利益的协调与重新配置,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伴随着各种利益冲突。如何平衡政府、企业、公众的利益诉求,在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之间进行合理选择是水法调整的关键。从流域综合管理法治的发展历程看,水法正从资源利用法治转向生态环境法治,其调整重点从水资源的经济效益管理转向水生态的环境管理。这意味着,现代水法的主要目的在于促进流域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不再只是一种手段或者工具,而是与经济、社会发展一样,属于目的本身。它也要求未来我国水法制建设应该在注重多元利益协调的同时,更加侧重于对环境利益的维护,当环境保护与局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冲突时应坚持生态优位,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引下作出合理选择。
(二)以流域共同体建设为中心重构综合管理体制
从管理体制看,《水污染防治法》《防沙治沙法》的规定主要依循統一管理与分级、分部门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展开,分别由环保部门和林业部门作为统管部门;《水法》则规定了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体制,流域管理由水利部在重要江河湖泊,如长江、黄河、淮河等设立的流域水利委员会实施。总体上,上述关于流域管理体制的规定仍然呈现出部门管理与行政区划管理特征。从机构设置原则看,纵向设置主要按行政序列展开,横向设置主要依事项按照政府部门分工进行划分,并整合于对应一级政府。这样的体制设计看似机构明确、职责清晰,但恰恰违背了综合管理原则。上下级间、部门与部门间协调不够,特别是针对跨行政区域事务,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的分割使协调的制度成本增加,容易形成流域管理的碎片化、断裂局面;从专门流域管理机构设置看,黄河水利委员会、长江水利委员会等流域管理机构的设置在形式上符合基于流域单元进行管理的原则,但从实施效果看并不尽如人意。因为这些机构都隶属于水利部,在性质上属于部委派出机构,并不具备独立的管理职能,限于权限很难糅合地方政府以及其他部门形成对流域的整体管理。而且囿于派出机构定位,《水法》对这些机构的综合管理授权有限,承担水利部门具体执法的职能却较多。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机构的作用实质上只是水利部门在具体流域职能管理的延伸,很难达到整合效果。
为了能够真正实现以流域为单元进行管理,避免在跨区域事项上出现府际间隙、“九龙治水”等现象,需要在管理体制、流域管理机构设置等方面作出新的调整。
一方面,在管理体制总体安排上,应从行政区域管理转变为以流域为单位的流域共同体治理。从国外情况看,以流域为单位的综合管理无论在国际水域还是国内流域都取得了积极进展。例如,在欧盟《水框架指令》要求下,欧洲29个国家,包括27个欧盟成员国和瑞士、挪威,都已经致力于以流域为单元,采用统一目标、措施和时限对流域资源实施共同管理。[德]J.F.栋泽尔:《欧盟水框架指令下法国水资源管理的创新》,李慧、孙远译,《水利水电快报》2009年第9期,第41—46页。就我国而言,《水法》规定的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体制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达到政策预期,流域内行政区域间协作困难、部门缺乏协同仍是流域公共治理碎片化的主因。因此,在流域管理体制总体设计上,仍然需要进一步革新。这种革新反映在管理结构上,主要是确立起国家—流域管理机构—地方的新型管理关系。在国家层面,一方面设立国家河川委员会负责研究拟订国家河川可持续发展战略、审议河川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统筹协调国内水资源开发和国际合作的重大事项;另一方面,延展已有改革成果。例如,结合国务院机构改革,进一步以事权为中心展开部门整合;以“河长制”建设为契机,在落实党政领导河湖管理保护主体责任的同时,附加区域协调、部门整合功能;在流域层面,设立独立于水利部门的流域管理机构,围绕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系统保护展开各项工作;在地方层面,在同级政府指导下强化横向涉水部门整合,可以借鉴广州市的作法,设立水系建设指挥部,将水利、环保等各部门及区县负责人纳入其中,实现部门间协同。任敏:《“河长制”:一个中国政府流域治理跨部门协同的样本研究》,《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第25—31页。
另一方面,在流域专门管理机构设置上,应在每个流域或者流域群设置适当的行政安排。现有体制只在重要江河、湖泊设立了七个流域管理机构,应将这一机构建制向全国其他流域稳步铺开。从分类管理角度看,全国性重要江河、湖泊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职权范围应在《水法》中予以明确规定;其他跨省江河、湖泊管理机构的设立可以采取“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式,由国家作指导,地方政府间通过平等协商以契约形式予以确定;省内流域管理机构设立则可以由省级政府自主决定,国家层面只对流域水质进行目标责任考核;从性质上看,流域专门管理机构不应只是咨询机构而应是实质的管理机构。在其内部又可以分为流域委员会和流域管理局,前者作为决策机构,后者作为执行机构,既职责分工又相互配合;从管理事项上看,只有影响到整个流域层面的事务,如流域管理规划、水量分配、跨界水纠纷处理等才属于流域管理机构管理范围,更多的流域管理事务仍应交由具有信息优势的地方流域管理机构进行管理,形成层级互动的良性管理结构。
(三)圍绕司法专门化建设提升流域司法保障能力
在环境司法专门化建设方面,我国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截止2017年7月,全国共有18家高级人民法院、149家中级法院和128家基层法院设立了专门的环境资源审判机构。吕忠梅:《环境司法专门化:现状调查与制度重构》,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年,第13—14页。但也应该看到,我国在流域司法保障能力建设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对跨界水纠纷处置,《水法》仅规定了行政裁决制度,却没有规定诉讼解决方案;在法院管辖上,流域水事纠纷仍然按照一般纠纷由普通法院受理,并没有归口于专门的环境资源审判机构或者集中于层级较高的法院,与涉水事务集中管辖的应然要求相悖。为化解这些问题,需要围绕司法专门化建设进一步优化审判机制以提升流域司法保障能力。
首先,针对跨行政区域水纠纷,应在行政裁决机制基础上增设跨行政区域水纠纷司法处置路径。我国《水法》对跨行政区域水事纠纷处理作出了规定,形成了同级政府协商、上级政府裁决的处理方案。这意味着相关案件只能通过政府协商机制解决而不能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其后果是司法适用被排斥,应有的司法保障功能未能实现。从国外经验看,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特别是司法救济途径是化解跨界水纠纷的基本形式。例如,荷兰《水法》规定了水纠纷平等协商、行政裁定和法院判决三种形式。当发生水资源利用矛盾或者水污染事件时先由利益相关者自主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可以由水资源部作出行政裁定,对裁定不服可以要求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诉讼。陈燕、傅春:《荷兰水管理体制与水资源综合管理》,《中国水利》2004年第3期,第70—71页。就我国而言,通过适时修订立法增设司法纠纷解决途径是必要且可行的。具体的作法是,修改现行《水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在“协商不成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裁决”后补充规定“对裁定不服可以要求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诉讼”,以覆盖诉讼机制。
其次,以集中管辖为主,辅之以指定管辖推进省域内流域环境司法体制建设。从现实出发,省域内流域和跨省际流域应当区别对待。针对省域内流域,应选择省会城市或者流经地级市某一中院进行集中管辖,并在该院设置环境资源审判庭。可以借鉴海南省的做法,将省内“五大河流”归口某一地方中院环资庭实施跨区域集中管辖。例如,万泉河流域相关案件由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昌化江流域相关案件由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宁远河流域相关案件由三亚中院管辖,南渡相关案件由海口中院管辖等。除了集中管辖以外,为了避免受地方因素影响,在特殊情况下,应由省高院直接指定某一地区中院进行管辖,以解决管辖不能或者管辖争议问题。此外,还应指出的是,上述法院受理范围除了流域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案件、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以外,还应涵盖司法审查案件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再次,发挥专门法院跨区域管辖优势,推进跨省际流域环境司法体制建设。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的决策部署。但究竟如何建设尚处于摸索阶段。可能的方案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改造现有的专门法院,例如将海事法院发展成为跨行政区划法院;另一种方案是另起炉灶,新建跨行政区划法院及上诉法院。相较而言,前一种方法制度转换成本较低,不会大幅增加人员编制,而且在现有体制下能更好的与地方法院协调,应是较为合理的选择。具体海事法院的改革方案,一方面应根据《法院组织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规定海事法院所在地高级人民法院作为一审法院,同时明确十个海事法院管辖的具体流域;另一方面,扩展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在现有船舶碰撞、船舶排污案件基础上扩大到跨行政区划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案件,特别是行政案件,实现对跨行政区划案件的专门管辖。
四 结 语
流域综合管理法治已成为推动流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未来,我国流域综合管理法治建设不仅需要从制度发展逻辑中寻找规律,也需要立足于我国现实在实践中探索前进;不仅需要基于一体化治理理念推进流域综合管理立法,亦需要以流域共同体建设为中心重构综合管理体制,围绕司法专门化建设提升司法保障能力。当然,流域综合管理法治仍处在不断发展演进之中,更多的从理论到实践、从国家到地方的系列问题仍有待深入研究,这将是未来不断充实提升的方向。
Histor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of Law
in Basin Integrated Management
LI Qi-wei
Abstract: Integrated management by law is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good governance in the basin. From the diachronic angle of view, integrated management by law has experienc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to “equal stressing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o “integration management”. In addition, there are obvious comprehensive trends in legislation, law enforcement and judicature.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hat we should make the law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integrated management, reconstruct the integrated management system centered on the basin community and improve the judicial support by judicial specialization to enhance the capacity of basin governance.
Keywords: integrated management; comprehensive legislation; basin community; judicial specia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