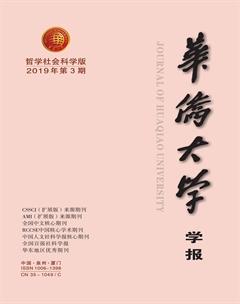传承五四传统与重建礼乐文化
摘 要:台湾三三文学集团诞生在乡土文学论战时期,一般都被定位为乡土派的对立面。实际上,他们并不反对乡土书写,只是其所指涉的乡土文学概念、内涵与主流有所区别。三三文学集团的作家传承了五四文学传统,描写了乡土社会在现代化冲击下面临的多种问题,试图透过贤德者的引领、学习科学技术、“回归民间”来解决问题。他们的重点不在批判与启蒙,而是致力于描绘天清地宁的乡土画卷,意图重建中华礼乐文化,也有着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他们吸收了中国古典叙事美学,在认同微观视域、回归传统、宗教“复魅”等方面,表现出了与台湾后乡土文学相同的特征和取向。三三文学集团的乡土书写催生了台湾后乡土文学,是台湾乡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证了中华文脉在台湾的传承与发展。
关键词:三三文学集团;乡土书写;朱西宁;五四传统;礼乐文化
作者简介:吴学峰,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无锡开放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E-mail:1252437326@qq.com;江苏 苏州 215006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华文作家的中华文化身份认同研究”(14AZD079);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三三文学集团成员小说的书写研究”(2018SJA0554)。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9)03-0046-08
台湾乡土文学的概念与内涵长期处于流变状态,至今没有很清晰客观的界定。上世纪20年代,在祖国五四新文学的影响下,台湾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乡土文学。日据时期,台湾乡土文学担负了反封建任务,还发挥着揭露和批判殖民者剥削、维护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等作用。台湾光复后,“二二八”以及白色恐怖,使得本省与大陆来台的左翼作家遭受打击和压制,台湾乡土文学进入了低潮时期。20世纪70年代,国民党一系列的“外交”挫败,在岛内激起了强烈的民族意识,让民众更加关心社会现实。台湾文坛掀起了以“回归传统、关怀现实”为主要标志的乡土文学思潮,矛头直指颓废虚无的现代主义文学,引爆了乡土文学论战。乡土文学阵营以左翼姿态,采用现实主义手法,书写底层人民的生活苦难,批判西方的经济殖民,揭露统治者的剥削,表达了民主诉求。
纵观台湾乡土文学史,可以发现追求批判与启蒙意义的乡土文学占据着主流地位,几乎掩盖了其它乡土文学类型的存在,甚至被视为是台湾乡土文学的全部。福柯认为任何一个事物或观念都是在多种“彼此相异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中产生,过程是非连续和非线性的。台湾乡土文学也不是一种文学类型的连贯发展,存在着“彼此相异的力量”的作用,有着丰富的内涵与多样的面貌。朱双一教授认为台湾当代乡土文学有四种类型,即“描写(殖民地)苦难”型、“扎根
土地”型、“田园牧歌”型与“批判、启蒙”型。朱双一:《台湾文学创作思潮简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226页。“描写(殖民地)苦难”型乡土文学主要是以描写台湾日据时期以及大陆沦陷区的苦难为主。“扎根土地”类型主要表现先民移居台湾的奋斗历程,是最具本土特色的乡土文学。“田园牧歌”型则是书写家乡风土,抒发爱乡之情的乡土文学,如外省作家的怀乡文学。“批判、启蒙”型既继承了五四新文学传统,也传承了日据时期台湾乡土文学传统,占据了乡土文学的主流地位。四种类型都是在五四新文学的影响下发生发展的,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见雏形,也见证了祖国大陆和台湾本土的乡土文学传统的融汇发展。
三三文学集团诞生于台湾乡土文学论战时期,是由胡兰成、朱西宁指导,以朱天文、朱天心、马叔礼、林慧娥、谢材俊、丁亚民等人为核心,以《三三集刊》为创作平台的一批青年作家。结合年龄和辈分划分,胡兰成、朱西宁等人可以称为“老三三”,朱天文姐妹等早期成员为“大三三”,林耀德、杨照、林俊颖则属于“小三三”。沈芳序:《三三文学集团研究》,台中:静宜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第38—39页。三三文学集团的成员以做天下国家之士为目标,立志传承中国道统,重建中华礼乐文化。他们以胡兰成为精神领袖,奉张爱玲为模仿对象,形成了独特的“张腔胡语”文风,因此文学作品常被排斥在乡土文学之外。三三文学集团的根据地是朱西宁这个台湾外省人家庭,不少成员还参与了乡土文学论战。在张诵圣、邱贵芬、庄宜文等诸多学者的论述中,三三文学集团基本被定位为外省作家群,是乡土派的对立面。事实上,三三文学集团中的萧丽红、林慧娥、谢材俊、履彊、吴念真、杨照、林俊颖等人都是本省作家,可见它是一个跨省籍、具有包容意识的文学社团,绝非“眷村第二代”“外省人”的聚合。三三文学集团也从未反对过乡土文学本身,萧丽红、履彊、吴念真还常被视为乡土文学作家。乡土书写始终是三三文学集团作家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其所指涉的乡土文学概念、内涵与主流有所区别,但都可以纳入台湾乡土文学的四种类型,也影响和推动了祖国大陆乡土文学传统在台湾的延续和发展。
一 乡土与现代的冲突
中国现代性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入侵而发生的,它带来了科学技术與民主思想,也破坏了中国传统的经济模式、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念。朱西宁受到了鲁迅、老舍、曹禺以及张爱玲等作家的影响,是在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浸润下成长起来的作家。苏玄玄:《朱西宁——精诚的文学开垦者》,《幼师文艺》,1969年9月号,第189期,第89—105页。他又从国家动荡与民族危亡时期走来,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两面性有着亲身的感触和思考,既欢迎现代文明带来的理性启蒙、科技效率,又为传统的失落而感伤焦虑。他早期的多篇小说都反映了现代性对乡村传统文明、经济的冲击,《铁浆》是其中的代表作。孟昭有舍命从沈长发手中抢下盐槽,不久火车驶入小镇,提升了货物的转运速度,传统盐槽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孟昭有没有赢得预想的家族兴旺,相反加速了家族的败亡。火车驶入乡村小镇,象征着现代文明对乡村文明的入侵,而士绅阶层的孟、沈却和普通百姓一样,想到的只有利益、鬼魂与风水。《新坟》中的能爷自己学习医术,却无缘接触现代医学,目睹亲人的悲剧一再发生。《福成白铁号》中的小老板固守传统手艺,不愿与时俱进,导致家境日益贫困。“他们和《春蚕》中因为长久依靠的赤膊船被通过官河的小火轮推入浪颠时,极其恐慌的农民是一样的害怕却无能为力;同《林家铺子》里的林老板一样,面对社会变动带来的经济危机时,只能在无助中盲目地挣扎。”方忠:《台湾当代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传统》,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101页。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文坛盛行的是怀乡文学,基本属于游子热爱家乡而美化故乡的典型追忆。朱西宁的乡土小说与怀乡小说有着明显的区别,“中国是农业国家,农村生活才是中国人的生活,在基本的态度上,乡土小说也可以说是对旧时代的一种批评和破坏,所以处理的态度上并不是出诸怀古、乡愁的情绪。我在气氛和情调上并不曾流露出依恋和一种对残缺的偏好”。苏玄玄:《朱西宁——精诚的文学开垦者》,第89—105页。朱西宁的小说取材于乡土不是要表达“怀古、乡愁的情绪”,而是带着批判的美学考量,关注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从而提升作品的美学层次与现实意义。他的乡土小说继承了五四文学写实传统,剖析了乡土社会中残留的腐朽思想,批判了愚昧国民与落后传统,他此时认同的乡土文学显然属于“批判、启蒙”型。朱西宁勾勒了在底层悲苦挣扎的小人物形象,但缺少对阶级压迫与经济剥削的义愤,没有鲁迅那样对国民性与传统文化作彻底批判,也欠缺吴组缃、艾芜、沙汀等人的革命意识,更多侧重于表现人性的暧昧与命运的无常,在批判的同时也对笔下人物给予了悲悯和包容。就整个中国文学史来看,朱西宁“上承三、四0年代的原乡视野,下接王祯和、黄春明等的本土情怀,在文学史的传承关系上,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他的乡土书写也弥补了上世纪50—70年代大陆此类乡土想象的空白,成为上世纪80年代大陆寻根文学的外来根源之一。王德威:《乡愁的困境与超越——朱西宁与司马中原的乡土小说》,《小说中国》,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12年,第279—297页。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工商业快速发展,西方资本大量涌入,对农村社会与民众生活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些是台湾乡土文学的缘起和素材,也是三三文学集团作家书写乡土无法避免的议题。三三文学集团中的谢材俊、履彊、萧丽红等本省作家,对台湾乡土受到现代文明的影响与冲击有着深切的感受,延续着朱西宁考察乡土的视角。谢材俊的《大风歌》写了父亲进城打工,最后丢下农村妻儿一去不返,折射了现代工业发展给农村家庭、传统婚姻带来的冲击。履彊的《锣鼓歌》中老榕树下铸锣为生的邓家,讲求手艺与品德并重。随着城市化的推进,邓火土不再以铸锣为生,经过多年奋斗创办了商场。儿子邓正雄后来接续了商场经理,整日唯利是图、声色犬马,导致家庭破裂,最后遭遇车祸住院,商场也突然失火化为灰烬。小说表现了在商业大潮之下,传统技艺的危机与传统道德的沦丧。《杨桃树》是履彊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叙述了吕昌平挈妇将雏从台北回老家探望父母的故事。昌平父子回到乡下恢复了活泼的本性,而来自都市的妻子淑蕙不习惯农村生活,以种种借口要提前到第二天就回台北。为了让儿子一家带回喜欢吃的新鮮杨桃,吕老夫妻趁着暮色偷偷爬树采摘。昌平发现树上树下的父母,内心非常感动;淑蕙也被公婆无声的关爱震动而深感歉疚。昌平一家长期在城市生活,从思想到言行都已经都市化,没有了原初的淳朴。这些作家描写了乡土社会在现代化冲击下存在着各种问题,但是已经与朱西宁早期的乡土书写有了内在的不同。现代与乡土的冲突仍在,但是造成人民苦难的原因不再是落后的传统与腐朽的思想,而是现代思想的“无明”。三三文学集团也提出了解决之道,即一是寄望贤德者的引领,二是学习现代文明中科学技术,三是“回归民间”解决“现代的无明”朱西宁:《回归何处与如何回归》,《日月长新花长生》,台北:皇冠出版社,1978年,第166页。。朱西宁的小说经常出现智慧老者形象,为人解疑释惑,带领人走出传统与现代纠葛的迷幛,他上世纪70年代之后的乡土书写莫不如此。《茶乡》中的崇德是个传统儒生,而又非固守陈规。他送儿子留学只是为了让他学习西方科技,至于精神之本还是要依靠中国传统文明。他支持儿媳妇良凤入学读书,接受现代文明熏陶。良凤后来兴办学校,努力为农村培养人才,成长为现代文明和传统道德兼具的完美女性。《华太平家传》中的祖父并不排斥西方现代科技,提出了“基督教中国化”和“西体中用”的观点,主张用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去诠释西方基督文明,从而重建中华礼乐文化,同时拯救“无明”的西方文明。履彊《锣鼓歌》中的邓火土辛苦创办的产业被大火烧光后,他敲起原来的锣,唱起了自己三十年前创作的风靡四方的锣鼓歌。锣是邓火土发家的本源,象征着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邓火土重新唱响锣鼓歌,意味着只有根植于本源才能获得精神动力。邓正雄抛弃传统道德,脱离精神本源,最后人财两空,折射出履彊召唤和保存传统文化的期望。萧丽红小说中的民间女性大都是重视妇德、遵守礼节的典范。《千江有水千江月》里,贞观的大舅三十年生死未卜,大妗还要奉老养幼,每日为丈夫祈祷未曾停过。二姨和母亲在丈夫去世后,都是始终为丈夫守节。母亲重视传统秩序,“她不准贞观将衣服与弟弟们的作一盆洗;男尊女卑,贞观是后来读礼记才晓得,而她的母亲也只是读了几年日本书;她是连弟弟们脱下来的鞋,都不准贞观提脚跨过去,必须绕路而行”萧丽红:《千江有水千江月》,台北:联合报社,1980年,第316页。。如同胡兰成的庶母,“她家的规矩,箱子里女子的衣裳不可放在男人衣裳的上面,男人的贵气是生在女心的喜悦”胡兰成:《今生今世》,台北:远景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9年,第98页。本文所有关于《今生今世》的文本应用皆出于此,下文中不再注释。。贞观将男尊女卑内化为价值观,自省在男友大信心绪最坏时与他拌嘴决裂,是缺少女性的包容,“愧对旧人,有负斯教”萧丽红:《千江有水千江月》,第324页。。《千江有水千江月》是依照胡兰成礼乐学说构建的女性大观园,把回归礼教作为女性消弭现代性痛苦的出路。《白水湖春梦》中,萧丽红描写了人心在现代思潮影响下的异化。比如白水湖人在政治选举诱惑下变得贪图金钱;黑猫丹追求夫妻平等,整日争吵不止;铁梦男友林允亮出国就移情别恋。铁梦通过修行佛法才忘却情伤,白水湖人依靠坚忍宽恕走出了历史阴影。小说宣扬了佛法消解现代人烦恼,以及消弭历史悲苦仇恨的功能,把民间乡土化为了佛国净土。三三文学集团作家继承了五四批判现实传统与人道主义情怀,同时也延续了许地山以宗教哲理来观照与消释俗世苦痛的手法。然而,他们既无意透析下层人物遭受压迫的根源,也没有彻底剖析传统文化,更没有指向西方资本殖民,神话了民间传统的功能,批判现实的力度逐渐弱化。面对乡土与现代的冲突,他们逐步回归民间和传统文化,或多或少带着保守主义倾向。
二 天清地宁的礼乐画卷
胡兰成的自传《今生今世》可以说是三三文学集团作家的乡土书写范本。首章《韶华胜极》把故乡胡村描绘成了一个天清地宁、人情和美的礼乐世界。胡村“夏始春余,男人在畈上,女人在楼上养二蚕,大路上及人家门庭都静静的,惟有新竹上了屋檐,鹁鸪叫,鹁鸪的声音有时就在近处,听起来只当它是在前山里叫,非常深远。灶头间被窗外的桑田所辉映,漏进来细碎的阳光”。(《今生今世》31页)他笔下的日常生活就是礼乐风景,胡村“山河浩荡,纵有诸般不如意,亦到底敞阳。但凡我家里来了客人,便邻妇亦说话含笑,帮我在檐头剥笋,母亲在厨下,煎炒之声,响连四壁,炊烟袅到庭前,亮蓝动人心,此即村落人家亦有现世的华丽。娘舅或表哥,他们乃这耕田樵採之辈,来做人客却是慷慨有礼仪,宾主之际只觉人世有这样好。”(《今生今世》20页)胡村人见到他人有庆,自己也是心生欢喜,“竟是阶级意识全无”(《今生今世》16页)。胡兰成笔下的自然与人皆好,民间无阶级矛盾和劳作之苦。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没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敌对,没有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仇恨,只有王官与王民的相知相亲,普通平民也有王气、贵气,这是源自天道的王道和礼教。他不可能看不到人间苦难,只不过故意掩盖和美化,或视为“天道无亲”,以显示自己的“浩荡”“慷慨”,进而作为辩解自己滥情和失节的理由和依托。当历史逐渐远去、仇恨日益消散,他的文学书写和礼乐学说反而渗透出奇崛的审美特质,吸引了朱西宁等三三文学集团成员的目光。
随着台湾乡土文学论战的爆发,朱西宁与胡兰成的交往也越加深入,他的乡土书写逐渐减淡了批判色彩,更多倾向日常生活的描绘,试图重建中华礼乐文化。客观来说,三三文学集团在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中扮演的是第三方的角色,就创作倾向可以定位为“自由人文主义”朱双一:《台湾文学创作思潮简史》,第309页。。朱西宁对乡土文学论战双方都给予了批判,“所谓的现代主义文艺与乡土文艺,一是太过贫贪外求,一又失之于紧缩创作世界,而过分保守”朱西宁:《中国的礼乐香火——论中国的政治文学》,《日月长新花长生》,第146页。。三三文学集团在反对现代文艺的西化倾向、强调“回归传统,关注现实”等方面,与乡土统派大体一致。乡土文学派强调阶级批判意识,书写农村的经济破败与底层民众的苦难,揭露社会黑暗与统治者剥削。三三文学集团笃信胡兰成的礼乐学说,对乡土文学派的阶级观点、取材内容与书写方式则持不同态度。马叔礼认为,“任何作品都是乡土的,只是它的土性不同,每位作家都有偏于他自己土性的倾向”,“中国农民之勤劳,是来自中国人对天地相亲和的传统,此绝非奴隶制下的奴隶可比。何况佃农在今日已经不复存在了,中国农民之勤劳、简朴乃是不视劳动、贫穷为痛苦,其对土地、粮食有一种血肉相连的情感和敬意。”马叔礼:《历史的见证:谈“根”兼论乡土文学》,《文明之剑》,台北:三三书坊,1980年,第41页。他提出了“土性”的广泛性,意在涵盖各种类型的乡土文学,以稀释乡土文学派作品的批判色彩。三三文学集团所阐释的乡土和农民太过浪漫化和理想化,曲解了农村的真实情况,但表达了对于礼乐人和的向往,也折射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凝重乡愁。
朱西宁长篇小说《茶乡》里的杭州乡间风景如诗如画,与自然环境相应的是未受现代“污染”的古朴民风和厚重传统。查氏家族以“精知简行,不敢放奢”为家训,查崇德讲求茶道,为人仁厚。儿媳妇良凤孝养公婆,任劳任怨,贤良淑德。丈夫无情无义,而她无怨无悔。江南茶乡完全是一处桃花源,就是胡兰成理想中的礼乐之邦。《华太平家传》中《新春》《春来无痕》《清明早雾》等章节名称与内容风格类似于《今生今世》的部分章节,巨细无遗地铺陈了苏北的民俗风情、农活程序,洋溢着乡间劳作的热闹与喜气,绘就了一幅清末乱世之下的岁月安稳、田园青青的乡土画卷。萧丽红的乡土小说常常出现家乡布袋港的美麗景色,以及南台湾的风俗民情。《千江有水千江月》中的经典画面是水月辉映的景象,渲染出澄澈空明的意境和深邃悠远的禅意。萧丽红还大量细致铺排了端午、七夕、冬至、除夕等节令民俗,呈现了南台湾的民间风情与中华民族悠久的礼乐文化。与自然环境、文化氛围相呼应,小说中的女性温婉恬静、勤劳尊礼,都如良凤那样顺从宽容男方,散发着圣母般的圣洁光辉。《千江有水千江月》的写作手法、表现主题与《今生今世》《华太平家传》总体类似,写尽了“台湾世家的礼俗,草地儿女的深情。我们赞美萧的乡土情怀同时,不会忘记她与三三集刊的往来,师事胡兰成学说的往事。她的‘华族情结随处可见,而她向往的礼乐情缘,温柔敦厚,恰与李昂那样的男女关系,背道而驰。”王德威:《国族论述与乡土修辞》,《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台北:麦田出版,2007年,173—174页。
朱天文姐妹被认为是外省第二代作家的代表,但她们母系家族来自本省,姐妹俩也有不少关于台湾乡土题材的小说,浸润着台湾民间礼义与乡民温暖。朱天文的《剪春萝》通过女主角的视角,叙述了外婆阮阿笋的出殡过程。外婆生前行善积德,德高望重,出殡时乡人均在路边致祭。无论是老情敌,还是关心过的疯女人阿足也前来祭拜,折射出台湾民间的丧礼文化与仁厚民风。《安安的假期》写安安与亭亭小兄妹在外婆家过暑假的见闻。寒子是个善良的疯女人,救了差点被火车撞到的亭亭。外公医治好了意外骨折的寒子,而寒子每天清晨都会在外公家大门水泥墙柱上插放一束清香扑鼻的野姜花。朱天心的《绿竹引》与《安安的假期》题材、内容基本相似。小说中的疯女人寒子两次救了童年的“我”,寒子是美好乡土的代表,构成了“我”温暖美好的回忆。对不少外省第二代来说,他们的乡土不是祖国大陆,也不是有着本然地理特色与特殊历史积淀的台湾本土,而是眷村这个具有军政色彩和封闭性的空间。朱天心的《未了》中情窦初开的眷村第二代如同宝玉、黛玉等纯情的少男少女,眷村也被点染成了无忧无虑的大观园。马叔礼的《日出东南隅》记叙了广仔、津津等外省第二代儿童时的学习、生活与友谊,侧面表现了弥漫在眷村的浓浓人情味。丁亚民《林家有女初长成》里的眷村女孩小璇有过浪漫的明星梦,最后还是平凡地嫁人,代表了眷村第二代普遍真实的人生,也浸润着他们青春梦想和感动。袁琼琼的《再生缘》塑造了一群从大陆逃亡到孤岛的普通眷村民众。他们有着生活的艰辛苦恼,也有相濡以沫的温暖回忆。消亡的眷村成了外省第二代的浪漫记忆和悠远乡愁。正如苏伟贞所说,“眷村岁月从来不曾老去,一种最刻意安排的桃花源生活,都无法达到这种境界。”苏伟贞:《眷村生活》,青夷《我从眷村来》,台北:希代书版公司,第48页。
三三文学集团的作家大多也是“张派”,但在胡兰成的影响下,他们试图以礼乐学说来解读张爱玲的小说。马叔礼认为,乡土派的小说大多缺少数千年来中国农民对大自然积累的朴实情感,而“张爱玲的《秧歌》,写金根夫妇为着劳军做年糕的事情,前夜里大吵了一顿,可是第二天做年糕时,金根揉着那一团糯米球,也会为之着迷。这种地方都隐隐地流露出中国人对过年过节情不自禁的兴奋和对粮食的传统惜爱之意,张爱玲的作品始终有着广大的中国民间背景。”马叔礼:《历史的见证:谈“根”兼论乡土文学》,《文明之剑》,台北:三三书坊,1980年,第40页。三三文学集团误读了张爱玲的小说,也故意忽略了张爱玲笔下人物的世俗精明,一厢情愿地将张氏小说纳入到胡氏体系中来,最后也导致张爱玲与朱西宁断绝了联系。三三文学集团已然对中国民间投射了礼乐乌托邦式的价值向度,“中国则是井田以来即有礼,祭礼婚礼冠礼,乡饮酒及朝聘会同宾主之礼,单是庶民皆有一套礼服,客来必市馔沽酒”,“还有四时佳节,灯市龙船,是有这样的人生繁华”。胡兰成:《山河岁月》,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7页。“中国文学随时随处可得耕耘收割采桑采莲采菱采茶乃至剜菜浣纱捣衣诸般劳动的喜气;唯也不是歌颂劳动说教劳动,才更见出是与劳动相忘的好”朱西宁:《中国人(之五)——苦与乐》,《落江前的手势﹒三三集刊第九辑》,台北:皇冠杂志社,1978年,第18页。。杨照認为三三文学集团作家的乡土书写完全拔除了对威权体制的威胁,“变成了文明的避风港,变成了都市人休憩与救赎的地方了。重点不再是应该如何解救农村、同情在农村里保守剥削的人,而成了是要都市人学习、了解农村旧事旧俗、旧情旧义可贵。‘乡土的概念,到这个地步就完全被收编了。”杨照:《从“乡土写实”到“超越写实”——八〇年代的台湾小说》,封德屏主编,《台湾文学发展现象——五十年来台湾文学研讨会论文集(二)》,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1996年,第142页。杨照的解读基本准确,但是“收编”一说未免主观片面。三三文学集团致力于描绘岁月静好、天清地宁的乡土画卷,体现了他们的中华文化信仰,以及对中华礼乐文明的自信乐观。然而,他们将中国封建社会描写成一派和乐景象,把节庆民俗想象为全部世俗生活,甚至将受苦美化为清坚贞节、人性之美,无疑掩饰和消除了人间苦难和阶级剥削,脱离了历史事实,浸染了士大夫阶层或贵族公子哥的审美趣味,有着明显的历史与思想局限性。王德威将胡兰成的礼乐美学与沈从文的“抒情考古学”都纳入中国抒情传统现代性体系。王德威:《抒情与背叛:胡兰成战争与战后的诗学政治》,《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艺术家》,台北:麦田出版,2010年,第334页。三三文学集团的乡土书写也继承了大陆乡土文学中的抒情传统,总体可以归为与沈从文乡土小说同类的“田园牧歌”型。
三 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叙事传统
不管何种形态的乡土小说,其赖以生存的依托是对风土人情的描绘。朱西宁、萧丽红的乡土小说都透着浓郁的风土人情,叙事手法上都受到了《红楼梦》的影响。朱西宁认为,中国旧小说“除了在《红楼梦》中我们可以看见中国人的生活之外,其他的说部都很缺乏。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遗憾。”苏玄玄:《朱西宁——精诚的文学开垦者》,《幼师文艺》,1969年9月号,第189期,第89—105页。《红楼梦》重视日常生活的具体展现,从而扬弃了传统小说强化戏剧性的叙事技巧。吴至青:《不断求变的朱西宁》,《书评书目》1978年第60期,第70—71页。上世纪70年代之后,朱西宁不再注重叙事和故事情节的营造,常常离题漫游开去,巨细靡遗地描绘实物实事。比如《春去也》中关于养蚕、缫丝的方法,《茶乡》中关于冲茶技巧的介绍,《华太平家传》对各种农活、年节民俗的细密铺陈。这些细节描写和知识介绍,如同人类博物志,也类似于电影的长镜头,延长和拓展了叙事时间与空间,溢满着浓郁的地域风情。民俗、饮食等描写是萧丽红小说的重要特色。《桂花巷》中婢女阿恨介绍某次菜色:“有梨炒鸡……鳝丝羹、清燉鳗……黄芽菜煨火腿、风肉……和腌的五香咸菜……精肉切的薄薄的,泡酱油,再入火烧,红镐爆,炒去血水,等微白了,取出切丝,加酱瓜、糟萝卜、蒜头、砂仁、草果、花椒、橘丝、香油,拌好盛起,加一滴醋。”萧丽红:《桂花巷》,台北:联合报社,1980年,第254页。这里的菜谱移植于袁枚的《随园食单》,也有着《红楼梦》的影子,彰显了南台湾世家的日常生活。三三文学集团作家关注微观视域,铺陈日常生活,继承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方式,也展现出恢复乡土生活本真的意图。
方言具有凸现人物的形神、传递别样情致和承传地域文化等作用。三三文学集团的祖师奶奶张爱玲和导师胡兰成对方言也情有独钟。张爱玲认为方言有“语气的神韵”张爱玲:《〈国语海上花列传〉译者识》,见韩邦庆著、张爱玲注译《海上花落﹒国语海上花列传1》,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5—16页。,常在小说中引入上海话和合肥话。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夹杂着浙江方言,给人行文奇崛之感。朱西宁《铁浆》、《狼》等小说就有不少家乡宿迁的方言。《华太平家传》更是大量应用宿迁方言书写。把兄弟们为“我父”追大美出主意,“日他的,软的不行,来硬的,不用你动手,俺几条大汉缠不倒她个丫头蚌子,给她扒个精腚光儿,俺都四下里拽著捽著,敞壳儿上她个妹子的,看她还反不反韁”朱西宁:《华太平家传》,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年,第657页。。这些土语贴合农村人的身份与性格,苏北旧日民间风情也跃然纸上。萧丽红擅长应用台湾俗谚、歌谣与方言来塑造人物形象。《桂花巷》中仆人福嫂辱骂阿悦嫂勾引自己的丈夫,林嫂在旁边火上浇油。剔红先骂林嫂“丢刀子给她们相杀”“拆材添火灼”;再以“利刀割肉痕易合,恶语伤人恨难消”劝和福嫂与阿悦嫂;后来劝福嫂“子孝父心宽,妻贤夫祸少”,不要“母鸡不关打老鹰”。剔红娴熟应用俗语劝诫,既符合民间女性的身份特点,又展现了主家的智慧。《白水湖春梦》主要用闽南语叙事,以中国传统典籍为闽南词汇作注,让叙述既体现了地方特色,又有古典雅韵之美。三三文学集团作家巧用方言俗谚,突出了乡土文学的在地“土性”,也折射了中华文化的多姿多彩。
三三文学集团的乡土书写不受现实主义的约束,能灵活应用现代主义及后现代的写作技巧。朱西宁的《旱魃》在结构上不分章节,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叙事方式,不断通过秋香的闪回记忆,让时空参差对照,突出了人物命运的悲喜跌宕。朱西宁还常常会在乡土书写中渲染一抹神秘鬼魅色彩,以更好地实现写作意图。《旱魃》中的花重生先是被冤魂缠身,幸得金长老的祈祷才得袪魅重生,死后又被村民污蔑为旱魃附尸,被扒坟曝尸才获清白,得到真正的救赎。《华太平家传》中祖父有神药“拒铁丹”,如果吃了可以抵御枪炮袭击;义和团的向日葵杆无解的坚硬无比。履彊的中篇小说《天机》以黑色幽默的手法,讲述了有才村上下如附魔般地四处寻觅彩票中奖征兆的故事。有才村最后在地震中变成废墟,村民们居然还在关注和猜测彩票的中奖玄机,让故事充满了荒诞的意味。小说《回家》则颇具魔幻色彩,王中杰肉身已经死亡,灵魂飘回老家有才村,识破了本省岳父虚伪与丑恶,体会到了外省继父的悲苦与付出。三三文学集团善用虚实相生的“复魅”手法,表现出与“批判启蒙”型乡土文学不同且独特的人文思考与价值反思。
上世纪90年代,西方“后学”在台湾开疆拓土,乡土文学有意摆脱本土化的政治绑架,孕育了迥异于以往乡土书写的“后乡土文学”。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后乡土文学在认同微观视域、回归传统、宗教“复魅”等方面,表现出了与三三文学集团乡土书写的相同特征和取向。林俊颖是“小三三”之一,他的长篇小说《我不可告人的乡愁》从写作手法到思想意涵都被划为后乡土小说的代表。小说采取双线结构,单数章节描绘了后现代都市台北的眾生相,双数章节斗镇林家从甲午战争至“二二八”的变迁,以都市人的萎缩颓靡映照林家人的饱满元气,呈现出回归乡土与召唤传统的意图,照应了朱西宁回归民间的呼唤。小说详细描写了祭拜妈祖、拜溪王水府、放水灯等台湾民间宗教与风俗,烘托出浓郁的台湾风土人情。台湾某些作家用闽南语书写小说,故意用拉丁文来代替汉字,意图切割与中华文化的血脉联系,实现“文化台独”的目的。林俊颖认为闽南语保留了汉语古音,有音必有字。他延续着萧丽红《白水湖春梦》的特色,把闽南语转化成对应的具体文字,打通了闽南语与古汉语之间的血脉,锻铸出浓郁的地方特质和古雅的文学质地。小说也有着魔幻现实主义意味,让老父灵魂重现、妈祖显灵救难,反映了民族文化与民间信仰的强大生命力。林俊颖继承和发展了三三文学集团乡土书写的叙事美学与技巧,可以说三三文学集团的乡土文学是后乡土文学的源头之一。
三三文学集团的乡土书写传承了五四新文学传统,呈现了乡土社会在现代化冲击下面临的多种问题。然而,他们逐渐淡化了现实批判色彩,对民间生活和传统文化投射了乌托邦式的价值向度,努力透过文字重建中华礼乐文化。他们的乡土书写吸收了中国古典叙事美学,融合了现代主义手法,糅入风土人情与方言土语,丰富了乡土文学的类型与内涵,也催生了台湾后乡土小说,属于台湾乡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证了中华文脉在台湾的传承与发展。
Inheritance of the May 4th Tradition and Reconstructionof Rite-music Culture
——On the nativist writing of Sansan Literature Group
WU Xue-feng
Abstract: The Sansan Literature Group was born in the period of the Taiwanese nativist literature debate, which was basically positioned as the opposite of the nativist? literature school. In fact, SanSan did not oppose nativist? writing, but the concept, connotation and mainstream of nativist literature are different from the mainstream literature. The Sansan writers inherited the May 4th literary tradition and described various problems in the local society under the impact of modernization. They tried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through the guidance of virtuous people, learn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returning to the folk”. Their focus is not on criticism and enlightenment, but on the description of peaceful and beautiful painting scrolls, with the intention of rebuilding the Chinese Rite-music culture, which also has historical and class limitations. They also absorbed the Chinese classical narrative aesthetics and showed the same characteristics and orientation as Taiwans post-nativist literature in identifying with the micro-horizon, returning to tradition and religion “re-enchantment”.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SanSans nativist literature gave birth to Taiwanese post-nativist literature, whic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aiwanese nativist literature and witnesse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in Taiwan.
Keywords: The Sansan Literature Group; the nativist writing; Zhu-Xining; Chinese culture; Rite-music 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