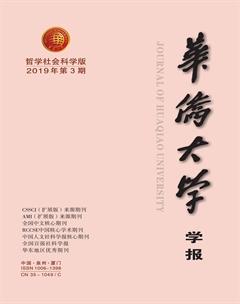追忆人心物性 抒写乡土变迁
摘 要:台湾著名作家阿盛以卓异的审美视角、讲好“乡土故事”的叙事特质和匠心独运的艺术呈现,追忆发生在台湾民间世界中的人文故事和乡土传奇,体现出他对时光流逝和社会变迁的高度敏感性。阿盛秉持中华文化的精神特质,极为重视个人家世血脉和乡土情谊。其散文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民间故事和乡野动物,汇聚了中华五四新文学的“大传统”与台湾方言写作的“小传统”,承载了多元驳杂的深刻人生体验与感悟,折射出台湾社会与文化递次嬗变的历史桑田。
关键词:阿盛;乡土变迁;人物刻画;动物摹写;传奇叙事
作者简介:倪思然,文学博士,华侨大学文学院/海外华人文学暨台港文学研究中心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台湾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理论(E-mail: nisiran@126.com;福建 泉州 362021)。
基金项目:华侨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乡土文学思潮与“五四”文学之关联研究》(14SKGC-QT05)。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9)03-0034-12
阿盛阿盛(1950—)原名楊敏盛,祖籍福建,出生于台湾台南新营乡村,毕业于东吴大学中文系。他曾任台湾《中国时报》记者、编辑、主编等职,随后曾主持“写作私淑班”,并兼任台湾师范大学人文中心的现代文学教师。自1977年起正式开始文艺创作,1978年3月1日在台湾《联合报》副刊发表了追忆童年见闻、以“厕所”折射时代变迁的散文《厕所的故事》,始受文坛同侪广泛瞩目。1981年出版首部散文集《唱起唐山谣》,20世纪90年代起兼及长篇小说创作,阿盛迄今已出版散文集《行过急水溪》《心情两纪年》《萍聚瓦窑沟》等,歌诗《台湾国风》以及长篇小说《秀才楼五更鼓》《七情林凤营》等逾二十册作品,其中多篇收入台湾高中及大学教材。与祖国大陆许多当代作家不同的是,他亦写作亦教学,亦采访亦编文集,先后编选了《台湾现代散文精选》阿盛主编:《台湾现代散文精选》,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4年初版。《故园无此声》阿盛主编:《故园无此声》,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6年初版。等二十多部,为台湾散文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阿盛的文学活动尚未引起中国大陆学界的足够重视。据笔者所掌握资料,仅有朱双一、匡琼等学者撰文专门研究参见朱双一:《乡土和庙堂文学的交融——阿盛论》,《台湾研究集刊》1995年第2期,其改写版收入朱双一著《近二十年台湾文学流脉:“战后新世代”文学论》,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匡琼:《从“文化遗迹”看阿盛散文乡村关怀》,以文本细读,深入触及阿盛散文之“诗心文心”的成果朱双一在《从文风差异谈海峡两岸台湾文学研究界的取长补短》(《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8年第1期)中,恰切地指出:当时中国大陆的台湾文学宏观研究文章,在台湾学界看来往往“缺乏真正能触及诗心文心的艺术分析”。此处仅是借用此说法,客观描述大陆的阿盛研究现状。,这就为本文提供了可开拓的学术空间。
细心的读者从“阿盛”这一具有中国南方乡土色泽的笔名,大抵可以嗅闻到他身上的家乡“泥土味”。应该说,阿盛对于其故乡土地和民间文化的浓厚情感,是其从事文学创作的重要动力来源。阿盛的人生经历,为他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出身于台南北部新营地区的穷困乡村,经历年少懵懂浪荡的求学阶段,青年时期失学当兵的吃苦经历,考上大学后到台北都市打拼的生活艰辛,一路走来,读者追随着阿盛的文笔,可以跟随着到他的童年乡村、青年澎湖与都市台北去见识他的成长,伴随着他的敏感心灵去感受台湾当代乡土世界及社会文化的递次变迁。
在《阿盛精选集》(散文集)的卷首,陈义芝写道:“阿盛是无可取代的乡土作家。在砖庭土厝的变动光影里,在民间底层人物的辛酸记忆里,他创造了一种独特韵致的‘说书风格。沧海桑田牵引的生活细节,百味杂陈的生命体会,以及烟熏斑驳的信仰,在他笔下都栩栩如生地存活。”陈义芝:《推荐阿盛》,陈义芝主编《阿盛精选集》,台北:九歌出版社,2008年,第11页。这段评价虽简明扼要地概括了阿盛散文创作的独特风格与特质,但从学术角度来看,第二、三句因“诗意”略嫌浓厚而较为抽象,却促使笔者生发问题意识。若以“五四”以降两岸新文学整体观的视野观之,阿盛的散文创作在写人状物方面有何特色?陈义芝所言“说书”风格在阿盛的散文创作中是如何呈现的?其散文作品在台湾乡土文学的流脉中,又有怎样的思想文化意蕴?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走入阿盛散文创作的世界中。
一 以独异人物折射乡土之变
早在20世纪20年代,鲁迅、彭家煌、台静农与许杰等成为了中国大陆乡土文学的代表性作家。阿盛的散文创作,与作为“五四”时期乡土文学之典范形态的“侨寓文学”颇有相似之处,即均是在离乡后具有一定的时空阻隔或位移之前提下,回望故乡、追忆故乡,并审视故乡的风物民俗和文化心理,笔端往往带有浓郁而复杂的情感。但与鲁迅、许杰等人反思、批判国民性,并“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25页。的“五四”乡土小说流脉有所不同的是,阿盛散文往往并不着重于批判或“揭出病苦”,而是紧紧抓住乡野民间人物形象最突出的特质,淋漓尽致地彰显出人性的多面向性与人物情感的丰富性,并以此映照出乡土世界的深刻变化。
读者细读阿盛的散文,能发现阿盛为读者塑造了一个“辨识度”颇高的独特人物画廊。阿盛散文中的主人公大多是他的亲人、同学及乡里具有传奇色彩之人物,他善于从当时农村生活空间中人们习焉不察的日常之中,摄取题材,以“说书人”的文化姿态娓娓道来,细致、生动地描绘那些具有时代特征的人物,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乡土叙事风格。阿盛笔下的人物,是建立在真实的生活基础上的有血有肉的人物。作者往往撷取生活的片断,通过回忆、联想和艺术综合等构思方式,来拓展自身的叙事心理空间,“讲好乡土故事”,表现他对自己所处之时代及其嬗变状况的独到感悟和体察。
《木村三郎还在》阿盛:《木村三郎还在》,原载台湾《联合报》副刊2003年9月7日,收入阿盛《民权路回头》,台北:尔雅出版社,2004年。一文,有力塑造了一个从日据时代台湾走过来的独异人物木村三郎。算辈分,木村三郎是阿盛的三表舅,而在作者笔下,木村三郎是一个相当典型的趋炎附势、以邻为壑的人物,他“实在有演戏天分”,60年代“在新营夜市卖跌打损伤丹散与补肾丸,声气极内行,吞剑、挣断铁线之类特技,全会”陈义芝主编:《阿盛精选集》,台北:九歌出版社,2008年,第29页。。而早在日据时期为了巴结殖民统治者,他积极响应“皇民化运动”,改了日本姓氏“木村”,自称是“食天皇俸禄”的日本人,仗势欺负乡亲、六亲不认,向日本人告密反抗殖民者的亲兄。在台湾光复之后,他仍以“木村”为名,“勤学北京话,花钱结交势力人”,当上铁路局车站巡视员,因对“穷乡亲”捡拾运煤车掉落之碎屑的行为严加检举,使“我”母亲吃官司。后来又“转途”为镇长、议员的选举出力,动辄密告他人,得到“长江九号”(笔者按:擅长栽赃陷害)的讽刺名号。在历次抗议活动、台湾最高领导人民选乃至战时台籍日军向日本要求赔偿的活动中,木村三郎均全程介入陈义芝主编:《阿盛精选集》,第28—32页。。作者在此惟妙惟肖地徐徐道出一个个故事,彰显木村三郎在不同时代均极其善于见风使舵、投机取巧的个性,对于权势人物谄媚依附、对于平民同胞欺压凌辱,从而突现出经历过日本殖民的台湾社会中这种戏剧性病态人格的分裂与矛盾。如果说,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的阿Q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中国农村中落后愚昧、靠着精神胜利法自我慰藉而活着的农民形象,那么木村三郎就是台湾经过日本殖民教育出来的畸形人格之奇特个案。从现实主义理论视角看,他的阅历和举止比阿Q更具传奇色彩,是异类而独特的“这一个”形象关于文艺创作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此处借鉴了恩格斯的论述:“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刘方喜等主编:《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论文艺与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66页)。。阿盛把他放在台湾时代变迁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加以刻画,呈示出该人物一切从自身私利出发,毫无原则、厚颜无耻、“墙头草随风倒”的嘴脸。值得重视的是,作者借木村三郎人心“善变”的传奇故事,折射出台湾从日据到“白色恐怖”再到“解严”,六十余年来乡亲们不变的善恶分明价值观——这显然是难能可贵的。
阿盛热爱家乡的土地与人民,受到珍视“乡土情谊”的中华文化精神有关中华文化中“重视乡土情谊”特质的源头,可参见李中华:《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华文出版社,1994年,第197—205页。熏陶。由此,他在创作中较温和地否定了木村三郎(按:毕竟是“我”的三表舅)的行为,并且还深情地描写了许多亲人形象,有祖太、祖父、叔叔、兄弟等,往往以人心之变折射时代之变。而其中的母亲形象令人印象尤为深刻。早期作品《爱的故事》阿盛:《爱的故事》,《唱起唐山谣》,台北:蓬莱出版社,1981年,第17—23页。逼肖地叙写“我”的“爸”与“妈”戏剧性冲破“女大男小”和“八字不合”等观念阻碍,幸福結合并养育七个儿女的感人故事。后来,由于父亲常年在外,混游四方,英年早逝于异乡,家庭的生活重担,自然落在了母亲身上。她日夜操劳,“为了养活一家人,不择粗细工作,没经验的工作也接下,例如捞捕虱目鱼,大清早浸在水池中,连着几日,手脚处处裂绽”,彰显母亲的勤劳持家、“务实坚忍”等宝贵而动人的品格阿盛:《流银虱目鱼》,载台湾《联合报》副刊2004年2月4日,此处参见陈义芝主编:《阿盛精选集》,九歌出版社,第41—47页。。应当说,阿盛的人生成长经历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母亲。母亲教育自己最心疼关爱的儿子做人应该要有志气,不可做惹是生非的“小太保”。在阿盛为母亲76岁生日祝寿兼谢恩的散文《心情两纪年》中,他回忆母亲一生劳碌辛苦,忘不了母亲当年对他说的话:“盛也,尔心肝软,不够奸雄,做小太保,莫使得啊”阿盛:《心情两纪年》,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3年初版,第39页。。阿盛牢记母亲的谆谆告诫,终于在读初中三年级时“改邪归正”,开始一心读书,走上人生正道。在《杨母赖氏闪事略》(笔者按:阿盛之母姓名为赖闪)中,“我”简笔勾勒母亲生平二三事,言简而意丰。“我”半生谨慎处事,坦承“学做人多过其他”,尤其是“母亲的厚道,我确实学到一些”阿盛:《杨母赖氏闪事略》,原载台湾《中国时报》2011年10月31日,此处参见阿盛:《萍聚瓦窑沟》,台北:九歌出版社,2012年,第66页。。阿盛对母亲的感恩和孺慕之情,在《心情两纪年》(1991年初版)和《萍聚瓦窑沟》(2012年初版)等散文集中,均有多篇对母子往事深情款款的讲述,可见其细腻的呈现。
在台湾当代文坛,有不少描写母亲的名篇佳构,诸如黄武忠、张春荣、琦君、林文月、林清玄等散文大家笔下的母亲。例如林文月散文《白发与脐带》,选取母亲贴身的“白发”和“脐带”两个遗物,分别象征衰老和新生的意象,成为了“我”向甫过世不久的母亲寄托哀思的重要载体,感人至深。琦君和林清玄等也都是抒写母爱的好手。正像台湾大学何寄澎教授指出的,台湾当代散文家总是以“孺慕之心情,赞颂之态度”描写母亲形象,表现母亲“集慈爱、坚毅、勇敢、勤劳、简朴等美德于一身”何寄澎:《永远的搜索:台湾散文跨世纪观省录》,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4年,第186页。的可贵品质。然而,相形之下,阿盛的母亲书写之独异处,在于看似平实、甚至略显平淡的“讲故事”文字背后,往往“不平常”地暗藏着深刻反躬自省的质朴思想。他曾发自肺腑地真诚“自剖”内心,写下了颇值得重视的“心里话”:“我曾祖(讳保)、祖(讳为)世居六甲乡,父(讳文杞)迁居新营。影响我最大的是母亲(赖氏讳闪),她过世时,我默祷她莫再出世为人,盖人生多苦。每念及她,心语难宣一二,我不孝”阿盛:《散文阿盛》(自选集),台北:希代出版社,1986年,序言。,联系上下文语境,可知这段文字的价值不仅在为吾人继续探寻和研析阿盛的家世渊源提供了线索笔者研究阿盛散文时,对作家有意识追寻家族血脉的行为产生了浓厚兴趣,进而试图探求其先祖在祖国大陆的具体活动遗迹。对此,阿盛另撰有散文《风流龙溪水》(载台湾《联合报》副刊1993年12月6日),详述自己“三进漳州老城”,返乡执着寻找“祖根”的情形。他并且写到在一处杨姓部落,因时代久远的不确定性,“不能贸然认亲”。此问题,有待笔者日后通过田野调查等方式进一步考证。,更在于阿盛借梳理自身家世脉络,怀想母亲,满心感恩,并十分恳切地道出:“我”因无法“反哺”最爱的至亲,而深感有愧于心。
阿盛在1978年初正式跻身文学界,正值台湾文坛“乡土文学论战”正酣之时。从当时乡土文学思潮的时代语境来看,阿盛散文的“说书”形式和深深扎根于乡野民间的题材,娓娓道出“由乡土文明向现代资本主义文明转型中的台湾社会中人们的生存遭际”这是台湾当代乡土文学创作的主要立足点之一,详参拙文《大陆“寻根文学”与台湾“乡土文学”比较》,《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第18—19页。,“成为乡土文学的新世代传人”朱双一:《乡土和庙堂文学的交融——阿盛论》,《台湾研究集刊》1995年第2期,第67页。。不仅如此,他的散文创作,易让读者自然而然想起台湾著名学者吕正惠称之为具有“乡土说书人”特质的作家黄春明,阿盛散文善于讲故事,长于书写农夫和乡野动物,这和黄春明的小说颇有神似之处。在当代台湾作家中,同样出身于务农世家的吕正惠“对黄春明、吴晟和阿盛特别偏爱”吕正惠:《乡下“读册人”——阿盛以及他的时代》,陈义芝主编:《阿盛精选集》,台北:九歌出版社,2008年,第13页。,这三位作家也都是出身于台湾农村,专注于用笔描写乡土的作家。而与吴晟描写乡土事物,偏重将“乡下人的牢骚、辛酸和委屈”吕正惠:《乡下“读册人”——阿盛以及他的时代》,第14页。写进诗歌、散文不同,从阿盛的散文中,读者会感受到其对人类苦难的一种发自内心底处的同情心与悲悯意识,以及对于乡土之变的淡淡忧思。阿盛散文的独特性于焉得以彰显。
“热爱土地,重视乡土情谊”可谓台湾乡土文学的一大精神内核,也是中华农耕文明孕育的“安土重迁”观念之具体表现形式此处论述,参考了朱双一:《台湾文学与中华地域文化》(厦门:鹭江出版社2008年版)第二章第二节《台湾“土地”情结的产生与传衍》的相关内容,并加以衍伸。。阿盛在早期代表作《唱起唐山謠——请为我们的祖先鼓掌》(1978年)文中,极重视民间“讲古”和世族“家谱”,深情追忆台胞历代先祖渡海开拓土地的勤劳和艰辛过程。该文“在替勤奋俭朴,乐天知命,善良淳厚的中国人绘像”赵宁:《阿盛唱起唐山谣》,阿盛《唱起唐山谣》,蓬莱出版社,1981年,序言第3页。,从而为作者后来创作奠定了扎根土地,以及回归人生、人性与人情来见证时代这两大重要基调。
阿盛笔下的庶民图像,不仅充盈着作者热爱家乡土地的情感因子,也彰显了作者的人道主义情怀。他对自己笔下人物所遭受的人生悲剧与苦难,报以深刻的同情,表达出一种植根于中华文化土壤之中的善良心性。而这种秉承中华文化“仁者爱人”特质的情怀一旦落实到文艺创作的具体过程,则与“五四”时期鲁迅力倡的“立人”精神和周作人推崇的“人的文学”主张周作人于1920年少年中国学会的讲演中,揭橥了“文学的目的是为了人生,而非为文学而文学”的观念,开一代风气之先。到了“五四时期”后段(1926年前后),由于传统文明根基已松动,各种新思想又分歧混杂,因此不少青年在新旧文化之间进退失据,鲁迅的《呐喊》《彷徨》等作品中描写的人物也或多或少带上犹疑、悲观的情感色彩。然而,鲁迅仍没有动摇其于《文化偏至论》(1908年)中提出,并且一以贯之的“首在立人”的现代性人格思想。鲁迅、周作人兄弟的文学理论对台湾新文学思潮发展,产生了颇为深远的影响。有关上述问题的研究,可参见[美]周策纵著,周子平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88—394页。颇有内在契合之处。阿盛“为人生而艺术”,发抒自己对土地的热爱和依恋,对母亲的孺慕和感恩,真诚同情穷苦出身的“乞食儿”,深切怜悯鹿港老妇的不幸遭遇。具体言之,在《状元厝里的老兵与狗》阿盛:《状元厝里的老兵与狗》,原载台湾《散文季刊》创刊号,1984年1月,收入阿盛《行过急水溪》,台北:九歌出版社,1997年。中,他讲述家乡流传很久的一个老兵的故事,老兵以买卖旧物为生,与一只老黄狗相依为命,直至最后孤零零地被埋葬。在那困苦年代里,老兵尤为坎坷而艰辛的命运令读者唏嘘,也体会到作者对于底层人物老无所依的炎凉世态的惋惜和哀愁情愫。《十殿阎君》阿盛:《十殿阎君》,原载台湾《联合报》副刊1986年3月12日,收入阿盛作品集《十殿阎君》,台北:华成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则讲述一个娼寮妓馆出身的“鹿港婆”的运命遭际,她双眼烂红半瞎,靠着在太子爷庙前弹唱月琴勉强哺养一对儿女。然而因疏于关注子女内心成长,儿子林秋田最终却成为大流氓,因杀人犯罪,被处极刑,读来令人悲戚而感喟。《故事杏仁》阿盛:《故事杏仁》,原载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88年2月20日,此处参见阿盛《心情两纪年》,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15—22页。叙写的是家乡早年一个患了“桃花癫”(按:癫狂病症之一,患者多为年轻女子)的女人,即一介无名无姓苦命的“乞食婆”,辛苦养育的儿子张福田后来考上大学,却忘本不孝,由此更衬托出杏仁的悲苦命运。这两篇散文中,时代看似在进步,人心却并未因此“进化”,甚或向着忘恩负义的“泥淖”沉沦,作者的忧愤和反思也寄寓在文本的字里行间。
阿盛勾勒的庶民图像,蕴含着他对被压迫被损害的底层人物的深切关怀,也可视作接续了日据时代赖和、杨逵、吕赫若等作家开创的,以“庶民关怀”为内核的新文学左翼传统。由此,阿盛与陈映真、黄春明、杨青矗等作家,一同体现了台湾当代乡土文学思潮关切现实、紧贴民间脉动的重要特征。
不仅如此,阿盛十分注意散文的选材角度,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往往会选择乡间的奇人异事,甚至是具有新闻价值的人物作为写作蓝本。“阿盛最大的长处是:他总会找到最恰切的细节来‘再现农村社会的生活”吕正惠:《乡下“读册人”——阿盛以及他的时代》,第15—16页。,并以他富有乡土味的文字记录加工成文,重点描绘了台湾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降生活在贫困农村的人物故事。然而,他并不是抱着“野人献曝”或猎奇的心态在叙写乡土故事的。正如台湾学者李瑞腾所说:善于讲故事的阿盛“显然有意透过说故事作为手段去诠释”台湾现代化过程“时间线上的沧桑变化”李瑞腾:《说给你们少年听——谈阿盛的散文》,阿盛《唱起唐山谣》,蓬莱出版社,1981年,第206页。。由此,我们从其自选集《阿盛精选集》中,也可清晰地看出阿盛欲借助创作活动,来试图以“追忆”和“诠释”相结合的散文美学,掌握和再现“乡土之变”的种种努力轨迹。
阿盛散文创作的选材特点,与他从小生长在台湾南部农村的自然环境与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与福建、湖南、贵州等南方地区农村相似的是,这里乡村中具有巫觋文化色彩的佛教、道教等相对迷信或保守的活动。在阿盛笔下,颇有特色地一再出现家乡流传的一些神魔传奇和谈鬼说狐的传说,而戏剧作品,也常常在演绎着天堂、地狱与人间三界的奇幻故事。加之阿盛是中文系科班出身的作家,喜爱阅读《儒林外史》《搜神记》《西游记》和《聊斋志异》等古典小说。这些文本往往长于以陌生化、艺术变形、幻事等构思方式,暗示现实人生,折射出现实世界中的反常、丑陋或病态之处。读者从其散文作品中,不难感受到阿盛善于活学活用中华传统文化之优秀因子,对于古典小说艺术能够融会贯通与灵活借鉴。尤其是阿盛的《石头罗汉传》《华年鬼故事》等散文文本对于这些民间传说的化用和古典小说手法的借鉴可谓十分精妙。这些作品富有奇幻色彩却未荒诞不经,摹写“鬼故事”却不骇人听闻,从而自“鬼性”和“人性”相互映照的独特面向,折射并彰显出了社会现实和人情人心的沧桑变迁。
二 以动物摹写承载乡土情怀
阿盛散文描写农村生活,对于“接乡土气”的家乡景物和与农人关系密切的动物尤为熟悉。寻常动物诸如猪、狗、猫、鼠与麻雀等,他均能够根据平日里的注意观察,深入认识并掌握这些动物的特征,准确地牢牢抓住动物的生活习性。并且,在独到的艺术发现基础上,活画出动物与人的求生本能的相似点,表现动物的生存智慧,新奇创譬,别具匠心,达到从形似到神似的境界。在动物描写中,阿盛既突出了台湾农村的乡土文化特征,写出了农人对土地的深厚感情,同时又承载着自身深沉的乡土情怀。
阿盛深谙田鼠的生活习性,曾对民间乡土满怀“文化自信”地写道:“田鼠不会在稻菜根处钻穴为窝”;“阡陌边角较安全,对田鼠而言”阿盛:《稻菜流年》,原载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85年4月2日,此处参见阿盛著《绿袖红尘》,台北:远景出版公司,1987年,第135页。。他并且在《天演猫狗鼠》一文中把猫、狗和老鼠这三种动物的习性放在一起比较描写:“猫的深隐阴谋强过狗,狗沉不住气,如何捕鼠?”认为“狗对人依赖、忠诚,猫对人若即若离,喜自由行动,狗像公务员,猫像江湖人。”并且视角独特、妙趣横生地写道:“狗智不下于猫”,“猫狗彼此不顺眼”,文章由动物的习性,兼而触及人性,议论人性的复杂多端,亦庄亦谐,笔锋充满智慧,进而提出人类应该“深刻观察了解动物,人会明白自己该向鼠猫狗牛马羊学点什么,以利人种进化”阿盛:《天演猫狗鼠》,原载香港《香港文学》2004年6月号,此处参见陈义芝主编《阿盛精选集》,第67—73页。。若将此文与我国唐代陈黯的《本猫说》、来鹄的《猫虎说》、陆龟蒙的《记稻鼠》等同样描写乡野动物的文章比较,则它们在以动物喻人的构思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而阿盛对于猫、狗、鼠生活习性的观察比较与描写,以及对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法则的深刻认识,则更胜一筹,也更具文化现代性的意义。
此外,《拾岁砖庭》一文细致描写乡间麻雀在砖庭啄食稻谷的机警,麻雀一边偷着啄食那晒在砖庭的谷子,一边会注意观察人的脸色。阿盛利用细节描写,逼真地“复现”现实生活的片段场景,颇有小说文笔的生动传神特质。阿盛并从中悟及:“乡间的麻雀终究跳不出田地与院庭”,“尽管稻草人愈来愈像真人,它依然看得准落脚处”。话锋一转,“可是,人呢,人在砖庭上一粒一粒捡拾稻谷,在砖庭中一点一点听闻旧事”,“人跳不出一线一线的砖隙。”阿盛:《拾岁砖庭》,原载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86年1月3日,此处参见陈义芝主编《阿盛精选集》,第107—109页。阿盛在此自然而然地采用联想与类比的艺术思维,由鸟雀思及人类,天生万物以养人,人与动物一样也是靠着天地万物的滋养而生存,而人在都市中讨生活,犹如麻雀在砖庭中啄食稻谷,该担心那捕雀的畚箕和绳子——活着不易。文末着力点题,发人深思,促人警醒。
我们再看《状元厝里的老兵与狗》,作品中,那只经常咬食物给老兵吃的黄土狗,与老兵一起栖身在破烂的状元厝里相依为命。老兵的穷困潦倒令人同情,而那只黄土狗对于主人的衷心耿耿,更是令人感慨不已。动物对于人类的帮助与情感依恋,是那么有情、纯粹而又动人。阿盛通过动物性与人性的对比,反衬出当代台湾社会剧变时期人情的浇薄与世态的炎凉。
此外,《姑爷庄四季谣》一文中,讲述的则是故乡猪哥三、议员兴、鸭母王、道士司公古等人的故事。猪哥三牵着猪哥(笔者按:闽南方言,指公猪)讨生活,走村串巷给母猪配种,其中写到猪的习性:“猪是会认人的,台湾种和红毛种都一样:人对待它好不好,它肯定记得,它通常用声音表示对人的欢迎或拒绝”阿盛:《姑爷庄四季谣》,参见阿盛著《心情两纪年》,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23页。。而描写猪仔与母猪的区别时,作者的笔触则更是在猪与人类的“来往互动”中,充满了生趣:“猪仔的眼睛也比似小孩,直直地看人,没心机的样子。母猪可不同,老岁人说,人,耳后见腮,反相,猪,下邪偷视,贱格”阿盛:《姑爷庄四季谣》,第24页。。汉语普通话、闽台方言和日语里,都有形容“人笨得跟猪一样”的骂人话语,然而阿盛的散文文本,却令读者仿佛身临其境地体会到猪的聪明伶俐的一面,体会到人与猪的性情的对比、交汇与融通,从而感受到力透纸背的艺术感染力。
在台湾当代以动物为题材的各类文本中,不乏“动物散文”“动物小说”或科普读物,以及以动物为书写文本的寓言故事等。例如,丘秀芷的《我的动物朋友》、子敏的《小方舟》与琦君的《我爱动物》等散文作品均传递出对动物的倾心、爱护和关怀;徐仁修的《动物记事》、李淳阳的《李淳阳昆虫记》和黄美秀的《黑熊手记》等文本,则结合了自然观察、动物知识与保育理念,提供了重新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开阔视野。台湾学者黄宗洁曾从动物保护的角度,总结了台湾21世纪以来各类动物书写文本与自然环境保护的关系,提醒人们进一步认识人与自然环境乃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意识,我们应当加强对于自然环境的保护黄宗洁:《当代台湾动物书写中的动保意识》,参见《思想》编辑委员会编著:《后戒严的台湾文学》,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8年,第71—106页。。然而,阿盛散文中的动物描写,与上述文本均有所区隔。它也并不是诸如老北京的侃爷那种有闲之士对于草木虫鱼的玩赏,亦不同于台湾当代作家韩韩与马以工在报导文学作品《我们只有一个地球》韩韩、马以工:《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台北:九歌出版社,1983年。有台湾文学史研究者认为,该书是台湾环保文学思潮的开山鼻祖。中那種对环保意识的呼唤,而是承载着对于乡土与故乡情谊的拳拳依恋情感,借着对于动物以及过往农事的回忆,表达自己对故乡的人和事的深切思念,以及对于乡土今夕之变的忧思情愫。从文化哲学意义上来说,阿盛散文写作中表现出来的那种乡思与乡愁,是对于内心的精神原乡的追寻,是精神还乡的一种形式。阿盛对于动物与人性的描绘和呈现,离不开对于天、地和人的类比摹写和哲理阐述,他正是从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关系变迁中,观察和表现人性的真实,追寻着人类自己的精神家园。
三 戛戛独造的艺术创作方式
阿盛在散文创作中,非常重视读者的阅读需求和审美习惯。他所创作的作品,契合了台湾当地民众的审美需求与水平。阿盛的艺术传达有其独特之处,诸如浓厚的故事性、浓郁的乡土语言、意识流手法的活用等,以此来满足读者的精神和审美需求。他笔下那些生动真实的人物故事,呈示出台湾从农业文明向资本主义工商业文明过渡时期人们的生活面貌,具备了特殊的文化认识价值与审美意蕴。
(一) 故事:通俗有趣,谐于里耳
依据现代文体学的理论,散文与小说在写作题材的处理上是有所不同的。散文写作对题材的处理往往较为自由,较少拘束,可以以作者的情感发展线索为脉络,亦可以以事件的发展时空转换为依据。而小说要求摄取一个个富于戏剧性的生活片段,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集中,形成一定的悬念和波澜,人物的对话必须性格化,力求精粹、简明、扼要,突出人物个性,从而加深人们对于人物个性和生活的认识。中国古典小说滥觞于民间“说书”艺术,在发展过程中又吸取了宋代的拟话本、话本等艺术形式的特征,颇为重视小说的故事性。一部章回体小说往往有个核心故事作骨干,围绕着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安排故事情节。阿盛早年热爱《水浒传》《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中国古典小说,他在散文创作中显然创造性地汲取了古典文学的营养,打破了散文和小说的文体界限。作为“散文说书人”,他所讲的故事往往会追求那种“谐于里耳”的叙事美学效果。在人物形象选取的乡土化、情节安排穿插的连贯性、语言文字表达的口语化等方面,他都力图做到通俗有趣,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尽量适应台湾民众的审美心理和美学趣味。
阿盛十分擅长在散文文本中生动活泼地讲述故乡的故事。在他的散文艺术宝库中,有以“厕所”为“主角”,讲述家乡农人生活习性剧烈转变的《厕所的故事》阿盛:《厕所的故事》,原载台湾《联合报》副刊1978年3月1日,收入阿盛著《行过急水溪》,台北:九歌出版社,1997年。;有回忆当年大伯卖猪竞选县议员落败,映衬出台湾政治生态乱象的《选举的故事》阿盛:《选举的故事》,载台湾《時报杂志》1980年1月号。;有为乡里奇人立传,在《石头罗汉传》阿盛:《石头罗汉传》,载台湾《台湾时报》副刊,1981年7月10日。中绘声绘影描写号称“台湾东北虎”的石头罗汉的故事。他还撰有描述家乡大宅院的人事兴衰,颇具戏剧性地巧妙呈示“人的鬼性、鬼的人性”的《华年鬼故事》阿盛:《华年鬼故事》,原载台湾《联合文学》2004年2月号,收入陈义芝主编《阿盛精选集》,第48—56页。;乃至追忆当年在澎湖当兵,描写艰辛困苦军营生活的《咸风故事》阿盛:《咸风故事》,原载台湾《联合报》副刊1985年7月24日,此处据阿盛著《绿袖红尘》,台北:远景出版公司,1987年,第205—211页。等等。
台湾学者黄雅莉认为:阿盛笔下的多种“故乡风景”“其实就是一种文化心理背景,一种植根于心中的审美意蕴”黄雅莉:《今昔对比的时空流转:阿盛〈萍聚瓦窑沟〉日常叙写的存史意义》,载台北《台湾学志》第9期,2014年,第134页。,可谓言之有理,然而在笔者看来,此论仍有进一步阐发的空间。阿盛既借鉴了中华民间传统的“说书”艺术形式,又别具匠心地对作为“故乡风景”要素的民间故事进行剪裁构思,在题材处理和叙事安排上颇似小说。虽然写的是岁月流转,湮没在历史“溪流”中的故乡的人物事件,由于他善于剪裁安排,追忆人情物事,十分注重故事的趣味性、人物语言的个性化、情节的曲折性,以读者所喜闻乐见的形式,调动读者的审美愉悦感受,使得作品引人入胜,可读性颇强。其实,故事性是阿盛着力追求的散文美学特质,它为散文文本开拓了较为广阔的审美阐发空间,也成为阿盛散文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 语言:方言俗语,生动活泼
与阿盛擅长讲故事的艺术形式密切相应的,是其散文中具有深厚乡土文化底蕴之语言的运用。台湾乡土文学思潮中,文学语言呈现杂语交混的样貌,特别是台湾闽南语的化入,增加了语言文字的情感表现力,衍生出更多的文学意义。这种文学叙事话语的改革与创新,由赖和肇始,在当代的小说、诗歌领域,有着不断的发展与形式上的突破。而在散文领域,阿盛是颇有实绩的一位。我们知道,“讲古”是“说书”艺术在闽台两地的独特表现形式,是中华古典的“说话”艺术与闽台地域文化结合的产物。阿盛散文《姑爷庄四季谣》里,即以闽台两地常见的“民间讲古人”“民间讲古”是福建、台湾十分常见的民间文化现象。例如泉州电视台即有《泉州讲古》,莆田电视台有《秋生讲古》,均为使用当地方言讲述本地区历史文化故事的节目,深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口吻,讲述乡里的人物“猪哥三”和“鸭母王”“歹竹出好笋”的故事,其中穿插民间戏文,以及道士“司公古”施法术为孩子“收惊”的故事,惟妙惟肖,颇为精彩阿盛:《姑爷庄四季谣》,第23—38页。。文末概括人世沧桑:“故事如谣唱,不宜拖戏棚,反正世事万般风过水流,人生四季去不回头”阿盛:《姑爷庄四季谣》,第37页。,短句与长句错落有致,具有鲜明的时间哲学色彩。我们再看《六月田水》中,作者提及的草台戏里王宝钏的唱词:“人来出世无半项,返去双手也空空,总是为着填腹肚,劳碌一生奔西东”阿盛:《六月田水》,原载台湾《联合报》副刊,1987年6月23日,此处参见陈义芝主编《阿盛精选集》,第166页。,这是典型的“闽南方言化”了的唱词。若用闽南话口语朗诵,“项”“空”和“东”均是押“ang”韵,平仄交错,读来朗朗上口。内容上化雅入俗,作者借此活画出人生在世奔波劳碌的艰辛而无奈的图景。这样的唱词既有中华戏曲文化的底蕴,又生动体现出台湾闽南语的原初源头是闽南地区,是由祖国大陆文化母体所孕育的。可以说,阿盛在他的创作中恰到好处地运用新鲜活泼的方言语法,并夹杂民间的方言俗语,是非常契合其叙述人物故事和表达思想内容的需要的。
阿盛的散文无论是作者的叙述语言,或是简洁的人物叙事与对话,都具有浓郁的中华南方地区乡村生活气息,绘声绘色,活灵活现。并且,阿盛的散文语言还常常夹杂着文言与白话、闽南土语与乡村俚语,甚至戏文唱词的化用与穿插。由此,阿盛融合产生散文语言的新形式,为散文语言注入了乡土的“活水”,恰到好处地显示出其散文艺术的独特魅力。
纵观台湾乡土文学流脉,采撷民俗、运用方言进行写作的风气并非付诸阙如,而植根于广阔民间世界的乡土文学思潮也其来有自。日据时期,台湾作家赖和、杨云萍、吴新荣、吕赫若、张文环、龙瑛宗等就注重对台湾特殊风俗民情的刻画,在文学映照台湾下层社会现实的内容上,体现出台湾知识分子浓重的乡土意识。20世纪60、70年代的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洪醒夫与杨青矗等作家,也在他们的小说中描述了一个个具有台湾地域风情的画面。这一时期的方言进入文艺创作领域之中,“一方面联结了庶民文化,一方面也重拾台湾的文学/文化传统”陈建忠、应凤凰、邱贵芬、张诵圣、刘亮雅合著:《台湾小说史论》,台北:麦田出版社,2007年,第256页。。阿盛的散文写作传承、赓续了这一思潮,并有所创新和发展。阿盛巧妙采用民间俗语方言,正如朱双一所精确评价的:“以能表现乡土的生动性又不造成语言隔阂为原则”朱双一:《近二十年台湾文学流脉:“战后新世代”文学论》,第125—126页。,颇懂得兼容雅俗、化俗入雅,合于“音义相符”的言语规则。
不仅如此,吾人若从社会语言学和文本符号学的双重视角审视,则知阿盛的散文语言是便于理解和接受的,即使不懂闽台地方方言,读者也能通过音与义相生相成、艺术效果形象生动的文本符号,捕捉其背后蕴藏着的民间文化元素。从台湾20世纪70年代以降乡土文学思潮的视野观之,阿盛作品并未像台湾1987年“解严”之后,某些所谓的“台语文学”文本那样,因滥用方音、生造表音符号而导致音义割裂、诘屈聱牙,堕入易受到读者费解、误解乃至厌弃的境地台湾倡导所谓“台语文学”的主要有吕兴昌、林央敏和方耀乾等人。其中一部分创作常将闽南方言用生造表音符号来呈现,如“的”字用“ê”取代,“欸”字用“ㄟ”标识等,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汉字作为表意文字的特性,易造成误解和隔阂。。而作为乡土文学“本土派”中颇激进的一支,这一类“台语文学”写作不仅从作者到受众均走入了“自我窄化”的误区,而且背离了“五四”时期胡适等学者所倡导,台湾光复初期由魏建功、何容等人成功实践的“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之理论主张。也正因此,阿盛的散文创作,在“五四”时期以来追求中文写作“言文合一”的“大传统”之中,又创造性地刷新了赖和、吕赫若、黄春明等一脉相传、“接地气”的方言写作“小传统”,为乡土散文闯出一条新路。
(三) 追忆:生命体验与叙事技法
阿盛不仅重视散文的故事性,重视在散文语言的运用方面进行创新,重视对外部世界的观察与创作素材的选择,而且还在加工素材的方法上下功夫,经常运用追忆的方式来构思散文,刻画人物心理,处理文化记忆。阿盛会根据人物心理活动的流动多变和心理经验的转移,在艺术形式与写作手法上有所变化和开拓,诸如时序的颠倒、空间的转换、幻觉错觉的运用、象征意味的追求,以及行动、对话与内心独白的错综交叉等等,抓住人物的心理特征精神意识来描写,加深对人物的刻画,使心理活动形象化,在时序、空间的变换处理方面,把人物潜意识里的想法突显出来,体现出一定的思想深度。例如《酒店关门我就走》一文中,阿盛运用一种多向辐射的艺术思维方式,以第三人称的旁观视角,来表现一个陷入生活困境与思想孤独境地的老男人,独自坐在一家年轻人蹦蹦跳跳的卡拉OK餐饮店里,借酒浇愁,追忆自己上班30年来的大半生涯,“几曾得意的出头?”刻画他在喧闹的特殊环境中的动态的心理活动,追怀过去时光中的诸多生活片段,感慨“人心是个寂寞的城,一座座适应多诈社会的深锁的城”,感慨自己已经两鬓斑白,再也抱不住“时光巨人的大腿”阿盛:《酒店关门我就走》,参见陈义芝主编《阿盛精选集》,九歌出版社,第229—234页。。在人生的“大剧院”中,阿盛以观众的身份,观看了这样一个特殊环境中的特殊演员的出场,而其中又何尝没有融入作者的独到人生体验与反躬自省呢?
颇值得研究者注意的还有《银鲳少年兄》,该文呈示出阿盛对于生存空间的敏感,以及在意识流手法运用上的匠心独运。《银鲳少年兄》阿盛:《银鲳少年兄》,载台湾《中外文学》第24卷第10期,1996年3月1日。以意识流手法描写一个乡下少年到台北大都市打拼两年所经历的艰辛与心理历程。阿盛写入夜的台北夜景之令人窒息的黑,居所空间的狭小逼窄,与房东客厅里那只水族箱相似,而箱中唯一养活的银鲳鱼,在那两尺长一尺宽的空间里游来游去,让读者从中看到了“一缸子的孤独”。这个离开家乡,承载着母亲挂心与期待的少年,只身来到台北打工求生存的孤独与寒酸,与生存在狭窄的水族箱中的银鲳鱼构成了隐喻关系,显示出作者构思的巧妙。阿盛借助“银鲳鱼”意象,以直观的、自然的、具象的物体,对应表现人的思想情感,巧妙融合,让“银鲳鱼”成为作家情感寄寓的象征物。
现代心理学的原理通常认为:记忆是留存于人的心理结构深处中的生活感受,它往往会由于某种物体的触发,而被偶然唤醒。阿盛在散文创作中,往往由特定物象触发对少时事件的回忆。《六月田水》阿盛:《六月田水》,载台湾《联合报》副刊1987年6月23日。以第二人称的叙事角度,描写一位离开母亲,从乡村到都市打拼人的心理,虽然“他”自觉不停地拖着一具生活的牛犁,已经在大城市中走过日月走过岁,仍然还是对家乡心存“千千结”,难忘家乡六月稻田等待灌水拔高的稻谷,难忘老祖母疼爱儿孙的殷殷教示。“六月田水”已经成为阿盛心灵中唤起往事的记忆之物,触发他联想起那年六月天浊黄浊褐的大水漫过尺多高的稻株的灾年情景,以及乡下农人为着填饱肚子,劳碌一生、颠沛流离的困境,寄托着阿盛对于乡土的深度眷恋与难以割舍的忧患意识。
仔细研读阿盛的散文,往往会令读者不由自主地联想起法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以“追忆”的艺术思维方式,借助超越时空概念的潜在意识,不时交叉地重现已逝去的岁月,从中抒发对故人往事的无限怀念和难以排遣的惆怅。我们若是把阿盛四十多年来的散文创作当作一个整体来看,也会发现阿盛与普鲁斯特文学创作手法的一些相似之处。如果说,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是以叙述者“我”为主体,将其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融为一体,既有对社会生活、人情世态的真实描写,又是一份作者自我追求、自我认识的内心经历的记录,那么阿盛的散文创作,大多也是以“我”作为民间传奇、都市故事的敘述者和家乡往事的见证人,在向读者娓娓而谈他的人生经历与丰富见闻,从中忠实记录自己的内心成长经历过程。
然而,阿盛的文艺创作活动是植根于中华文化的肥沃土壤中的,以热爱故乡、眷恋土地为精神内核,这与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和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以及上世纪80年代王蒙的被纳入“东方意识流”范畴的小说《布礼》《蝴蝶》等并未重视“扎根乡土”创作观的作品,显然有显著的区别。阿盛以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内心活动为轴心,在自传式的文字记述中,不断吸取乡土与民间文化的养分,穿插描写家乡的人物事件,将叙述、描写、抒情与议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增强作品的艺术真实感和审美感染力。从单篇成名作《厕所的故事》(1978年)开始,阿盛出版了多部散文集。他饱含深情地“《唱起唐山谣》”(1981年),“《行过急水溪》”(1984年),描绘《春秋麻黄》(1986年),回望《岁月乡情》(1987年),抒写刻骨铭心的《心情两纪年》(1991年),追忆逝去的“《火车与稻田》”(2000年),反思《民权路回头》(2004年)的体验,守护“《夜燕相思灯》”(2007年),细味《萍聚瓦窑沟》(2012年)之感悟,并在创作功底日渐深厚之时,与读者共“酌”“《三都追梦酒》”(2014年)。我们若把阿盛散文主要作品依据出版时序,作如此“编年体”的纵向排列,则庶几可见证阿盛在台湾当代历史时空转换位移中所展开的散文创作历程。此外,颇值得我们重视的是阿盛晚近散文的重要作品《百工之二》与《打铁匠浣衣妇》阿盛:《百工之二》,初刊台湾《中国时报》副刊,2013年11月17日;阿盛:《打铁匠浣衣妇》,初刊台湾《中国时报》2013年11月10日。此二篇作品均收入其作品集,参见阿盛著《三都追梦酒》,台北:九歌出版社,2014年,第144—152页。,一如此前紧紧把握土地和人性作文章的写作路数,铺陈描写家乡的小人物故事,平实而不加矫饰地叙述生活在社会中下层的普通劳动人民,其中有辛苦劳作的手工弹棉被师傅、做事老实负责的补锅师傅、打铁匠,更有“我”那“为人洗衣”“供我们兄弟上学”的母亲。他们所从事的是传统的手工劳作,纯粹依仗着自己的坚韧毅力和辛勤双手养家糊口,还勤恳地培养了很有出息的下一代。例如《打铁匠浣衣妇》中“我”那勤劳质朴的母亲坚信“身教重于言传”,使“我”从很小即开始与“懒惰”作坚决的斗争。这些人物则可谓中华大地上千千万万“深耕”民间沃土、勤恳持重、恪守本分的劳动人民的典型缩影。
总之,四十余年来,阿盛一直以独辟蹊径的创作风貌,孜孜不倦地深入观察、生动描写家乡的人生百态,从中凝聚并呈现了由时空变换所带来的时代转化、人心嬗变和人世沧桑等图景。诚然,“追忆”已经成为阿盛重要的生命体验与文艺创作的技法。阿盛运用意识流的技法来追忆过往,表现出他对时光流逝和时代变迁的高度敏感性。同样有感于光阴流转和流年嬗变的读者,自然也会从阿盛的散文中引发强烈的情感共鸣和人生感喟。
四 结 语
在其创作生涯中,阿盛始终坚持“注视脚踏的土地,抓住人性作文章”阿盛:《阿盛散文观》,参见陈义芝主编《阿盛精选集》,第23页。,扎根社会现实,“深耕”脚下沃土,珍重乡邻情谊。他不断地从台湾乡土文化的资源中汲取创作的艺术源泉,去挖掘并呈示家乡风土的美学、文化学、历史学和民俗学等多元价值。细致玩味阿盛的散文文本,读者不难发现其中所折射出的台湾农村民情风俗,感受到人与自然、人与土地、人与社会关系的历史变迁,进而体会到离开农村进入都市奋斗的社会底层人物的艰辛、挣扎、拼搏与隐忍。阿盛的散文创作,离不开他对于个人内心和外在经历的体验、感悟与反省。他的创作,也可以说是对于饱含个人情感和灵感的、多年积淀而成的个性的艺术呈现。读者从阿盛的散文文本中,可以探析作家的许多心理特征,如他本人的人生经历,他对于人性孰善孰恶的鲜明观点,他对于乡村与都市文明的真挚见解,以及他对于时光流逝的敏感性与洞察力等。阿盛将对于民众内心世界的深入体察、对于社会现实律动和乡土变迁的密切关注有机结合,从中体会人生苦难,寄寓悲悯襟怀,并孜孜追求文学应真切抒写人生、人性和人情的审美理想。其散文既是对往昔逝去的生命时光的追怀,也是作家本人内心风景的忠实见证,又可视作祖国大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人的文学”和“为人生而艺术”思潮,在当代台湾文化场域回响之中的有力音符。
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台湾文坛,简媜、林文义、杨牧、吴晟和陈列等本省籍作家纷纷涌现出来,呈现多样化的题材种类,技巧与风格也在不断创新。而阿盛以自身紧贴民间乡土的语言风格与讲求故事性的散文叙事方式,顯示出思想深度、文化心理与艺术技法等方面的独特性,在1980年前后即引起台湾文坛的高度瞩目和肯定。其后,阿盛笔耕不辍,以散文、小说创作为主业,写作教学、作品编辑等方面均有声有色,成果厚重,从而在台湾当代文学史的版图中占据了显要而独到的一席之地。
On Ah Shengs Prose Creation
NI Si-ran
Abstract: Ah Sheng, a well-known Taiwanese writer, recalls the humanistic stories and local legends that took place in Taiwans folk world from a distinctive aesthetic perspective,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stories” and artistic presentation of ingenuity, reflecting his high sensitivity to the passage of time and social changes. Adhering to the spiritu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ulture, Ah Sheng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his family background and local friendship. The characters, folk stories and rural animals in his prose work are a combination of the “great tradition” of the May 4th New Literature of China and the “small tradition” of Taiwanese dialect writing, which carries a variety of profound life experiences and perceptions, and reflects the historical mulberry fields of the successive evolution of Taiwans society and culture.
Keywords: Ah Sheng; local changes; characterization; animal portrayal; legendary narra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