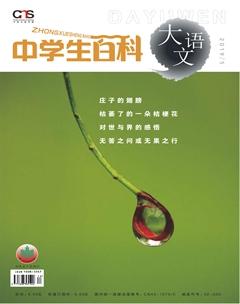艺术之于医院
陈竹
提起医院,你会想到什么?散发着药水味,总感觉弥漫着病毒的空气?一张张充满不安和焦躁的面容?冰冷的白墙?永远比想象中要流得慢的点滴?抑或紧张的医患关系?
似乎在当下,我们对于医院几乎很难有什么正面的印象。大多时候,我们还未遭受什么肉体上病痛的折磨,在心理上已对医院形成强烈的抵触。当然谁都希望自己健康,但生病不是我们自身可以控制的。所以好像谁都无法避免要去医院。那有没有办法来改善这种情况呢?
艺术在一个社会里被认定像医生一样,它具备让患者远离伤痛、舒缓压力的作用。不同则在于,一个是面向身体,另一个是面向心灵。可是治愈身体病痛的医疗过程中,永远无法忽视的是如何抚慰患者因身体受创而带来的心理阴霾和恐惧。于是很多国家让艺术走进了医院,使二者直接联系在一起。在医院融入艺术元素或者开展艺术活动的概念,最早来自1937年瑞典政府导入的政策:在新建或者改造公共设施时必须拿出百分之一的经费用作艺术上的支出。比方说在建一座医院时。院方必须在院内添置一些艺术的作品或元素,比如放置一些画作、插花作品、雕刻作品等,有人干脆直接把医院按照艺术作品的思路来设计。不知道的人从旁经过,恐怕会以为是一座博物馆或者艺术酒店。
前段时间,我所属的舞台艺术学科同文化设计学科的师生协同制作,分别在大阪市(日本生命病院,主要面向患者)和琾市(耳原綜合病院,主要面向职员)的医院做了一场现代舞的公益演出。我作为演员之一有幸参与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在其中一个叫《枯山水》(意为日式庭院)的作品中设置了互动性的舞蹈环节。不管是患者还是职员,看得出来她们对于现代舞的概念还比较模糊,但仍自告奋勇走上舞台同演员一起完成演出。最让我们欣慰的是看到观众分享在意见表上的感想,有观众写道:“这是第一次看现代舞,非常感动!希望还有这样的活动。”还有一位患者说:“两天前刚做完手术,看了今天的舞蹈后让我忘记了手术后的疼痛,感谢你们。”这些文字,打消了我们公演前的一切担心,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活动的价值所在。另外,如我前面提到的,这两家医院也都添加了大量艺术元素。其中一家医院之前的患者中有一些是摄影爱好者,医院把他们的摄影作品印刷后张贴在一面墙上并附上出处,经过这么一装点,也未必输给博物馆里的艺术作品吧。
这次活动的制作人之一——文化设计学科教授森口老师告诉我,日本有一位被确诊为胃癌晚期的落语家,在他入院治疗的第一天,那栋专门治疗癌症的楼里住着许多癌症患者,都是他的“前辈”,当中有一位对他说:“大哥,虽然得了病了,但可绝对不能成为病人啊!”患病不等于就是病人,这是这位癌症患者给予他的箴言。而后,他决定在全国各地的医院开始巡回表演。世界卫生组织如此定义健康健康,是在身体上、精神上保有完满的状态,以及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而不仅仅只是为消除疾病和衰弱。
我相信艺术之于人也是因为身体上、精神上、社会上的状态不完满而存在,比起消除和治愈来说,它更像是面对,更像是重新激活人本身就具有的免疫力。基于上述的健康观。艺术一定是有必要走入医院的。或许它不会改变医院的卫生条件,不会换掉医院的药水味和空气,不会让点滴流得更快,也不会告诉你怎么处理医患矛盾,但它有可能重建的是微妙的人伦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