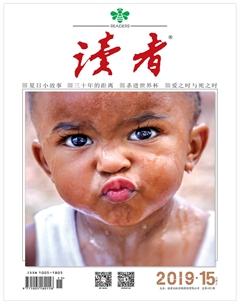不设限的多重天才
小庄

1947年,康奈尔大学迎来了一位讲俄罗斯文学和欧洲文学的教授。这名年近五十的男子相貌平常,眼中却颇有几分傲慢。因为不善言辞,他的课堂授课基本依赖讲稿完成,差不多就是照着念。幸好这门课在学生中口碑颇佳,因此常常座无虚席。显然,此前7年韦尔斯利学院的教学生涯已经给他积聚了一些名气,很多学生早就了解到:他姓纳博科夫,是一名俄罗斯流亡贵族,文学品位极其刁钻,对大作家的点评犀利透彻,常常能提供惊人的视角,而且十分毒舌,所以很想来一探究竟。
说来也是奇怪,这位文学教授此前担任过的一个职位,跟文学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鳞翅目的分馆长,而且正儿八经地在《昆虫学家》这样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过文章。很大程度上,在博物馆工作解决了他的一个大麻烦。纳博科夫一家是1940年来到美国的,他和他那身材娇小的妻子薇拉喜欢收集蝴蝶标本,拥有数量可观的藏品。随着藏品的不断增加,找地方存放成了问题。一开始,纳博科夫只是作为一名无薪的志愿者在博物馆工作,后来这份工作成了兼职,能够领取一份微薄的薪水,在他离开前,大约达到年薪1000美元。不管是由于一直不能谋得正职,还是出于其他原因,纳博科夫待到第六个年头,终于去了康奈尔,带着妻子和儿子,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克瑞格环路8号,搬到纽约州伊萨卡市东州街957号。
那一年,康奈尔大学并不知道自身很快将开启美国文学史上的新篇章。当然你知道——今天大家都知道——1955年,依然还在念着自己文学讲稿的纳博科夫教授,将会出版一本名叫《洛丽塔》的小说,掀起文学界几乎血雨腥风一般的争吵。关于这本书,我敢说即便没看过文字版,很多人应该也看过电影;即便没看过电影,多数人也能背得出它的开篇:“洛丽塔,我的生命之光,欲望之火,同时是我的罪恶,我的灵魂。洛—丽—塔,舌尖得由上腭向下移动三次,到第三次再轻轻贴在牙齿上,洛—丽—塔。”就这么个中年男子爱上未成年少女的故事,位列现代图书馆评选出的20世纪最佳英文小说第四位。
如果本文要讲的只有这个,也算老套到极点,你可以立刻停下了,一个字都不用往下看。事实上,纳博科夫不只是一位文學家,更有耐人寻味的多重身份,除去前面提到的鳞翅目专家身份,他还是一名国际象棋排局高手。想要探讨纳博科夫如何取得他在写作上那些成就的话,小说以外的兴趣和涉猎不可谓不重要,可能还更有趣。
借此表达风格野心的国际象棋高手
1899年4月22日出生于圣彼得堡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父亲是一名自由派记者和政治家,母亲是一名富有的继承人。纳博科夫和几个弟弟妹妹一起,从小就接受精英教育,用英、法、俄三种语言沟通,此外,音乐、体育、博物学一样不落。纳博科夫天资极其聪慧,他的中学同学奥列格·沃尔科夫在回忆录中写道:“网球,他把我们都打败了,象棋也是。无论他干什么,人们都为他的天赋感到惊讶。”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这个贵族家庭就开始了政治流亡。他们一度跑到英国,纳博科夫在剑桥的三一学院短暂修过动物学,同时进修斯拉夫语和拉丁语。1922年,他随家人前往柏林,以诗人和作家的身份混迹于当地的流行社团,常用的笔名是弗·西林。虽然在那个城市住了15年,不过他一直对那里没什么好感,其间他最持之以恒的娱乐项目就是下国际象棋,经常晚上在家里或去朋友处下棋,偶尔还参加比赛。他自认是一个“棋艺相当强的选手”,尽管不是德国人所说的“特级象棋大师”,但在俱乐部,水平已经遥遥领先。这段生活,都被他写进《天赋》中,主人公是一名诗人兼象棋排局高手,这部半自传小说也是他以俄文写的最后一部长篇,被认为是他对旧世界的告别。1926年4月21日,在一家咖啡馆里,纳博科夫甚至和别人一起,在一场车轮大战中差点赢了超现实主义象棋理论的开山鼻祖阿隆·尼姆佐维奇。据说当时纳博科夫已经有很大胜算,却被旁边一个人鬼使神差地挪了一步棋给坑了。在柏林期间,纳博科夫出版的第三本小说叫作《防守》,讲的是一个叫卢仁的象棋天才,最后因对手瓦解了他的防守而自杀。
除了喜欢对弈,纳博科夫还喜欢写象棋评论和设计棋题,发表在刊物上。1951年出版、1963年修订的回忆录《说吧,记忆》中,他写道:“在我20年的流亡生涯中,我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编制棋题上。在棋盘上精心设计一种阵式,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规定的几步之内把黑棋将死,一般是两三步。这是一种美丽、复杂、呆板的艺术……大多数下象棋的人,业余棋手和大师都一样……尽管他们会欣赏一个难对付的问题,要他们编制一个棋题却会被难住。”象棋问题像所有他为之着迷的形式那样,充满智力的趣味和美感。“设局者要具备一切有价值的艺术所具有的品质:原创性、创造性、简洁、和谐、复杂和绝妙的不真诚。”
西班牙裔语言学家卡洛斯·阿尔贝托·科洛德罗认为,国际象棋和纳博科夫的其他专长一样,是作为一种媒介来表达他高度的风格野心的。这种风格野心,呈现为一种智力游戏般的编织和设计,标志着创造者不可捉摸的高超技艺,出现在他的作品中。比如在“带着不合理的魔幻色彩的文学侦探小说”《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以及被女作家玛丽·麦卡锡认为是“一场地狱般的布局,一个捕捉评论家的陷阱”的《微暗的火》中,都可见其端倪。

1958年,纳博科夫与妻子薇拉在纽约的家中下国际象棋
极有远见的鳞翅目专家
“我有没有提到她裸露的手臂因为接种疫苗留下的8字形疤痕?我无可救药地爱上她了吗?她只有14岁?一只好奇的蝴蝶飞过,浸着光,在我们之间。”这是《洛丽塔》中一段提及蝴蝶的描写,为他笔下的角色以学者身份进行的观察和哲学思考提供了支持。而在《微暗的火》中,白色、褐色和红色的蝴蝶相继出现,给故事的发展带来了流动性的美,甚至杀机。纳博科夫在其文字中运用到这种节肢动物还有它们的美丽翅膀,可能真的只是一种驾轻就熟的信手拈来。这些经他提及的蝴蝶标本,很久以前就被钉在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一个柜子的托盘里,曾经是他的研究对象,他们朝夕相对。近些年随着他作为一个蝴蝶专家被越来越多地发掘,文学研究领域也有人开始构建以他为名的蝴蝶美学。
在蝴蝶分类方面,纳博科夫的确做了很多细致的工作,和写作一样,他对此是十分严谨而刻苦的。
2016年,耶鲁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斯蒂芬·布莱克威尔和库特·约翰逊二人合作整理并配以文字注释的纳博科夫手绘蝴蝶图集《纳博科夫的科学艺术》,有300多页,共收录了10位顶尖科学家和纳博科夫研究者的论文,强调纳博科夫的绘画作为科学文献的重要性,评估他对演化生物学和系统学的贡献。纳博科夫一生中画过1000多幅关于蝴蝶解剖结构的技术插图,这本书选取了其中的154幅。
他对一种蓝色蝴蝶做出过极有远见的预言,这大概也是他解剖得最多的一种蝴蝶了。在研究方法上,纳博科夫可说是另辟蹊径,并非根据其形态,而是根据其生殖器来进行分类。在1945年发表于《心智:昆虫学》期刊的一篇论文中,他提出了关于它们演化和迁徙路径的思考,推测这个亚种起源于亚洲,从西伯利亚通过白令海峡来到阿拉斯加,并一路南下到达智利。这个假设在当时可谓非常大胆,甚至有点天方夜谭。人们无法想象柔弱的小昆虫怎么凭借薄薄的一对翅膀进行如此遥远的飞行。但他认为不仅有过这种迁徙,而且一共有5拨。
著名演化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在《知识乱交的悖论》一文中,以纳博科夫为例,谈论了他眼中那些在一个领域被誉为天才而在另一个领域也有显著却不为人所知的成就的人。他提醒人们,纳博科夫可不是一个业余爱好者,而是一个完全合格的、才华横溢的、被正式聘用的专业分类学家,在生物学和一个主要类群的分类方面拥有公认的“世界级”的专业知识,发表过十几篇经受住时间考验的论文。不过,古尔德认为,纳博科夫是一位优秀的、可靠的科学家,但并非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毕竟,他在研究蝴蝶方面只用了业余时间,而在小说写作上,才达到了最高成就。
2011年年初,《英国皇家学会学报》发表了来自哈佛大学分子生物学教授内奥米·支尔斯团队的研究,他们和得克萨斯大学的另一个团队合作,证实了纳博科夫半个多世纪前的猜想是正确的。通过DNA测序比对,他们发现新大陆的蝴蝶有一个共同祖先,生活在大约1000万年前。但许多新大陆物种与旧大陆物种的亲缘关系,却比和它们近邻之间更近,这只能是数次从旧大陆迁徙而来。文章得出的结论,正如纳博科夫推测的那样,有5拨蝴蝶从亚洲来到了新大陆。
打破学科界限的天才们
1953年,纳博科夫来到康奈尔的第六年,他的课堂上来了一个名叫托马斯的小伙子。托马斯年轻得不像话,高中连跳两级直接上了大学,并且也是相当不务正业——主修工程物理专业却来听文学课。两年后,小伙子去海军服役,直到1957年才回到学校,以英语学位毕业。这个小伙子毕业后去了波音公司。1963年,他写出了一本叫作《V.》的小说,拿下了福克纳奖,他姓品钦。
不少美国后现代文学研究者都試图找到纳博科夫和品钦在康奈尔互有交叉的证据,但鲜有发现,除了如今珍藏在公共博物馆中的教师打分表上的确印了该名学生的名字——没有成绩。纳博科夫并不记得有这么一位学生,因为当时听他课的人太多了,而品钦到后来也承认,自己没把纳博科夫的课听完,因为对方口音太重,自己听不懂。只有纳博科夫的太太薇拉说她记得,托马斯·品钦的作业是她改的,很特别,一半手写,一半打印。
康奈尔大学在邀请纳博科夫担任文学教授的那一年,纳博科夫并不知道自己将开启美国文学史上的新篇章。不止纳博科夫,甚至不止品钦。库尔特·冯内古特于1940年入学该校,主修生物化学专业,1947年去了通用电气研究实验室,1969年出版了《五号屠场》。如果说这3个人有什么相似之处,那就是他们全都属于打破了学科界限的天才。科学和艺术都利用了人类独特的创造力,如古尔德所言,“没有想象就没有科学,没有事实就没有艺术”,这二者在某些人身上完全是共通的。
(空 谷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9年第10期,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