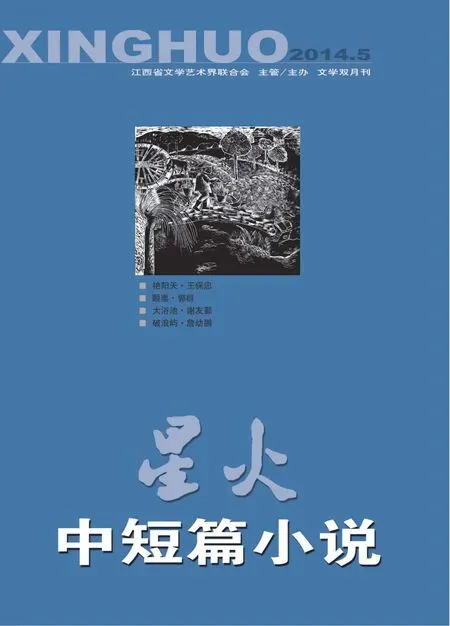寂静有遥远的回声(组诗)
○张作梗
寂静有遥远的回声
寂静也有遥远的回声,就像下在
内心的一场雨,一定对应着多年前某个
阴郁的黄昏或早晨。—常常是这样:
当大火被扑灭,是灰烬,
用慢慢冷下来的寂静,
说出了曾经的炽焰。“倘若不曾背井离乡,
谁会知道故乡也会成为远方?”
聒噪的寂静!当我无意中翻检旧信或
旧物,它就从往事中簌簌掉落,
粘在我的手指上,如琢如磨,
使我如此凝神地关注某个早已不在的
人或物。—它是一坛静水,
但怀揣着永不放弃的动荡;是石头,
渴望被敲击出火。
喧嚣算什么?顶多是水面麇集的蚊子、
石头暂时的沉默。唯有喧嚣过后的寂静,
才是万事万物的显影剂。—
谁没有被月光沉淀的体验?谁不曾
被回忆劫持,独自走进一座午后的树林?
寂静安排了每一次心灵的盛会,
又把人从别处拽回来,
投给火热的生活。“我内心有一座
焚烧寂静的熔炉,但常常又被死亡浇熄。”
因为死亡是一个反弹的皮球,它不时
反弹回来,令我们发热的大脑降温。
灯光里的扬州之夜
站在缀满草坪和篱笆的灯光里,
第一次,我发现夜的构成起了变化。
树叶层次分明,从低到高,
仿佛有一条上浮的光谱;—
而不远处停建的楼盘,将大地拢在一起,
看上去像是一个倒置的星空。
有人散步而来—就好像在一扇
透明的门里走进走出,
看得见身影,但看不见脸。—性别在此时趋向于精确的无形;
而如果背对运河,我的影子就会
在河面上拖出去更远。
河里淌流着灯影,但没有了桨声。
一层层加固的护栏,仿佛把河水圈养在
栅栏里。偶尔,桥上疾驰
而过的车辆将光喷射到河上,
那巨大的水的反光便会把我站立的
位置,朝前或向后移动好几米。
鸟鸣销匿了,虫吟更加沸盈,
灯光踩上去仿佛有轻微的振动;
埋在土里的音乐,若有似无地飘出,
给水边的鱼虾带来一种清浅的
逸乐;我包融在这春夜里,又好像被
无限地孤立出来,—
远处寺庙如墨,水流无声。
我把经验缝在……
我把我的经验缝在一切过往的
认知上,就像蜜蜂把蜜缝在蜂桶中;
未知的物事有蜜蜂在蜇,
但尚未酿成蜜。
然而,思维的蜂桶总是赶不上飞翔的
花朵。当风吹歪了认知,当更多的
田野被四月驱赶,
经验变得手足无措,
我不得不将之推倒重来。
—我不得不重新塑一个菩萨,
以应付内心更多的祈求。过往的口袋
太小,总是装不下日新月异的生活,
而要想酿出更多的新蜜,
必须把火涂在唇上。
必须把旧我摈弃,在蜂桶里更新
酿蜜的软件,才能将大地捆缚在身上,
赢取更多悲辛的眷顾。而既成的
经验,也将在这悲辛的击打下,
如蝉蜕壳。所有的叩头只为了卸下
肉身的负担,劳作也是如此。
无名的愉悦
一到春天,我就有一种无名的愉悦。
这种愉悦使我看上去,非常像是从别处
投放到尘世的一块跳动的光斑。
正如“我悲伤我就跳舞”一样,
我跳动是因为我愉悦。
然而我掌控不了这跳动,更驾驭不了
这跳动。五花八门的跳动中,
我的心蓬松开来,
宛若一块生日蛋糕。—
我向每一阵拂过脸颊的风问好。
我致敬—对那块刚被我搬到阳光下的
阴湿之地。我甚至将我的祝福友好地
送给我的敌人,谨祝他健康长寿。
我的愉悦没头没脑,没心没肺。
我的愉悦是蒲公英的愉悦,就那样
轻悄悄地飞离“本我”;一层柔软的晕眩,
仿佛没有重量的跳动,
飘到哪儿都是欢乐的音符。
一到春天,我就被一种无名的愉悦捆缚。
唯有走出庭户—去到大自然中,
藉用斑斓的跳动松绑,
才有望拆卸这无形的绳索,
将我从窒闷的愉悦中解救出来。
鹅卵石
鹅卵石有光滑的局限性。
它不可能变成鱼、浮萍或水边的云杉,
也不能进化为雾天的垂钓者。
它几乎只能作为一块石头,和投水者、
失事的船只、落日一起,
沉埋在水底。
—它几乎只能是自己的一个寓言,
怀揣着永恒的被打捞之梦,
将锋利的棱角藏掖心里,
在一轮又一轮水的击打下,
修炼为一个大沉默。
它几乎只能被各种实有之物的倒影撕扯,
像一座从内部关闭的寺庙,
抱持一种摇晃的平衡,
摸着自己坚硬的名字赶路。
它几乎只能……不!当水退去,
当河床像一个真相显露,
那些船只、投水者、落日已了无踪影,
唯有它们像河水的块根暴凸出来,
从未腐烂,以不被消泯的存在,
记录下了水底漫长而动荡的
隐姓埋名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