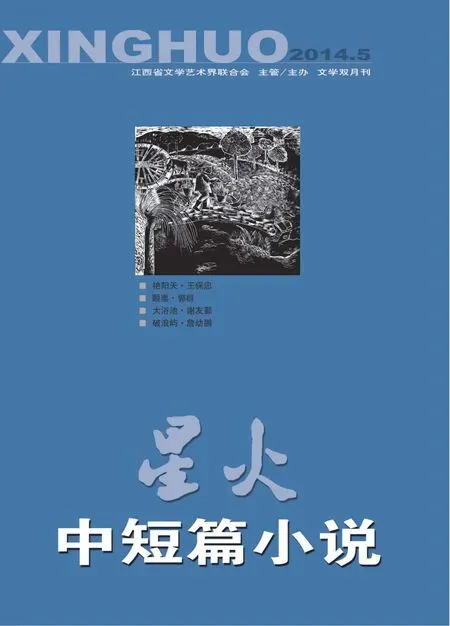最后一次探望
○赵海萍
在她去世前半年的一天,说不清是出于恻隐还是懦弱,总之,是一种强劲的力量,它促使我带着儿子回到那个我生活了十三年,但却始终不能爱上的村庄。因为不爱,所以,我尽可不受谴责地省略掉它的名字。那儿埋葬着我十余年的青春,是一片荡漾着痛楚与挣扎的死水湖。
白露乍过,薄凉微侵,静谧的天空突然显得高远、深邈,它以一副祥和而博达的姿态俯瞰人间。夕阳的余晖给这即将陷入寂寥的楼群增添了几许凝重和沧桑。杂草和月季完全失却了活力和光泽,它们衰败的枝杈使人伤感;几个泛黄且遍布皱纹的丝瓜在晚风的驱逐下微微颤抖着身体;有三五成群的闲妇迈着悠闲的步子打发时光,她们边走边窃窃私语。
我们的脚步乍一落上第一层楼的台阶,狗的尖细的欢叫声和激越的扑腾声便清晰地传来。它的记性好得让人意外和感动。我知道,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和一条年轻健壮的博美犬住在二层西门。老人是我前夫的母亲,差不多七十岁了。现在,她像半截正在腐烂的木头躺在卧室的大床上,或者,僵硬地坐在客厅的圈椅里打盹儿。她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每年圣诞节,这个以吝啬出名的老太太都会拿出二百块钱捐给教会,要知道,她每月只能领取六十块钱的补助。在她被疾病打倒之前,常风雨无阻地到教堂聚会,即使在我由于生产而急需照顾的那些日子。她仍痴迷于“我们日用的饮食源于主的恩赐”。不止一次,在给她端上饭菜之后,我盯着她坏坏地问:“要感谢谁?”她看看我,略显肥胖的脸上迅速掀起一抹羞赧,之后,她小声低语:“感谢主。”
“妈妈,你听,它知道咱们回来了!”
“是啊!它总是这么有灵性!”
打开房门的瞬间,博美犬“妞妞”像个疯子一样扑上来。它总是这样,即使你下楼不到五分钟折回来,它也会这么疯狂地表达爱意和思念。儿子蹲下,用手轻轻抚摸它光洁、纤细的长毛,它则不安分地吐着鲜红的小舌头寻觅他的脸亲吻……
“妈妈,你看它!”儿子一边嗔怪“妞妞”的过分热情,一边左右扭着脸躲避。
“哈哈,它简直像你的小情人儿!”
洁净的地面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一些竹板凉席的碎片,关于“妞妞”撕咬竹板凉席的嗜好,儿子的父亲已经通过电话告知过。我当时明确表态:“让它啃吧,反正这个竹板凉席早已派不上用场。何况,你让一只活蹦乱跳的狗儿拿什么消遣呢?”现在,看着这一地碎竹片,我突然怜悯起这个无辜的小生命。主人们都在外忙碌,它孤零零地陷落在这所空荡、寂静、毫无生气的房子里,只一个常年躺在床上熟睡的老人和它作伴。当然,一起生存在这个房子的,还有阳台上的朱顶红和茅厕里的潮虫、蚂蚁。但它们不谙孤独滋味,或者,它们没有愁苦、病痛和恐惧。
老人能够起身迎接我们,但她没有,她直挺挺地躺在透窗而入的一团白光里。那团光无限轻,似乎又无限重,它已经不能为她带来光明。听到有脚步声,她的眼珠转动了几下,并未扭头。我和她儿子结婚时,她身体尚好,只是肥胖,但肥胖还没对她的精神和健康造成影响。她对儿子结婚这件事漫不经心,既不肯拿出多年积蓄的几分之一,也不肯满心欢喜地拾掇新房,更不肯给予我们一字半句真诚的希冀和祝福。那时,我充分体恤她儿子的难处,就连婚戒都没买,并且还自作主张把彩礼报到最低,然后和他一起朝朋友们借钱……那时,对自由和奋斗的美好憧憬完全占据了我的内心,我完全不能预见两种家庭的差别,也不能预见自己即将开始“笼中鸟”的悲剧人生。
“还好吗?老太太!”我冲她笑了笑。
老人并不吭声,只是呆呆地看着我,眼珠一动不动地盯着我,那样子像端详一个陌生人。她的眼角被糊状的乳黄色眼屎堆满,眼神黯淡无光;稀疏的花白头发凌乱而倔强地支棱着;脸颊比两个月前愈显消瘦,皱纹密集,使一张脸看起来像一小片蛛网……一个人要是执意苍老起来,谁能阻挡得住呢?
“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你是我儿媳妇。”老人声音小极了,但并不吃力。她并没有因为我的到来而表露出些许意外和欢愉。
“想我们了吗?”
“想了。”
“你儿子呢?”
“不知道。”
“你女儿呢?”
“刚走。”
“尿湿了吗?”
“没。”
…………
如果我有兴趣这样问下去,她就会一直这样不紧不慢地答下去。我突然发现她身下的褥子已经洇湿,虽然光线暗淡,但洇湿部分的颜色深了许多。我习惯性地用手摸了摸——真凉!
“起来吧,尿湿了。”我没必要再对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粗声粗气,之前,我曾用刻薄语言冲她大吼小叫,那是我的罪,我承认。虽然我的罪源于她的罪。
“不湿。”老人伸出干瘪如柴的右手胡乱地朝身下的褥子抓摸后喃喃自语,她喃喃自语的时候像个孩子,无助又茫然。
“真的湿了,我还能骗你吗?”我又耐心地说了一句。
老人开始微微欠身,试图挣扎着坐起来。她在一场大病之后变得格外慵懒,尽管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起身,但只要身边有人,她就会放弃努力。这于她十分不利。但她显然不在乎这些,即使她不情愿早日见到心心念念的主耶稣,她也不屑于使自己的任何一个零部件得到合理的锻炼。
老人整天一动不动地躺着,并不介意谁来不来看望,也不介意裤子里的屎尿有没有人收拾,更不介意博美犬“妞妞”是否饿着肚子。“妞妞”已经是陪伴她最久的活物了,但她并不关心它,甚至,她厌恶它清澈的眼睛和讨好的叫声。有时候,“妞妞”会将小爪子搭在床铺上等待她的抚摸,但这样的愿望往往落空,它根本不懂她的绝望和阴暗。像她这样的人,即使在身体健康的时候都不会对一条狗表现出热情和爱。何况现在,她已经病魔缠身。每逢“妞妞”将小爪子搭在床铺上等待她抚摸的时候,她会恶狠狠地打它的脑袋。它并不躲闪,以为她只是做个架势罢了。但落到它脑袋上的巴掌格外实在,以至于它根本不能相信这样的力量会来自一个病恹恹的老太太。在多次挨打之后,它再也不主动到她跟前卖弄热情。
“脱掉吧,咱们换一条干净的。”我把不太柔和的声音抛向她。她茫然而无助地盯着我,妄图从我这儿得到力量。但显然,我没有朝她伸出援手。
她只好缓缓地坐起来,瘦弱的身子像一坨随时倒塌的稀泥。她究竟是怎样在两年时间内减掉满身赘肉且瘦得不成人形?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她的饭量相比往日有增无减,活动量相比往日大大减少,但体重却在这夜以继日的昏睡中悄然蒸发了。
“为啥要脱?”她突然大声问我,听起来有些愤怒,就好像遭受了戏弄一般。
“因为裤子湿了,被你尿湿了!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老往裤子里尿尿呢?你明明能下床走动,可为什么老往裤子里尿!”我不由地多说了两句。这十来年,我从来没有像爱自己的母亲一样爱过眼前这个女人,从她的中年到老年,从她的飞扬跋扈到弱如风烛。
“湿了吗?”她同时用两只手在褥子上抓摸,“没湿啊,好好的,没湿。”她怔怔地看着我,仿佛急切地等待我的肯定。
“脱。”这个字几乎是从我的嗓子眼儿压迫出来的,我觉得我的耐心和善意在刹那间被撕成碎片,一些恶的成分在霍霍地生长。
也许是我的声音太过奇特,毕竟有愤怒和无奈的成分在里面,“妞妞”摇着尾巴循声而来,径直跑到我跟前伸出小舌头舔了舔我的手,在发现并无异常之后又跑开了。
“怎么了,妈妈?奶奶又尿裤子了吗?”儿子急忙跑过来,顺手拿掉我斜挎在身上的背包,“您有活儿干了!嘿嘿。”他略显拘谨地站在那儿,将目光投向多日未见的奶奶。对于孙子的出现,老人并未表现出惊喜和热情,甚至,她都没有呼唤他的小名,也没有招手让他过去。
儿子带着“妞妞”去了客厅,我听到从“妞妞”的嗓子里发出一种尖细而怪异的声音,我知道它在向昔日的小主人表达思念和爱意。
“脱掉?”老人面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这次没等我继续下命令便乖乖地开始了脱的动作。她的双手已经不能准确地发力,即使她思维清楚,但指挥双手准确无误地活动已然费事。她一点一点往下褪那条由于洇湿而涩滞的单裤,很费力,但最终还是脱将下来。
“这还算是一个女人的身体吗?”我的心刹那间痛得剧烈抽搐。老人的胸部及以上部位由于上衣的遮拦我不能看到,但凹陷的腹部及附着在松塌塌腹肌上的大片黑斑醒目地裸露在我的眼前,两条蜷缩着的大腿瘦巴、干枯,像稍一用力就会折断的干柴棒,要知道,它们曾经像白玉般丰润动人呐!可怕的岁月和病魔毫不客气地摧毁了一切。
老人终于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将裤子脱掉,像丢弃废物一样把它扔在地板上。若是几年前,一定会有大颗粒的汗珠簌簌滚落。但现在,没有一滴汗。我想,她果真进入了衰竭期,距离面见耶稣的日子不远矣。我一直对她不冷不热,俨然一个客气的亲戚。即使在我还是她儿媳的时候,我也只是例行公事般照应她的一日三餐。有时候,她明明知道饭已上桌,却并不利索地起床;有时候,我明明看到她已经欠起上半身,但稍过些时候再看,她又四平八稳地躺了下来。这样,我的怒气便迅速淤积,于是,我便用手掌朝她屁股上拍几下。“干吗打我?”她用眼睛瞪我。“你到底起不起?”我扯着嗓子问。“起。”她才哆嗦着开始起身。其实,我应该拉她一把,帮她穿上鞋子,带她到餐厅,扶着她在圈椅里坐稳,把筷子递到她手里,把碗朝她推一推……但我很少这么做,多数时候,我像个冷静又绝情的旁观者观摩她笨拙的“表演”,任由她孤零零一个人对抗衰老、病痛和孤独。
我把尿湿的裤子拿到卫生间冲洗。为她刷洗被屎尿污染的衣裤已然成为习惯。浓重的尿骚味升腾起来,霎时,我被这久违的味道感染,心也跟着柔软起来。回想这十余年时光,即使我包揽一切家务,即使我善待她所有的亲戚,即使我偶尔给她买衣服和鞋子,我仍然感觉心有愧疚。因为这看似饱满的温情和爱意并非出自我的本心,而完全源于责任和良知。其实,这和施舍并无二致,老人心知肚明。但她显然习惯了被动地接受。老人逐渐变得寡言、漠然、迟钝,即使两个亲女儿逗她,她也爱答不理。她终日默默无闻地躺着,任由透窗而入的阳光明灭,或者移动。她全然忽略了活着本身,而只顾妄自活着。
我带着儿子离开时,轻微的打鼾声已经在狭小的房间响起。她睡着了。之前,她还健康的那些年,她的打鼾声格外高亢,抑扬顿挫地拉着调子,而现在,它们衰弱得使人伤感。自从被高血压、脑溢血、宫颈癌等各种疾病纠缠上之后,睡觉就变成她证明自己活着的主要方式。只是活着,没有任何内容。她惧怕死亡,尽管她深信自己死后灵魂能够得救,能够和耶稣及信徒们生活在那没有饥饿、病痛、欺诈等一切罪恶的美好国度。在死亡面前,她仍然表现出了一个凡人的拒绝和恐惧。最后那段日子,她知道能够维系她生命延续的不是耶稣,而是食物和药品,为此,在吃药和吃饭上,她表现得英勇无畏。但我知道,她距离那最后的栖息地越来越近,并且,她可能不知不觉加快了前进的速度……
第二年初夏的一天,我忽然接到孩子父亲的电话,他沙哑着嗓子说:“过来吧,老太太不行了。”当我赶到她床前,那一副比之前更为枯槁的身体把我吓坏了。她的脸呈现出可怕的暗黄色,闭着的眼睛深陷进密集的皱纹里,颧骨突出,嘴巴微张,鼻息微弱。那一刻,一股沉重而酸楚的气流在我胸腔里翻滚,撞击着我的五脏。我哭了,第一次为这个并不爱戴的女人流下了伤痛的泪水。我像是她晚归的不孝女儿坐在床边陪着她,一刻也不敢离开。但她一直没有睁开眼睛看我,她安静地躺在那儿,不痛苦,不悲伤,不恐惧。正午时分,透窗而入的阳光照着她的上半身,她的双腿剧烈地抽搐了几下,牙关紧咬……她永远地去了,在我的注视下。那一刻,我再一次哭了,为一个生命的陨落,也为这最后也是最彻底的诀别。
如果我知道她会在第二年初夏就永绝于人世,我想,我会在最后一次探望她时表现得更温和一些,或者,我会经常带着儿子去看她,为她日渐干涸的生命增添一丝暖意。如此,我就不会在每每想起她时,心生怅恨和悔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