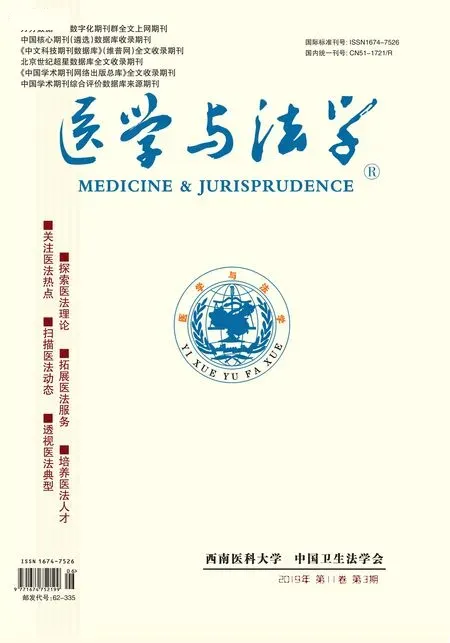“健康中国”视域下药品零售不当促销现状的原因分析(下)*
孙寒宁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取消以药养医,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制度。《“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也提出要推动医药分开,调整市场格局,使零售药店逐步成为向患者售药和提供用药及药理知识学服务的重要渠道。但我国零售药店的实际发展现状,却普遍存在处方药买药品赠药品、虚假宣传、诱导消费者过量购药或购买高价药等不当促销行为,且其已成为广大消费者皆可体察的行业“潜规则”。笔者对长沙、株洲、湘潭(以下简称“长株潭”)的零售药店进行抽样,并对当地的消费者进行问卷访谈,实地考察药品零售不当促销现状,以期能为规制药品零售不当促销提供现实依据和数据参考。对于实地调研中药品零售存在的诸多不当促销的行为及其原因,笔者主要从现有法律规范的制定与实施、药品零售行业、消费者三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
一、不当促销系现有法律规制体系及行政监管存在不足使然
法律规范体系的统一协调与完善不仅是立法科学性的重要体现,也与法律规范的贯彻落实密切相关;同时,“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实施是实现法律作用与目的的条件。但目前,我国对于药品零售促销的规制体系及行政监管存在诸多不足。
(一)现有法律规制体系不完善
我国既有的药品零售促销法律规制体系的不完善、不健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法律规范的矛盾冲突影响法律适用。
对于零售药店的药品能否有奖销售、搭售和买赠,以及哪类药品可以有奖销售、搭售和买赠的问题,不同法律规范的规定存在较大差异(详见下表)。虽然在实务适用中,可根据《立法法》的有关规定适用《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条,但事实上却已造成了地方性规范和执法监管的不统一。
2.对药品零售的不当促销缺乏有效规制体系。
其一,现有法律规范滞后性明显且缺乏对药品零售促销行为的专门规定。有些现行的法律规范都是十年甚至二十多年前出台的,比如关于“暂不允许采用网上销售方式”的法律规定①仍属有效,而药品现今在网上的销售却已开展地如火如荼。在我国医药卫生体制大刀阔斧改革的当下,相关规范的制定和更新存在明显的滞后性。针对药品零售之有奖销售、虚假宣传、活动解释权等不当促销行为的法律规制,只能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等进行认定和处置。
其二,违法促销的责任追究机制不健全。尽管相关法规明确禁止药品的有奖销售,却并未明确如何处罚此类违法行为,《药品管理法》也未涉及此问题,这就造成虽然违法却无须承担法律责任的状况频频出现。[1]有些虽然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处罚较轻,缺乏威慑力。《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药品零售企业违反该法第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未凭处方销售处方药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以1000元人民币以下的罚款。也就是说,零售药店无处方销售处方药时,相关监管部门只是“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只有逾期不改正或情节严重时,才处以最高1000元的罚款。如此低的违法成本,很难达到规制的效果。

表 现行法律规范关于药品促销活动的不同规定
3.相关规范的制定脱离实际,缺乏可实施性。
调研的十类不当促销行为中,最严重的问题是200家零售药店全部存在无处方销售处方药的行为。但是按照我国法定的处方药销售流程,“无处方销售处方药”仅是其中一环,除此之外,处方必须经驻店的执业药师审核之后才能销售相应的处方药。但是我国执业药师数量严重不足的现象长期存在且至今未得到有效解决。这就使得即使严格遵守“有处方才销售处方药”的规定,零售药店的处方药销售也会因执业药师数量不足在药师审核药方环节受到阻滞而不能贯彻下来。

图1 2013-2017年我国零售药店数②和零售药店执业药师数③
由图1可以看出,2013-2017五年间,零售药店执业药师数量虽然一直在快速增长,但是由于与零售药店的基数差距较大,截至2017年12月底,零售药店执业药师注册数量最多时,其与零售药店数量相比仍存在92259人的数量缺口。而且,在这些虚高的“零售药店执业药师数量”④中,有相当数量是“执业药师证”而并非执业药师本人。[2]而催生这一现象产生的制度性原因在于:在执业药师数量与零售药店数量严重不匹配、也无零售药店分级管理等配套制度下,法律规范仍硬性规定经营处方药、甲类非处方药的药品零售企业应当配备执业药师。
(二)药品监管机关的执法监管乏力
现有监管制度中,对零售药店的日常监管方法主要有全面检查、专项检查、跟踪检查、有因检查、日常巡查、飞行检查及远程电子监管等。
但是由于监管人员、监管手段、监管分工等方面的问题,使得行政机关对药品零售不当促销行为的监管并未达到理想效果。
其一,“目前药品监管机关的监管队伍远远不够解决现实问题,仅靠现有的人员和监管情况,监管部门很难发现不当促销行为”。面对长沙市的4300多家药店,监管部门的人员非常有限。同时,许多违法促销活动又具有隐蔽性,零售药店的促销活动灵活多变,可以随时改变、换撤店内场景布局。特别是一些处方药、甲类非处方药买药品赠药品问题,药店为了规避法律和监管,往往在门店内不做任何宣传和标识,当向消费者具体推荐时,才会口头告知,这些行为也增加了监管发现的难度。
其二,药品监管机关的监管手段也较为有限。对于具体哪些是不当促销行为,很难得出比较稳妥的界定,这给执法监管中带来了认定上的困难。也就是说,对于严格依法执政的监管部门来说,法律依据是不明确的。在药店促销中,比较多的是买药品送乙类非处方药的情况,除此之外的一些促销行为,如说买药品送鸡蛋,充值卡,或者是会员日打折,从形式上来看,并没有违反《药品流通管理办法》第二十条。但这些行为却在客观上刺激了消费者多购买药品,也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造成消费者的药物滥用。对于这类现象,药监部门只能提前告知,或者在发现时对其进行责令改正。
其三,药品零售促销不同监管部门之间存在权责分工不明,多头执法的问题。对于药品广告和促销活动,食药监部门需事前审查,一旦发现其存在违法,则由工商部门处罚,即由两个部门共同监管。此外,如果零售药店的广告或宣传是通过媒体发布的,就会涉及媒体相关的监管部门。这就使得即使发现不当促销行为,药品监督管理机关处罚和处理的措施和手段亦非常有限。
二、不当促销系药品零售行业的市场化运作使然
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主体,药品零售企业的市场化意味着其经营活动所更多地关注的是营利,故追求高毛利、强调销量的行为便无可避免;其市场化也影响着药店的竞争、地域布局和不同地域销售市场的差异。这些也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对零售药店具体促销方案的制定产生影响。
(一)零售药店趋利性明显致纷纷不当促销
零售药店作为市场经营主体,营利是其最终目的。零售药店的市场化发展使得提供社会公共医疗服务的场所变成了商业卖场。[3]
处方药必须凭处方销售,而处方的不易获得,消费者对处方认识不足等情况使得去药店购买处方药的消费者带处方的概率并不高,这会影响药店药品的“短频快”销售,药店为了保证销量和盈利,多不会遵守该规定。有受访者表示,“曾经有段时间去药店购买处方药必须要带处方单,但药店搞了两个月就没再搞了”。为了应对处方单检查,在调研时发现,一些药店会让店员补写处方笺。
此外,为了获取更高的利润,在通过各种促销活动吸引消费者购药的同时,常常会搭配销售或有针对性地向消费者推荐高毛利的药品,一些医院销售的毛利低的药品,零售药店要么没有卖,要么不参加活动,而且价格一般要比医院药房的高。
(二)零售连锁药店的市场竞争激烈
连锁药店违法不当促销率较单体药店整体偏高,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相较于单体药店,连锁药店实力雄厚,有更雄厚的人力、物力及财力资源以多次开展促销活动,且促销活动的类型更多力度更大;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即为了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因为健康中国战略、医药体制改革的大潮不仅给零售连锁药店带来机遇,也是带来了巨大挑战,这种机遇和挑战具体表现为:其一,政策鼓励提升药品零售连锁率;其二,在取消医院药品加成、处方药外流政策的推动下,零售药店有机会承接更多的处方药,但这部分资源需要与社区诊疗机构等其他承接处方药的主体相争夺;其三,药品零售行业内部竞争激烈,一心堂、老百姓、益丰等大型连锁企业不断通过并购跑马圈地,多次斥资收购单体店和小连锁,[4]在此情形下药品零售的低水平扩张和市场竞争同质化的趋势日渐明显;[5]其四,多种资本渗入,市场资源争夺激烈。医院自办药店快速增长,主要经营处方药为主的品类,[6]电商进入药品零售业,外资也乘此机遇,加快入股国内药企的步伐。[7]
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零售连锁药店为了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争夺有限的消费者资源,便试图通过开展各种促销活动来达到吸引消费者、增加消费粘性、提升品牌知名度、获取更多销售利润的目的。
(三)大型医院附近消费群体较稳定
至于实地调研发现大型医院附近零售药店的处方药、甲类非处方药的买赠、有奖销售、贬低他人、“凑单满减、多买多送及其他”劝诱销售行为的发生率低于整体水平,其主要原因则在于这些药店占据优良的地理位置,仅“借力”大型医院稳定、高频的需药群体,便能获得较其他地区零售药店更为充沛、稳定的消费者资源,故其为吸引消费者买或多买药品的处方药、甲类非处方药买赠,以及有奖销售和“多买多送、凑单满减及其他”劝诱销售行为的发生概率较低;另一方面,从医院出来的消费者,一般都有较为明确的购药目标(不是有处方单,就是遵医嘱或者对自己的身体症状有了更为正确的认识),故这些药店店员一般也不需要为了推荐某个药品以贬低他人的方式进行推销。
三、不当促销形式同消费者欠缺相关药品消费知识间的关联
消费者对药品基本知识的了解程度、药品促销法律规范的认知水平及维权意识的强弱,直接影响着零售药店的销售行为——针对不同的消费者,采取不同的不当营销策略。同时,消费者作为最普遍的守法主体和社会监督主体,上述认知的不足也会影响法律政策的贯彻落实。
(一)消费者药品基本知识匮乏
药品知识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而且药品属于低频消费品,一般消费者用药需求不大,很少去药店,也较少关注药品相关知识,对药品分类等基本知识的了解程度也不够深入。
1.消费者无法有效区分处方药和非处方药。
如图2,在200位受访者中,104位,占比52%的受访者不能区分处方药和非处方药。73位,36.5%的受访者“不太能区分,只知道一些是处方药”,且在73位不太能区分的受访者中,有相当一部分受访者所理解和认为的处方药,就是指医院医生开的处方单上的药品;或者仅知道药店里放在柜子里的药品是处方药。只有23位,占比11.5%的消费者能够区分处方药和非处方。也就是说,近九成的受访者是无法有效区分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的。

图2受访者能否区分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占比

图3受访者能否区分甲类非处方药和乙类非处方药占比
由图3可以看出,167位,占比83.5%的受访者不能区分甲类非处方药和乙类非处方药;25位,占比12.5%的受访者不太能区分甲类非处方药和乙类非处方药;只有8位,占比4%的受访者能够区分甲类非处方药和乙类非处方药。也就是说,高达96%的受访者不能区分非处方药中的甲类非处方药和乙类非处方药。
由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消费者药品分类管理知识极为匮乏。此种情况下,即使消费者知晓凭处方销售处方药的相关规定,但其在去零售药店购药的过程中,因无法有效识别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并不知晓店员向其推荐了处方药,甚或产生没用处方即可买到的药就不是处方药的错误认识。
2.消费者对“安全用药”缺乏正确认识。
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消费者因为药品专业知识的匮乏,对用药安全也缺乏正确认识,多数受访者认为只要不是假药就是安全的。对药品不良反应、药物滥用等问题缺乏必要的认识和重视程度。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抗生素滥用现象,在确认受访者是否去药店购买过处方药时,只要问是否买过阿莫西林、头孢等抗生素,基本上都给予了肯定回答。实地调研中,对于胃痛、腹泻等症状,店员在搭配销售时,也常会搭配阿莫西林、诺氟沙星等抗生素。
(二)消费者欠缺相关药品零售促销的法律知识
消费者药品零售促销法律知识的不足是前文所述的“无处方销售处方药”问题普遍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访谈数据显示,169位去药店够买过处方药的受访者中,61位,占比36.1%的人“有时带有时不带”(有就带,没有就不带)处方;37位,占比21.9%的人称“药店没说让带”;30位,占比17.8%的人认为“根本不需要带处方”;2位,占比1.2%的受访者认为“药店既没说让带,自己也觉得不需要带”;仅有39位,占比23.1%的受访者称自己去药店购药时必须带处方。有些受访者表示,虽然知道购买处方药不带处方是不合理的,但是让我们带处方的话,又不经济:“自己感冒拿个消炎药,还要跑去医院(诊所)开个处方才能买到,太麻烦了。”“这些药我都吃过,自己知道,根本不需要处方。”由此可以看出,对“必须凭处方销售处方药”的问题,消费者的认知程度非常有限。

图4零售药店销售行为是否存在违法不当之处
由图4可以看出,对于零售药店存在的“活动解释权(药店单方享有解释权或者最终解释权等滥用解释权的行为)”和“无处方销售处方药”这两类法律规范明文规定的违法行为,前者有29位(占比14.5%),后者有32位(占比16%)受访者认为是正当合法的。大多数受访者表示不清楚(分别为84人,占比42%;77人,占比38.5%)。高达半数以上的受访者都不知是否违法,甚至认为是正当合法的行为,更谈何举报投诉和维权呢?
(三)消费者维权的意识不强且积极性不高
面对在药店购药时遇到的零售药店滥用解释权的行为,只有4.5%的受访者回应会“与药店据理力争”,而30.5%的受访者“感觉自己受到了欺骗,会直接走人”;20.5%的受访者会选择“不跟药店计较”;42%的受访者选择“只买需要的,不再参加促销活动”(详见图5)。也就是说,当零售药店出现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时,超过90%以上的受访者是选择不了了之的。

图5遇到解释不一致的情况一般会如何处理
虽然有的药店在显著位置公布了行政监管部门的举报电话,连锁药店还公布了公司内部监管部门的联系方式,但是就整体看来,消费者维权的积极性并不高。在对受访者进行访谈时,对于如果在零售药店购药的过程中遭受了不当促销的情况是否会维权的问题,50.5%的受访者权选择“视情况而定,损失严重会”(详见图6),即对身体健康和经济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况下才考虑维权。对于如果会选择何种方式维权(可多选)的问题,仅选择“要求药店赔偿”和“如果是连锁,向零售药店内部监管部分投诉”就占比41.5%(23%+18.5%)。也就是说,更多情况下,消费者倾向于采取“私了”的方式维权。

图6药店购药遭受不当促销是否会维权
有些受访者表示:“直接找药店说说理就行啦,维权来维权去没有用。”“自己打过一次举报电话,但是占线,就再也没试过了。”“我比较懒,嫌麻烦,能不搞就不搞。”“去法院起诉的话,成本多高啊,不到万不得已,不会选这个的。”“我不会找连锁药店内部的监管部门的,它们是一起的,找他们不管用。”或称自己“没文化,不参与。”还有受访者明确且反复地强调自己的选择自己负责,有些则称“虽然会选择去行政部门举报,但是不晓得程序”。
由上可知,缺乏权利意识;时间、经济等方面的成本过高,过程繁杂,成效不明显等,是消费者维权积极性不高的重要因素。
四、结语
报告根据抽样数据,对长株潭三地药品零售不当促销现状进行了统计分析,并对现象背后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对于药品零售不当促销规制中的结构性困境,应将药品流通体制改革放到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大盘子中统筹考虑,采取“标本兼治”的方式加以推进。[8]药品零售不当促销行为多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药品零售行业内部以价格取胜的低水平、同质化竞争。对此,零售行业应当转变竞争思路,相关行业协会和政府部门也应当提供适当的行业指引。此外,还应加强宣传教育,增强消费者安全用药意识,特别是对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应该予以特别关注。
注释
①《处方药与非处方药流通管理暂行规定》第十四条处方药、非处方药不得采用有奖销售、附赠药品或礼品销售等销售方式,暂不允许采用网上销售方式。
②数据来源:《2006-2017年度食品药品监管统计年报》,统计数据截至2017年11月底,http://samr.cfda.gov.cn/WS01/CL0010/,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8月9日。
③数据来源:笔者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执业药师资格认证中心公布的全国执业药师注册情况统计所得。http://www.cqlp.org/Default.aspx,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9月17日。
④截至2016年底,考试合格人员中,分布于生产、批发、社会药店、医疗机构人员约为9万、6万、21万、27万;而截至2016年底,注册于生产、批发、社会药店、医疗机构的执业药师人员约为0.3万、35万、29.8万、0.5万人。数据说明,尚有大量工作于药品生产企业和医疗机构执业药师没有注册;在社会药店注册人员又多于考试合格人员,除了合理的人才流动因素外,另一个因素即是“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