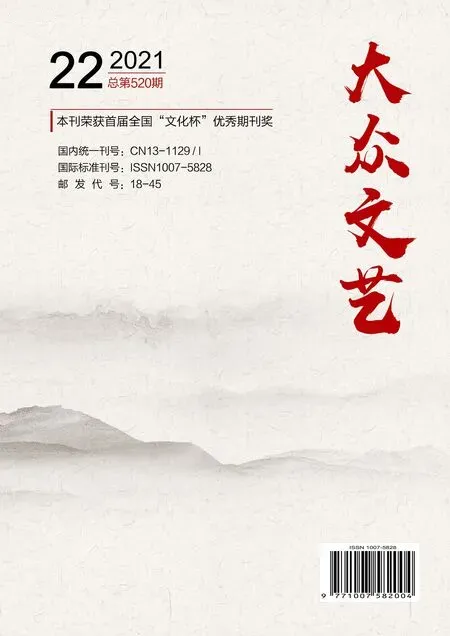基于《四个春天》纪录媒介的影像解读
田 慧 (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 400044)
一、一、视点与诗意: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思与诗
导演陆庆屹以独特的私人化的视角拍摄了4年光阴里父母的美丽日常生活图景,期间也穿插了对父母过去生活的时间记忆。梅索斯兄弟曾说:“如果一个拍摄者缺乏耐心和感情,并没有用镜头凝视所拍摄的对象,那么出来的画面将是冷漠的,无法打动人1”。凝视死亡、凝视日常生活中的诗意,把焦点对准了自己最熟悉的父母,导演在作品中有了三重身份:1、儿子;2、纪录片拍摄者和制作者;3、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导演陆庆屹也坦言:“因为我对我爸妈很了解,我想把他们的生活框起来,让他们自己去观察,看着他们美好的自己2”。在片尾处,母亲跟父亲探讨着如果自己走了,谁又来陪伴父亲?儿子北漂还没有成家怎么办?在无意识之间,最痛苦的莫过于站在镜头背后的导演,透露出导演对父母老年的一份哲思和守护。
视点作为一种特殊的细节,是表象中的某一瞬间。这种细节吸引了我们的凝视,促使我们队表象以及我们于它的关系进行重新审视3。《四个春天》把父母的日常生活并置,并创造出作者私人的、独有的视点。导演陆庆屹也在访谈中谈起喜欢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中家庭关系的处理手法,包括沟口健二、侯孝贤等人影像风格的影响4。小津安二郎中淡化的叙事技巧和对自然主义式的家庭生活记录;一开场就把视点带到了贵州独山县的乡野之地,以春节回家准备家宴的视角开始了叙述。在人物设计的细节铺设上,正是父亲对乐器的热爱,母亲尤为钟爱做菜和唱歌,使得这两位老人在人物关系上有了更多的交集,也使得片子本身具有了诗意。当然,陆爸和陆妈独特的人物个性和生活情调则使得本片在人物性格上就已经有了个体化和典型性的性格特征,使得人物本身就充满了诗意。
二、喜与悲:情感交迭之间的浪漫与现实
在结构安排上,《四个春天》以家庭过年相聚为主线,一共拍摄了四次春节回家的素材,期间穿插着姐姐庆伟的去世和90年代拍摄的家庭录像素材。在表达策略上,本片主要围绕时间的递进和情感的流淌为线索,运用一种积累式和爆炸式的情感对立的共情方式。《四个春天》通过对人物心绪长时间的跟踪记录,是创作者随着现实生活的不断演进,并不断深入父母的生活态度上,拍摄对象慢慢地把内心深处的剖析,使得情感从平淡之中跌入到悲伤,再到父母乐观对待女儿的去世的起伏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从现实向浪漫的回归。
生活中的残酷让生命中的欢乐无处可居。纪录片的叙事不像小说或电视剧电影那样讲述故事和设置情节,精心安排的事件形成以因果关系的编排。《四个春天》在结构上集中突出情感因素对人物的心绪走向,对事件的提炼和浓缩,进而对现实进行了创造性的处理。在影片结构方面,导演按照电影的结构来对纪录片进行铺排,前面的人物心绪比较平淡和欢快,对于姐姐庆伟的病情和去世,也只是陆爸略微提及“她生了那个病”,中间也穿插了一家人去贵阳的医院看望二伯,对于姐姐庆伟的病情却只字未提,以至于中间揭开姐姐的病情和去世时,基调由喜到悲,由生到死的情感转变直接打破了生活的平衡,到后面三分之一则充满了生死观的主题性的见证:姐姐庆伟的生病到去世,90年代的家庭录像,亲历了父母年华的老去,也见证了一个家庭的成长与变化,但始终没有改变的仍旧是陆爸陆妈在经历生离死别之后的豁达人生态度,传达出生命乐观豁达的哲理性思考,也是对现实层面的一层浪漫主义回归,这得益于导演陆庆屹对爸妈生活的敏锐观察和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生活化的细节积累,和创作主体的个人情感的介入,透过爸妈质朴的生活和积极的生命态度赞誉。在喜与悲,生与死,平淡与沉重的交迭中,传达了对炽热生命下的光影礼赞和韵味悠长的乡土画卷。
三、抒情与物化:平淡化的现实创造
于平淡中见生死,方寸中显亲情。正如别林斯基所说:“内在生活把外部事物化成了自己”,平凡人设中的平凡世界,没有大起大落的戏剧化的场面,有的也只是对子女日与夜的守候和等待。约翰·格里尔逊对纪录片中的戏剧性这样评论:“人们普遍认为,艺术中道德的崇高只有通过英雄、暴力与流血牺牲才能得到表现,就像希腊和莎士比亚的作品那样,这种观念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粗俗”5。在过度的强调戏剧性、冲突性的叙事思维的今天,《四个春天》用最平凡的影像,书写中国式独有的家庭影像之书,将这个平凡生活之中的伟大情感,用淡然化的手法呈现出具有普世性的亲情回馈。约翰·格里尔逊所提倡的不仅要拍摄自然的生活(the natural life),而且要通过细节的并置创造性地阐释自然的生活。通过对生活中的戏剧性的提炼,将这个普通的中国家庭道德与伦理跃为景框中的影像,窥见了一段专属于中国人独有的家庭情感。
母亲的对子女的最好的抒情方式则是通过中国传统的熏香肠和一桌美味的菜肴,父亲更多的则是对音乐的痴迷和对传统生活仪式的遵循。于生活中窥见真情,本片没有刻意去书写父母老年生活的艰难困苦,也没有去刻意书写女儿庆伟从生病到葬礼的悲伤,而是把着力点放在了表现父母对生活的乐观态度。片子呈现了一次有关有关生死的场景:姐姐庆伟在医院里的最后时光。母亲只能对于女儿的病痛只能以念佛的形式来祈福,相对于父亲来说,以一种更加含蓄而淡然地方式来诉诸对女儿的爱。父母仍然在用他们独特的方式去爱儿女:吃饭的时候要给女儿留双筷子;去女儿坟边种菜,种花,母亲则是给远去北京的儿子打包好饭菜。无论是喝交杯酒的怨言:“你都不看我”,还是埋怨老伴把蜜蜂当初恋情人,在垂暮之年的两位老人,也将人性中的真善美和传统的爱情观“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长情完满告白。
四、写实与写意:一种媒介的人文关怀
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影像媒介,既能复刻如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的‘物质复原论’和安德烈·巴赞的‘电影本体论’的写实主义,也能在影像上如同王国维“曰景,曰情”般的情境交融。导演陆庆屹的摄影技术上的“非专业性”的缺憾却被反哺到的朴实情感所填补,在电影结构的安排中,情感的呈现方式上则更多的遵循了情感的细节性的积累和人物心绪的把握,尽管影片的风格趋向于电影的表述方法,将生活巨细的细节置于眼前,凸显着诗意情感的电影,聚焦于身边最熟悉家人的人文视野,在父母简单、纯粹的世界里,“业余性”的镜头展现出了对生命礼赞和乐观人生的本真性,在家庭题材中熔铸以其独特的人物个性和地方景观的写意。“蓝色的天空像大海一样,关阔的大路上尘土飞扬”,两位老人背对着在女儿庆伟的坟前自由歌唱,父亲已经不大记得起歌词,在这个平凡的世界里,一首《青春友谊圆舞曲》的时代之歌,也成了父母的陪伴,而儿女则成了父母爱的供养。结尾父母的旅游日记,也为这份私人影像里掺杂了时间记忆,使得家门口寻找素材的典型,平民化的影像美感从写实到写意的媒介方式得以回归。影片诗意风格的体现,还在于选取了各种意象来表达主题。基于片中的出现的各种动物和植物的意象:池中的鱼,飞回来的燕子,养的蜜蜂,腊梅花,花椒树,两次浇花,给鱼换水,女儿的坟边种菜等系列生活细节的铺设,一切景语皆情语,足以见两位老人对生灵的守护,对生活的热爱。燕子又飞回来了,把蜜蜂像初恋一样对待,用塑料带去照看蜜蜂等生活细节的捕捉,使得本片人物塑造得更加鲜活。
于平淡无奇中见真情,在这份家庭影像的方寸之间,记父母的年华老去,书写着年华中最长情的告白。纪录片最本真的一面就是对现实中的人本身的观照,从格局上来说,题材并非边缘化,而是对最熟悉的父母生活的提炼和凝缩,简单的记录了父母的老年生活的缩影,也是对父母老年生活的人文精神价值的终极关怀。
注释:
1.吴保和,王培主编,《隐喻与细节:世界著名纪录片导演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1,第78页.
2.http://m.v.qq.com/play/play.html?coverid=&vid=f07286j97kk&pt ag=2_6.3.9.17501_copy,来源于腾讯视频.
3.麦茨等著;吴琼编,《凝视的快感:电影文本的精神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84页.
4.《北京电影学院学报》(Journal of Beijing Film Academy)[J].《四个春天》导演访谈,陆庆屹,孙红云,张浩,2019年03期.
5.杨远婴主编,《电影理论读本》[M](修订本),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1.第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