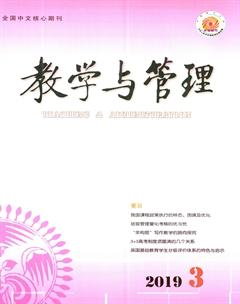历史数据史料运用前的鉴别
苗颖
摘 要 将数据史料运用于教学之前,必须对其真伪正误进行鉴别,以保证历史教学的科学性。对数据史料的鉴别应主要关注三个方面,一是考史源,也就是从史料形成的源头上考证其科学性,谨防史料来源“先天不足”的情况;二是明史变,充分认识时代变迁带来的度量衡制度的变化,确保数据换算的准确;三是慎史述,转述历史应严谨,要杜绝舛误和以讹传讹。
关键词 历史 数据史料 鉴别史料 实证
史料教学是当前历史课堂的常态。中外史料多彩多姿,给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教学资源,但正如何炳松先生所说,“史料之中,所在多伪”,“当今可信史料,寥若晨星”[1],运用史料之前,对史料的真伪正误进行必要的鉴别,既是历史教师求真求实精神的体现,更是历史教学科学性的前提。“正是对史料的整理和辨析工作,或者说史料考证工作,才形成了历史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一种专门技艺。”[2]修订版课标将史料实证作为学科核心素养之一,更是大大增强了中学历史课程的学术色彩,也对史料鉴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如何开展教学运用前的鉴别工作呢?本文试以数据史料为例略作说明。
数据史料在历史学中有着广泛的“分布”,也一直是教学和命题的常用素材。自2013年陈志武等人在清华大学举办每年一届的量化历史讲习班以来,借助数据史料研究历史成为了历史学界的热门话题,也给中学历史教学的数据史料运用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源和更加广阔的前景。数据史料能够将历史事物量化,让历史的呈现更加精准精确,更显严谨,也更具说服力。但一利亦有一弊,由于资源有限和中学教师普遍缺少深入的历史研究,加之数据史料披有“精确性外衣”,各种讹误较为隐蔽,史料的鉴别工作极容易被忽略。
一、考史源:谨防史料來源“先天不足”
大部分的数据是时人或者后人出于某种需要而进行的整理或统计,由于时代局限、技术落后、资料散佚乃至于主观故意,许多数据史料并不能反映历史的全貌,有些甚至严重偏离历史真实,在教学中加以运用,更需要我们审慎地从史料形成的源头上考证其科学性。
中国古代虽有浩繁的典籍,但其中的许多数据可信度不高。四川师大的张邦炜先生曾就北宋的耕地面积、亩产量等做过详细的计算,成果发表后被许多知名学者广泛转载使用,影响颇大。但后来张邦炜发现,自己所依据的《宋史·食货志》等原始数据并不可信,在其基础上得出的计算结果并不能成立,于是在2008年出版专著《两宋史散论》时,就干脆把所有自己据此研究得出的数据统统删掉了[3]。对于中国古代史上的数据混乱和不全的情况,王家范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非常遗憾的是,历史文献并没有给史家提供这种数量统计最起码的条件——例如虽有偏差极大的全国垦田数,却没有全国农业总产量的数据;有严重隐漏的全国人口数,却没有全国农业人口的统计数据。”中国古代计量史学“几乎不可能”,勉为其难,也只有“各种象征性的或示意性的统计”[4]。
除各种客观原因造成的数据史料失真以外,主观原因造成的数据错误也比比皆是。网上有一篇标题叫做《差距太大太大的史料数据》的帖子[5],说的是中日双方对日军在抗日战争各主要战役中伤亡数量的记录差异,笔者虽无从考证其真伪,但依常情想来,中国方面为了鼓舞士气,在战果宣传中有所夸大在当时也是必要的。由于中学生没有足够的鉴别能力,教学中一旦运用这类史料,危害远大于历史研究。因此,中学历史教学和命题必须谨慎选用那些已被学术界认可的数据史料。
2005年上海卷第23题就是一个数据来源“先天不足”的典型。试题用图表的形式给出了清代丁税征收的变化,让学生选出四个选项中表述正确的一个,见图1。
本题的数据史料运用至少有两处错误,一是丁口混淆。竖轴标出的是人口,但实际上所给的数据则是人丁数。这在当年已有老师撰文指出[6]。二是图示人丁数及与之关联的人口数是学术界早已提出质疑并基本否定的说法。古代的人丁和人口数,由于统计手段的落后,赋税制度的影响、各种瞒报漏报等,存在很大的统计偏差。比如,据明朝官方的统计数字,人口长期徘徊在6000万左右,而今天史学界普遍认为,明朝人口超过1亿,有专家甚至估计超过2亿[7]。清朝初年的人口也至少有1亿,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约有1.5亿,乾隆末年则达到3亿多[8]。本题图中所给出的清初人口数仅2千万左右,显然与事实相去甚远。试想,从1734年的2千多万增长到1794年的3亿多,增长率岂不高得离谱?
二、明史变:谨防单位换算“以今律古”
时代在演进,度量衡制度也会发生变化,后人认识历史上的数量时必须充分考虑古今度量衡的不同。忽视度量衡差异而造成的结论严重错误在历史研究中并不少见,王家范先生在《中国历史通论》的“农业产出、亩产量及其他”部分就专门分析了因忽视度量衡制度的历代不同而造成研究结论严重偏差的情况[4]。因此,严谨的历史学家总是很重视度量衡的换算。黄仁宇在著《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时,专门把度量衡的界定列在开篇[9],中国农史研究丛书的《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首章就是“先从度量衡亩的有关问题谈起”[10]。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由于一些教师忽视了度量衡单位的古今差别,“以今律古”,造成了明显错误,试举一例。
一位教师在解释人教版必修二的“1866年,方举赞投资200元,在上海虹口创办了发昌机器厂”时,为使学生直观地认识这200元的价值,对币值进行了古今换算:“鸦片战争后清朝的银元1元为0.72两白银,同时古制一斤等于16两,一两就是31.25克,按照今天的一克白银5元计算可得:1866年的200元就是现在的22500元人民币。”
将历史上的数量换算成今天通用的计量单位,链接学生的生活实际,直观性、现实感都很强,对学生理解历史大有裨益,是一种很好的教学创意。但此处的换算有着简单化的倾向,且不说一百多年来的物价上涨因素必然会影响货币价值的变化,仅是计量单位的换算就存在明显的问题。清代的一块银元重0.72两,即七钱二分银子是不错的,一斤等于16两也是对的,但清代的一斤是今天的500克吗?一两等于31.25克吗?
从先秦时期,我国就有了斤、两等重量单位,历代均使用,但换算成今天的“克”,则不同时代之间差距悬殊,最多时约合670克左右(唐朝),最少时约合220克左右(魏晋)[11],无法一概而论。清代的度量衡制度称之为营造库平制。以纵黍百粒之长为长度的基准,称营造尺,以一立方寸金属(黄铜)作为重量的基准,叫库平。对于清代一库平两折合今天的多少克的问题,学术界已有共识。据度量衡史研究专家对清代多件权衡器的测量折算,测得清代的一库平斤在594.4~596.8克之间。到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划一度量衡时,改从西方各国之制,以营造尺一立方寸純水在摄氏4度时的重量定为库平两的基准,后来还请巴黎万国权度公局代为制造铂铱合金“两”原器和镍钢合金“两”副原器各一个,今藏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这就为我们实测清代一库平两的实际克数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经实地测量,清代“两”原器重37.3克,折合一斤等于596.8克[11],上例中的31.25克显然是错误的。
除“斤”“两”等重量单位之外,“尺”“寸”“里”等长度单位、“升”“斗”等容量单位和“亩”等面积单位的古今差异也是非常大的,在教学时一定要弄清古今的换算关系,以免出现不必要的错误。
三、慎史述:谨防数据转引“鲁鱼亥豕”
和一般史料不同,数据史料在转引时极易出错,且错误不易被发现,而数据上的细微错误(如小数点的位置)都足以谬之千里。这就要求我们在转引数据时要仔细再仔细,尽量避免鲁鱼亥豕之误。笔者去年曾开设了一节《明朝的政治》公开课,教学中引用了大家耳熟能详的一段史料:“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日,送到皇宫的奏章共1160件,涉及3291件事情。”这一材料最早进入中学教学领域应该是2005年高考上海卷第29题,当时试卷并没有给出出处,笔者备这节课时,在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找到了相同的表述[12],以为找到了试题材料的出处。但后来发现,自己竟然是在以讹传讹,原始材料根本就不是如此。该记载最早出自《明太祖实录》:“己未,给事中张文辅言:‘自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日之间,内外诸司奏劄凡一千六百六十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事。。”[13]其后在多次转引中,这两个数字逐渐出现了新的“版本”。为便于说明,笔者结合自己的阅读及推测,列出了一个从《明太祖实录》,到《春明梦余录》[14]《天府广记》[15],再到《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文献文章中这两个数字的变化,以展示其中的讹误现象(见表1)。
《明太祖实录》中的两个数字是1660和3391,到了孙承泽那里变成了1660和3291,到钱穆先生则变成了1160和3291,上海卷命题人想必是和笔者一样转引自钱穆著作,结果这组数字就持续错了下去。实际转引过程未必如笔者所述的如此简单直接,但数据经过转引后变得面目全非,就连史学大家如钱穆也概莫能免,数据转引错误的易发性、隐蔽性可见一斑,引用数据史料岂能不慎重?
参考文献
[1] 何炳松.通史新义·历史研究法[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
[2] 徐蓝,朱汉国.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解读[S].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3] 张邦炜.历史学如何算起来?——从北宋耕地面积、粮食亩产量等数字说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4]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5]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1b8fd90102uwmp.html.
[6] 陶圣建.我国古代的人口和人丁问题[J].中学历史教学,2005(12).
[7] 葛剑雄,曹树基.对明代人口总数的新估计[J].中国史研究,1995(01).
[8] 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9]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M].阿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10] 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
[11] 丘光明,邱隆,杨平.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12]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13] 董伦,等.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六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4]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
[15] 孙承泽.天府广记[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责任编辑 郑雪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