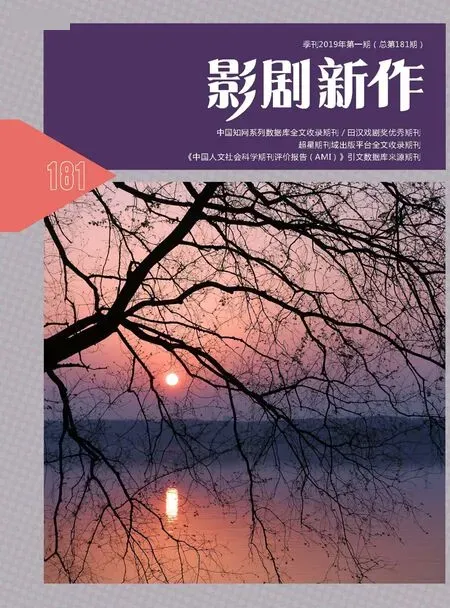逼近体验性
——以回到现场为目标的《敦刻尔克》
胡 珺

2017年上映的电影《敦刻尔克》,是名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首次尝试真实战争题材改编的作品。影片采用陆海空三条叙事线和大量个人视角,展现了1940年5月至6月间德军围困法国敦刻尔克海岸时,在轰炸机、潜艇等威胁中,40余万英国士兵中的幸运者,受到联军各兵种支援和普通民船协助,跨海返回故乡,并取得国民谅解的战争故事。
诺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多次强调,他是以惊悚悬疑片的方式处理这一“人的生存”题材的,并以还原历史、还原人物置身其中的“肉体性”(Physicality)为目标。面对数十年间已成为英国国族传奇和二战影视热门题材的“敦刻尔克奇迹”,诺兰发挥了自己既有的风格——影片拥有他标志性的非线性叙事结构、持续的悬念、紧张的节奏、令人惊叹的视觉奇观、烘云托月的音乐与音效。可以说,《敦刻尔克》是一部因彰显民族凝聚力而带有主旋律感,同时又有意规避好莱坞式战争类型片已形成的叙事手法、伦理格局、影像风格,具有实验性又不乏商业性、流行性的诺兰作品。
一、架构叙事表盘:联结时间与生命的整体隐喻
按照观看顺序,全片结构可划分为六段。
第一部分(00:00:00-00:05:34),序言,不再是复杂的历史背景交代,影片用字幕、传单和跟拍镜头迅速地切入被围堵的英国士兵处境。小型冲突后丢盔弃甲、硕果仅存地到达敦刻尔克海岸的步兵汤米,既是英军困境具体而微的象征,更是将观众带入历史场景、代入种种感性体验的良导体。
第二部分(00:05:34-00:52:03),是影片内容的铺垫部分,也是三线叙事语法的构建部分。在简洁的字幕说明后,不同空间、不同时长的三条叙事线依照“防波堤—海上—空中”的固定顺序,分10轮分别交待了代表“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待拯救者、施救者、掩护者的英国士兵、民船、空军各自的行动,让观众了解各方目的的同时习惯本片的叙述方式。
第三部分(00:52:03-1:09:30),是影片推进悬念的部分,观众已觉熟悉的叙事线在此分裂得更为复杂。实际上,在防波堤线的第10段落,于汤米的视角之外,随着位于屏幕中心陆军上校在逆光中步过海岸,防波堤叙事线已分裂为汤米和堤岸军官两处。空中线也因为飞行员柯林思的迫降,产生了叙述的碎片(稍后整合进海上线)。海上线也发生了变化和冲突:从海上废墟到来的“颤抖的士兵”不愿意再回到代表着死亡的敦刻尔克;在他与船长道森的争执中,学徒乔治被误伤了。
第四部分(1:09:30-1:22:02),是影片的高潮与华彩段落。在一次次的恐惧、努力、失望的充满未知的轮回里,由英国出发的大量民船带给海岸士兵们最切实的鼓舞,停滞的撤退得以继续。各位主人公与不同的叙事线也因“救助士兵”的共同目标里在临近敦刻尔克的海面上汇合,大部分人物的生死悬疑都有了结果。三条叙事线也缝合成功。
第五部分(1:22:02-1:28:04),是影片走向收束的下降段落。飞行员法里尔在耗尽燃油后仍然在敦刻尔克英勇地驱逐德机。道森船长也在返程途中指挥若定,保护众人免于受害。
第六部分(1:28:04-1:34:48),是影片的尾声,保住性命的士兵、默默死去的少年、自愿奉献的飞行员展现着各自的选择,又受到了肯定的评价。
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叙事“戏法”里,最关键的是对各线交接点的交待以使观众能够通过逻辑自行复原事件的全貌;同时又能在导演的精心安排下,于不同叙述段落的悬念与期待、紧张和松弛的组合、切换中尽情体验“此时此刻”的超强时间感和超越时间感。对这些关键点的处理,让同一件事发生多次而改变视点,是成熟而有效的方法。叙事线相互交汇之际,也正是已发生过的事件越来越高频地“重新被看见”之时。
此外,诺兰还以“时间”为焦点——从柯林机舱中上升的碧绿海水,跳接荷兰商船被打出的弹孔漏进的涨潮活水,再联系法里尔被机油量具体化了的飞行限制——这些让角色们命悬一线的“时间压力”,指向的都是被观众感知了困境的年轻生命的点滴流逝。时间与生命这两个具有抽象意味的相关概念,通过导演设定情境的物理、心理转换被具体而可感地传递到了观众终端。
有评论指出时长分别为一周、一天与一小时的三条叙事线各自同时推进,其意象如同表盘上的时针、分针与秒针,它们前进,交错和汇合,组合出命运的无常图景。时间,这一与敦刻尔克大撤退休戚相关的元素,正好也是诺兰长期钻研的对象,在这一点上,诺兰的多线叙事手法与这一历史题材取得了内在的契机,其叙事框架也因此撑起了事件推进的经纬,承担了总体的隐喻功能。
二、体味生存的“正义”:战争中的伦理困境与和解
虽然诺兰版的《敦刻尔克》没有采用历代战争片导演建立起来的类型片成规,例如,没有拍摄血肉横飞的阵地战或肉搏战,没有最高统帅的作战指挥部,甚至没有出现具体的纳粹军人形象,但观众一样能由影片人物的伦理困境体会到非理性战争的残酷、无情给人带来的身心重创和造成的人性扭曲。
为了给自己平凡的人生添上些英雄气概,刚从学校毕业的乔治在没有深思熟虑的情况下登上了月光石号。道森对他说“我们要到战争那儿去”,他恐怕不完全明白。天心难测,乔治就那样默默地倒在了底舱中,弥留时能够回忆的也只是那并不显赫的期望。然而,我们似乎无法完全怪罪伤害了乔治的“颤抖的士兵”。见多识广的道森可以明白他确实正深陷于对死亡的恐惧中,“他已经不是他自己了,而且有可能再也无法是他自己”。以上两种都是战争给予人的最不可逆的、超出了时间维度的伤害。事实上,我们确实无法比较哪一种更难于承受。
在防波堤,矛盾更紧急、更尖锐。纵然指挥官设立了撤退秩序——伤员应该优先,士兵应按军种重要性列队等候,法国盟军不能挤占英军船支……但战争可以轻易破坏这一切,在德军斯图卡轰炸机的嚣叫声里,连医务船都无法免于战火。影片用冷淡的态度尽量客观地展示战争中人们生死一线的偶然,甚至荒诞。飞行员努力阻止敌机伤害海面行船,然而被击落的敌机又成为致人于死地的新祸首;维系着人们生命的渔船,被敌军当成了枪击训练的标靶。这些冰冷现实激发了人类求生欲望的赤裸裸的自私。表面上看来,逃生是人们的共同目标。可是,作为个体最高利益,求生的资源又如此稀缺,那么为了自己生存而牺牲他人的同等权益,就成了这种极端情境中最阴暗又最几乎是最“合理”的策略了。
荷兰商船里,直率霸道的亚里克斯借用民族主义的语汇要求冒充的法国士兵离开,为大家减重;并且他认为下一个备选的“异己者”就该是并非同一战斗单位的汤米。然而鲁莽的他毕竟还没有想到,如果这个挑选仍需推进,新的标准该是什么?面对法国士兵于最后逃生可能之际,莫名失去行动自由,遗憾身死,相信观众的同情心会油然而生,从而超越对“吉布森”是投机逃兵的道德判断。求生毕竟是人们共有的最顽固的心理动机,在此又成为观众对人物产生代入感、同理心的人性基础。
作为作者导演,诺兰也在片中安排了和解的段落,并且确实是巧妙的。对观众来说,在对人性的幽微、生存的困境、差序之爱的基础有了细致的体认后,飞行员法里尔不顾自身安危,一再选择掩护同胞逃生,其难能可贵就被反衬和突显了出来。然而,对于敦刻尔克海滩上未知前途的士兵们,喷火战斗机的出现实在是姗姗来迟,有如鸡肋。当燃油耗尽的法里尔第一次滑翔过海滩,士兵们只是麻木而冷漠地无言相对。而当法里尔再次调头驱走德军轰炸机时,人们对他才报以欢呼和信赖——和解来自肯定,肯定基于误会的消弭,基于个体牺牲自身利益,为集体奉献、使集体受益。
相较之下,彼得在乔治死亡后,面对“颤抖的士兵”忐忑的询问,从愤怒的指责改口予以疏解,则体现了更加温暖和主动的人文关怀。作者没有刻意维持谎言,“月光石”号到港后,“颤抖的士兵”看到了乔治的尸体被运上岸。在本片这种“写实”的总体氛围里,可以倾向于认为影片末尾彼得完成乔治心愿的报社供稿举动,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借此少年身上确有的略显冲动的英雄气,来表彰大事件中那些看似平凡的无名、无声的普通人,从而礼赞敦刻尔克事件与本影片可以升华的共同精神内核——于绝望之中亦不放弃,以团结一致、坚持美善共铸人间奇迹。
三、由感官通道体验“现场”:在“复古”中实验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诺兰通过叙事手法选择和人物命运设定对《敦刻尔克》这一作品主题的开掘。此外,他还综合采用各种具体编剧、拍摄、制作技巧来巩固其风格与意蕴,于复古中又不乏实验性、开创性。所谓“复古”和“实验”主要体现在诺兰对经典悬疑片、默片技巧的借鉴,对胶片使用、实景拍摄的坚持,并结合叙事编织、音效设计等对其“重塑历史现场”目标的推进。
首先,诺兰通过对经典悬疑电影《恐惧的代价》(1953)、《海外特派员》(1940)等的成熟手法,使已知结果的历史事件,具体化为个人逃生的惊险过程,恢复了情节的不可预见性。三条叙事线上的海滩、民船、飞机都是封闭空间,没有被具象化的敌军被隔绝在外,反而更显得无处不在和异常可怖。影片通过生死悬念的制造、保持持续提供情节动力和吸引力,一步步推向情节和情绪的高潮。
其次,作为首次执导历史题材的导演,诺兰选择了相当激进的现实主义标准。他复刻了英军军装、重建了1公里防波堤,遍访全球寻找二战时期的古董战机、战舰真实出镜等等,其历史考证功夫得到普遍肯定。
由于实景拍摄受到实物条件、技术操作的种种限制,不如数字制作技术可以随心所欲,使得本片空中线的飞行镜头在空战类影片系列中,看起来相对朴素,没有呈现同题材作品“必备”的“大场面”与数字特效,受到一些影评人的诟病。然而,来自历史现场的真实道具营造了异常真实的刺激,为演员表演提供了独特的支点和引导;胶片作为成像载体,比起高清技术更接近人眼的感受性,提供给观众特有的沉浸感,是虚拟影像大行其道的时代里难得的“复古”。
并且,在本片由IMAX胶片摄影机呈现的画面里,仍有面向镜头(观众视角)两机相逐而来、由高空调头俯冲压制敌机的旋转视角等等精彩片段,使得影片在不断的悬疑、恐惧外,又为观众带来惊奇、冒险的官能冲击,进而由各种感官途径的刺激和“移情”产生对剧中人情感和经验的代入。同时,这种与商业电影相似的观影体验,又赋予作品以流行性、娱乐性,使得《敦刻尔克》最终得以打破斯皮尔伯格《拯救大兵瑞恩》所保持的二战题材影片的最高票房纪录,成为新的行业翘楚。
与此似乎矛盾的是,影片使用大量主观视角进行拍摄,并保持一贯到底的限知叙事,以此强调面对巨大的人类灾难,每个个体的所知都仅仅是主观的、有限的,不完全的。但在另一层面,那些被叙述内容的细节感又反映出个体经验同时是特殊的、无可替代的,不应该被抽象为统计数据或者文献词条的、活生生的。这样的感受又被导演设计为是台词极度压缩的,以营造压抑气氛、配合冷峻的纪实风格,同时希望如同默片时代作品那样,最大限度地依赖镜头语言叙事,以更接近于电影这一所谓“第七艺术”的特殊核心。
此外,原创音乐与音效、音响的精心编排,也是本片的重要技术成就,被一致认为与影片叙述达到高度的契合。“谢沷德错音”与采自诺兰怀表、真实武器的音效、甚至噪音等通过电脑计算由合成器制成完成;以极简主义的设计代替了大片式主题旋律,为将观众带入片中场景贡献良多。
以上种种取舍,都体现了诺兰电影创作的实验性和创新性。然而实验性总是带有先锋色彩的、不完美的,更经常是冒险的、非大众化的。《敦刻尔克》也是如此。叙事线的复杂设计,其意图传递本身要占据表达的时长,这是影片放弃为其人物设计具体背景、细节,造成某些评论谈及的人物无性格、无纵深的原因之一。当然,结合诺兰的创作定位,这样的后果可能无伤大雅,甚至更符合于历史上年轻而懵懂的英国士兵的真实情况,也有助于将观众的注意力更纯粹地牵引在人物的物理感受和心理波动上。但是,由于传递信息的手段被大大限制,本片的叙述效果,尤其是对空中线的理解,几乎只能依赖观众的悟性。相信能一次性分辨四类机种,将五次交锋的繁复起落理解透彻的观众只能是少数;更多人只会在信息缺失中眼花缭乱,连蒙带猜,其体验和感受必然因此失准,无从谈起。
幸而《敦刻尔克》是符合于电影创作规律的,在多次观看后,众多迷惑可以解开。诺兰的勇于尝试、积极实践更多体现的是正面的意义,他的“逼近体验性”追求具有一定的启示性。
——《克里斯托弗·诺兰电影文化研究》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