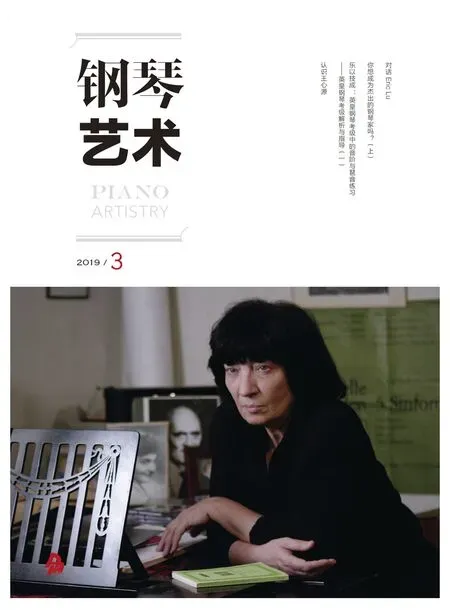“岭南风格钢琴曲”刍论
——梁茂春教授讲学记录(一)
整理/郑韵帷
整理者按:2018年5月3日至8日,广州星海音乐学院钢琴系和佛山市青少年文化宫联合主办了“迈向新征程——中国钢琴作品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的最后一天,中央音乐学院梁茂春教授作了名为《“岭南风格钢琴曲”刍论》的学术报告。笔者根据这次讲学的录像记录下了整个讲学的内容,又请主讲者梁茂春教授,参讲者冼劲松、曹光平、杜宁武、周凯模等老师过目并对记录内容作了修改。
梁茂春:我到广州来讲《“岭南风格钢琴曲”刍论》这个题目的起因是这样的,从2015年以来的两三年间,我一直在写一篇题为《百年琴韵》的长文,想写一百年来(1915至2015)中国钢琴创作的发展历史。这篇文章在《钢琴艺术》杂志上已经连载了18期,现在还在继续连载。我在梳理百年中国钢琴发展脉络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有趣而有意义的现象——中国已经形成了几个比较成熟的、带有鲜明地方风格和特色的钢琴曲创作群体。首先就是广东风格的钢琴曲,现在我称之为“岭南风格钢琴曲”,它从开始起步到逐步发展,到形成高潮,复又潮起潮落,却始终延续发展,一直持续到今天。可以说,这条线索非常清晰,相当完整。
和“岭南风格钢琴曲”同时或前后发展起来的,还有“陕北风格钢琴曲”“新疆风格钢琴曲”“西南风格钢琴曲”等。相比之下,“岭南风格钢琴曲”呈现出一条比较明晰的发展脉络,它是岭南音乐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一个新生的部分,是岭南音乐中充满生机的一个新的现象。
讲这个题目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的夫人蔡良玉和广东有联系。蔡良玉的母亲是广州东山人,所以,我和广东就有了这么深一层的关系,很愿意到广东来讲一下岭南风格钢琴曲的发展历史和成果。
今天不仅是我一个人讲,还有几位钢琴家、作曲家要来现场演奏和讲解。青年钢琴家张奕明昨天已经演奏了萧友梅的《哀悼引》等曲目,今天他还要演奏萧友梅1916年谱写的《夜曲》和《在暴风雪中前进》。这两首钢琴作品恐怕极少有人知道,只有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专业的人才听说有这样两首钢琴曲。此外,还有星海音乐学院的作曲家曹光平,曹老师不是广东人,但他在“星海”已经工作35年了,1983年就到了星海音乐学院,这么多年他创作了多首带有广东风格的、有岭南音乐语言特点的钢琴曲。还有一位钢琴家、作曲家杜宁武,他也要来演奏一下他自己的作品。
感谢这些钢琴家、作曲家的参与和帮助,这就为我们这个讲座的成功提供了保证。
“刍论”者,最初步、浅陋之论述也。《“岭南风格钢琴曲”刍论》这个题目,在我来广州之前认真准备了半个多月,自以为准备得相当充分了。但是,昨天我参观了星海音乐学院的“岭南音乐博物馆”,就感到了压力,因为我对岭南音乐知道得甚少甚微。博物馆收集了这么多材料,这么多民间音乐家,这么多演奏家,我都很不了解!
今天这个讲座是完全开放性的、讨论式的,因为我目前也是在学习岭南文化和岭南音乐的过程中。“岭南风格钢琴曲”是什么概念?它的特征有哪些?都是可以讨论和商榷的,欢迎所有的老师、同学都来参加讨论和发言,因为“岭南风格钢琴曲”是一个需要大家关心、众人参与的话题,希望大家就这个议题参与讨论,提出见解,直话直说。
讲到直话直说,我就想到了出生在岭南新兴县的禅宗六祖惠能,因为他讲经、写经都提倡明白直说,“直指人心”。这也应该是岭南的文风,因为只有直话和真话才能够直指人心。惠能留下的伟大著作《坛经》就是“明白直说”的典范。今天它是岭南文化的一部经典。我在这里所讲的关于“岭南风格钢琴曲”,都是我的直话和真话,但全部内容都是可以讨论、可以推翻的,可以进行重新思考,另行构建。台下的听众中,很可能对岭南音乐要比我熟悉得多。而我,只是一个音乐历史的旁观者,一个冷静的看客,我也是一个钢琴音乐的爱好者、一个“超级发烧友”。因此,我先来斗胆地提出关于岭南钢琴音乐的概念、历史、特点等方面的个人看法,供大家来讨论。
我今天讲的是关于“岭南风格钢琴曲”的四大论域的十二个论题。四大论域是分别为“岭南风格钢琴曲”的具体概念;“岭南风格钢琴曲”的文化特征;“岭南风格钢琴曲”的发展历史;“岭南风格钢琴曲”的今天和明天。十二个论题都是由上述“四大论域”引申出来的小问题。其中在讨论“岭南风格钢琴曲的发展历史”(即第四到第十个论题)时,要涉及不同历史时期的作曲家和作品,因此内容比较多,讲述和讨论也要多一些。这十二个论题,由我先对每一个论题作一个简要的介绍和表述,然后可以展开讨论,或深入阐述,或分析作品。
什么是“岭南风格钢琴曲”?
“岭南风格钢琴曲”可以说是“岭南音乐”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子系统,又是“岭南音乐”的一个钢琴创作的分支。
“岭南风格钢琴曲”的概念和初步定义是:
第一,带有“岭南文化”特征的钢琴曲。
第二,能够充分表现当下岭南人的精神面貌、理想追求和人文情怀的钢琴曲。
第三,带有岭南地区传统音乐或民间音乐特色和基因的钢琴曲。
上述三点中,第一点是基础;第二点是核心,是乐魂之所在,“岭南风格钢琴曲”的最重要的条件是“能够表现当下岭南人的精神面貌和人文情怀”;第三点是需要在音调、节奏、音色等诸方面与岭南传统音乐或民间音乐有某种联系。
以上三点是互依互存、相融相长的关系。与此三点能够挂上钩的钢琴作品,就可以称之为岭南风格钢琴曲,认识和理解“岭南风格钢琴曲”,需要透过语言表层,直达人文深层。
听众A:梁老师,我是广东嘉应学院的钢琴老师。请问岭南人在海外创作的带岭南特征的钢琴曲或者其他体裁音乐,它们算不算岭南风格钢琴曲或者岭南音乐?
梁茂春:谢谢你的提问,我试着回答一下。岭南处在五岭之南,它面向大海,是广东华侨出海最早、最多的地方。岭南的音乐家也是出国最早的,例如萧友梅、李树化、马思聪、陈洪等,我把他们的部分创作也包括在岭南音乐中,他们的创作有些是在海外写的,之后我会讲到萧友梅,他的最早三首钢琴曲全部都是在德国柏林谱写的,都是可以包括在岭南音乐中的,岭南音乐它有这样宽阔的怀抱。
今天,也有大批岭南籍的音乐家在海外创作。例如陈怡,她是广东人,到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之后又出国留学,现在在美国当教授,成为一位世界著名的作曲家。陈怡在1984年左右写过一首钢琴曲《多耶》,“多耶”是少数民族侗族的一个舞蹈,而广西的侗族属于岭南地区。广东籍作曲家黄安伦现居加拿大,他也创作了三部钢琴协奏曲和许多钢琴作品,影响十分广泛。还有一位广西籍的作曲家叫陆培,他现在也是美籍,应邀在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任教授,也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作曲家。年轻的岭南籍作曲家黄若,现在在海外非常活跃,是“星海”作曲系老教授黄英森教授的儿子。
曹光平:黄若在音乐创作上很有成就,他的名气已经很大了,相信他还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梁茂春:黄若是新一代的作曲家,谭盾是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黄若是70年代出生的,相差约二十年。黄若他们这一代作曲家已经有他们自己的创作追求了,创作风格上表现出了与陈怡、谭盾、陆培这一代作曲家不一样的追求。黄若也有采用岭南素材的钢琴曲,如《竹竿舞》等作品就有海南传统音乐特点,而黄若的祖籍是海南琼海。
黄若这一代作曲家的作品中,已经少有刻意表达民族标签的痕迹,他们的创作理念更为开放和随性,充分表达了开放式的文化融合观念。这不正是岭南文化的基因和特点的进一步发扬吗?
所以,眼前就有许多岭南籍作曲家在海外已经有世界性的影响了。我最初听到黄若的名字是在前几年,他被列入了一个国际现代音乐组织的“米勒剧场肖像音乐会”的系列,所谓“肖像音乐会”,就是作曲家的专场作品音乐会,黄若作为少数几位华裔作曲家被列入了这个作曲家系列,是很了不起的成就!所以,岭南籍的音乐家的成就是很巨大的,岭南籍音乐家在海外的发展是很值得期待的!
刚才这位嘉应学院钢琴老师的问题是,“岭南人在海外创作的带岭南特征的钢琴曲算不算岭南风格钢琴曲?”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当然,他们的作品中也有不带“岭南特征”的,那就不能算作岭南风格钢琴曲了。算与不算,你就用我刚才提到的“三条标准”来衡量它,即我说过的“文化特征”、“人文精神”和“传统音调”这三条。
曹光平老师对黄若是很关心的,我知道曹光平教授在“星海”开了一门新课——“中国的十二代作曲家”,他已把黄若列在了他的作曲课程中间了。
冼劲松:梁老师,我也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岭南籍或者说广东籍的作曲家,他们的作品也不全都是岭南风格的,我们是否可以以您所说的三点,即带有精神面貌的、人文的,及带有一定的岭南传统音乐来判断,怎样的作品才算是岭南风格作品?比如,虽然萧友梅是广东籍的,但是否很难把他的《哀悼引》看作是岭南风格的钢琴曲?第二个问题,如果非岭南籍的作曲家写的具有岭南风格特点的作品,那算不算是岭南风格的作曲家?
梁茂春:冼老师的这两个问题是相反相成的。先说第一个问题,“岭南籍的作曲家谱写的不带岭南风格的钢琴曲算什么?”简单来说,如果岭南籍作曲家谱写的新疆风格作品,可以归入“新疆风格钢琴曲”,谱写的江南风格作品,可以归入“江南风格钢琴曲”,余者类推。再说第二个问题,“外省籍作曲家写的带有岭南风格的钢琴曲算什么?”毫无疑问,可以归入“岭南风格钢琴曲”。这些作曲家采用了潮汕地区的山歌素材,或者运用了海丰地区的渔歌来写,当然是带有岭南风格了,那么这些作品完全是可以算成岭南风格的钢琴曲。比如曹光平老师是上海人,他已经在广州星海音乐学院工作了35年,应该算是广东人了。曹老师会讲广东话了吗?
曹光平:不能讲,只会听。
梁茂春:不能讲广东话,但你照样能写广东风格的音乐,能写地道的岭南风格音乐。这是不受影响的。
不但外省籍人谱写的广东风格钢琴曲能够“入列”,即使外国人谱写的广东风格的钢琴曲也可以算作“岭南风格钢琴曲”。下面我会专门谈到一位外国人——夏里柯。昨天我问蔡崇力老师,“夏里柯在香港、澳门生活几十年,他会说广东话吗?”蔡老师告诉我,“他完全不会说,只能讲一句‘我是打琴佬’”。粤语中“弹钢琴的人”叫“打琴佬”。这也不影响夏里柯改编出很地道的广东风格钢琴作品。
在认识“岭南风格钢琴曲”时,我觉得尺度可以放宽一些,思维也应该放开一些,包容度要大一点儿。不要死抱“岭南传统音调”这一点,更加重要的是应该从精神面貌和人文层面来分析。因为岭南人的精神是开放、包容的,因此就不要采用狭窄和闭锁的心态来看待“岭南风格钢琴曲”。也就是说,对“岭南风格钢琴曲”的界定不要过分死板,包容性要更加宽阔一些。认识“模糊”一点儿也没关系,不必要“一刀切”似的精确。
冼劲松老师刚才说的“很难把萧友梅的《哀悼引》作为是岭南风格的钢琴曲”,昨晚我在音乐会上听萧友梅的钢琴曲《哀悼引》的时候,就把它当作岭南风格钢琴曲来理解的,更准确地说,它是“岭南风格钢琴曲”在初创阶段的一个探索性作品。萧友梅1916年在德国谱写的三首钢琴曲都有这一特点。因为岭南文化的特点就是开放和包容。包容到各类音乐风格都可以接纳。萧友梅的钢琴曲属于中国最早的钢琴曲,他实际上也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就是岭南文化的“拿来主义”。那个音乐好听,拿来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了。所以我主张用更加宽阔的、开放的胸怀来看待岭南风格钢琴曲,精神涵容力要更大一些。
昨天上午在《广东钢琴音乐创作与演奏的探索》座谈会上,我举了一个例子,非常能说明问题。三百多年前,岭南人发现外国船上有船老大带来了一种洋玩意儿。大家叫它“洋琴”,是从欧洲传过来的,从广州上的岸。一敲起来“叮叮咚咚”响,非常好听!于是就拿过来啊,拿过来之后改造它,样子都变了,改成蝴蝶的样子,名字也改为“蝴蝶琴”,又名“扬琴”,飞扬的“扬”。数百年来,这个乐器就彻底地中国化了,成了典型的中国民族乐器了,现在哪个民族乐队都离不开它,成了民族乐器的“五大家族”(琵琶、二胡、古筝、笛子、扬琴)之一。所以说,中华民族本身有一种很大的文化涵容力。
上面讲的对待西方文化的包容态度。对待中国文化也是同理。中原儒家文化传过来了,中原人逃难过来了,好!欢迎!住在我这里,生根、繁衍。于是变成了客家人,形成了“客家文化”,成为岭南文化的一部分。
万事能包容,心胸似海宽,岭南文化的这个特性最为可贵!我讲了西方“洋琴”变为中国民族乐器“扬琴”的过程,按照这样的襟怀,按照这样的逻辑,西方钢琴同样是可以变为民族乐器钢琴的,条件是要有足够多的优秀的中国钢琴曲。
什么是“岭南音乐”?
“岭南音乐”是“岭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岭南”是一个地理概念,“岭南音乐”是一个“地理音乐学”的概念,“岭南”是一个人文概念,所以“岭南音乐”又是一个“人文音乐学”的概念。
从地理上来说,岭南即“五岭之南”,相当于现在的广东、广西及海南全境,包括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区。
“岭南音乐”和“华北音乐”“东北音乐”“西北音乐”“江南音乐”等相对应。
“岭南音乐”包括了这些地区的全部音乐——传统音乐和现代音乐,民间歌曲和戏曲音乐,琵琶音乐和钢琴音乐,高雅音乐和流行音乐……包罗音乐的万象。
“岭南音乐”还可细分为“广东音乐”“广西音乐”“海南音乐”“香港音乐”等分支。就拿“广东音乐”来说,学界又细分为“广府音乐”、“客家音乐”和“潮汕音乐”等,甚至还出现了“岭南广东音乐”这一概念。“香港音乐”当今也已经成为一个很有特点的“城市音乐”了,香港的钢琴音乐都可以自成体系,它的发展就以夏里柯改编的广东音乐为开始。
从地形、气候来看,岭南面向大海,背靠五岭。有山有海,河汊纵横。地近热带,四季如春。这种地理、气候条件,造成了“岭南人”性格上、文化上的诸多特点。
宋朝大诗人苏轼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后被罢官,发配到岭南惠州来当地方小吏,当时宋朝的岭南是“南蛮之地”,但他到了岭南,看到了海山葱茏的景色,就写了一首诗,其中一句是“岭南万户皆春色”。这句诗体现了他对岭南的美好感受,岭南真的是四季如春、绿草如茵,一个可爱的地方。苏轼在岭南时还为当地百姓做了好多有益的事情。他的这句诗也表现了岭南音乐的特色——春意盎然。
“岭南音乐”的文化特征是什么?
概要来说,“岭南音乐”的文化特色主要有下列诸项:
第一,开放性和包容性。
第二,传统性和创新性。
第三,自娱性和高雅性。
第四,坚忍性和幽默性。
第五,灵活性和轻巧性。
第六,平民性和世俗性。
岭南音乐有自娱自乐、自拉自唱、自吹自弹的特点,几个朋友聚在一个庭院里,演奏《娱乐升平》这一类的音乐,一天的疲劳就消除了。岭南人带有一种天生的坚韧性格,他要在这片荒莽之地开垦出一片绿油油的天地来,就一定要有坚韧的精神和幽默的性格。小调《卖杂货》表现民间小商贩的乐天个性,民歌《顶硬上》表现穷苦人的坚强性格,都是岭南音乐“草根性”的典型代表。“顶硬上”翻译成普通话就是“顶着困难前进”,这是光辉的“岭南精神”!在草根的民歌中展露无遗。
基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岭南文化是以农业文化和海洋文化为源头,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吸取并融汇中原文化和海外文化,逐渐形成自身独有的特点。
这些珍贵的文化特征,都应该是“岭南风格钢琴曲”发展的自然基因。
在上述六个文化特征中,我认为最为重要和可贵的是两条:即“开放性、包容性”和“平民性、世俗性”。
从历史上看,岭南文化向来被视为非主流的边缘文化,一直遭到主流传统文化的轻视和排斥。从实际上看,许多真正优秀的文化是因为处在边缘地带而受到轻视的。
中国文化数千年来的中心一直是中原文化,即儒家文化始终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当然有很多的优秀传统,但是儒家文化也有很多缺点,因为它是典型的封建主义文化,宣扬的主要是为封建王朝、为独裁政治服务的一种文化。岭南文化却不是这样的,岭南文化受到了海洋文化的深刻影响,带有鲜明的与中原文化的不同之处。岭南文化在许多方面是与主流的儒家文化对立的。而它的可贵性正在这里。
“岭南风格钢琴曲”的发展历史可分为几个阶段?
“岭南风格钢琴曲”发展成长的历史,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萌芽和成长时期——20世纪10年代到40年代。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是萧友梅、夏里柯、李树化、陈洪等。
第二阶段,成熟和曲折发展时期——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第二阶段的代表人物是马思聪、陈培勋、黄容赞等。
成熟时期的中心人物是陈培勋,代表作品是他的《广东音乐主题钢琴曲四首》(1954),还有马思聪,代表作品是《三首舞曲》(1950)和《粤曲三首》(1952—1953)。他们将“岭南风格钢琴曲”引出了第一个高潮。
第三阶段,在艰难竭蹶中崛起——时间是“文革”期间。代表人物是陈培勋、杜鸣心、储望华等。他们在中国钢琴音乐发展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推动“岭南风格钢琴曲”在1975年前后出现了一个高点。
第四阶段,持续深入发展时期——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新时期钢琴。第四阶段的代表人物有陆华柏、黄安伦、陆培、陈怡和倪洪进等。他们的作品使“岭南风格钢琴曲”产生了第二个高潮。
第四阶段由于历史视觉尚太短近,还难于以历史总结和定评。但我感觉这一时段“岭南风格钢琴曲”的影响也将是非常深远的。
我首先说一说“岭南风格钢琴曲”第一个高潮的情况。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出现了两个重要的广东籍的作曲家——马思聪和陈培勋。他们都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1950年马思聪就写了《三首舞曲》,后来又写了《粤乐三首》。但是流传最广的却是陈培勋的《广东音乐主题钢琴曲四首》。在那个时期,中国钢琴作品的数量还很少。为什么能够产生《广东音乐主题钢琴曲四首》呢?我曾就此问题问过陈培勋老师,陈老师给我们上过配器课,也给我们讲解过他的钢琴创作。我问他:“您为什么能够写出广东小曲四首这么漂亮的作品来啊?”他说:“是朱工一教授委约我写的。”朱工一是当时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教研室主任,由于上级号召钢琴老师和学生都要弹中国作品,因此朱工一就委约了陈培勋、江文也和马思聪来写。陈培勋的广东风格钢琴曲,一写就获得成功,钢琴系的师生非常喜欢,天天弹。20世纪60年代初,我在中央音乐学院上学时,每当从琴房中走过,两边琴房中都会传出《卖杂货》《旱天雷》的声音。真是“天天《卖杂货》,日日《旱天雷》,人人打《花鼓》,家家《喜相逢》”。其中《花鼓》是瞿维谱写的,《喜相逢》是郭志鸿根据同名笛子曲改编的。这四首钢琴曲,几乎可以和《牧童短笛》比肩,成为流传最广的中国钢琴曲。
张奕明:我最近视奏了苏夏教授1964年谱写的《黎族农村音乐素描》,这是一个非常棒的组曲,四个乐章。但我感到非常奇怪,在1964年那个时候怎么会出现多调性的写法?它第一乐章是《春耕》,描写黎族的农耕生活,其中有牛叫的声音等,完全就是多调性音乐,我觉得这是一部很令人惊艳的作品。我就想提一下这个作品,它应该属于您所说的第二个阶段的岭南钢琴曲吧?
梁茂春:对,黎族是海南地区的。海南应该是岭南的范围,苏夏教授1964年就谱写黎族风格的作品。
张奕明:《黎族农村音乐素描》的前两首是有点多调性,音乐非常现代化;后面两个乐章从风格上来说就比较传统了。我托人去问苏夏教授,他已经完全不记得写过这部作品了。
梁茂春:苏夏教授已经九十多岁了,现在还健在,但记忆力有些退化了。他的祖籍是广东东莞,现居北京,他出版过一本《苏夏钢琴曲选》①,好像收进了这部作品。谢谢奕明的提醒,这部作品无疑是“岭南风格钢琴曲”的组成部分。
多调性、无调性、噪音和声等现代作曲技法,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前是被视为“洪水猛兽”而加以禁止的,但是当时也有一批思想敏锐的音乐学院的青年教师和学生对现代作曲技法感兴趣,如北京的苏夏、徐振民,上海的桑桐、施咏康、汪立三、蒋祖馨、陈钢等人,他们偷偷地找一些外国现代音乐作品的谱子来进行分析和模仿,进行“地下创作”。作品写完之后只能放在抽屉里。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有机会拿出来。苏夏的《黎族农村音乐素描》也应该属于这种情况。由此可见,音乐创作上的好奇和敏感,是非常可贵的。
蔡崇力:我补充两点。第一点,昨天听了萧友梅的《哀悼引》,它给我的印象特别深。萧友梅是广东中山人,曾在德国留学,但是他早期是在澳门地区学音乐的,曾在澳门地区待了十年。那个年代澳门地区只有葡萄牙的神父或意大利的神父懂音乐,所以萧友梅受这个影响很深。我听《哀悼引》的时候,真的把它当成中国音乐来听的,当然他是用德国的和声,但是它的节奏、某些音乐的语言令我感动,其实它是中国的。萧友梅是在澳门地区接受音乐启蒙的,所以这是一个文化的传承或者说经过澳门地区的音乐洗礼,这就是萧友梅先生。
第二点,我想补充澳门作曲家林品晶,她在国外是很有名气的,她也是澳门人,是我中学的低一班同学,曾在澳门培道中学及培正中学就读,她一家人都是热爱艺术、热爱音乐。林品晶在国外拿过“罗马大奖”,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奖。她现在一般居住在纽约或者巴黎,但也经常回到香港或者澳门,是澳门乐团的驻团作曲家。她写过很多关于澳门的作品,还写过关于蔡文姬的室内歌剧。所以林品晶也是岭南音乐的代表人物。林品晶谱写了双钢琴曲《春晓》,1987年参加上海举办的“中国风格钢琴作品创作演奏国际比赛”,获得了中型作品二等奖(一等奖空缺)。
梁茂春:谢谢蔡崇力老师的补充,林品晶应该是一个典型的岭南风格的音乐家,她现在活跃在海外。还应该提到出生于澳门的作曲家林乐培。
蔡崇力:对!我来补充一下林乐培。他是在澳门出生的,现在是92岁,他也是跟意大利神父学的,就是在修道院学音乐。因为澳门当时没有音乐学院,也没有大学,所以学音乐都在修道院跟神父学。他后来住在香港,引导着香港的音乐界,任香港作曲家联会主席。退休之后曾移居加拿大,现在又回香港了。
梁茂春:在岭南风格音乐家群体里头,应该有林乐培、林品晶这样的名字。林乐培也谱写了钢琴曲,改编了钢琴曲《春江花月夜》,还改编了钢琴曲《昭君怨》,这些曲子都是用现代人的眼光来揣摩古曲意境。这也体现了岭南人的作风。
香港作曲家的钢琴曲是可以作为一个研究课题来进行的,非常适合研究生进行深入研究。除了香港、澳门本土的作曲家,还包括一批从内地去香港的作曲家,如林声翕、黄友棣、施金波、符任之、关乃忠、陈能济、屈文中等,他们都写了钢琴作品,都十分具有研究价值。
香港的音乐文化确实非常特别。20世纪三四十年代香港成为“广东音乐”发展的一个重镇,包括吕文成、尹自重、何大傻等艺人群体都集中到香港,他们演奏、灌唱片、教学生,进行商业性活动。自己养活自己,生活还过得挺好的。民族音乐走出了商业发展的路子。
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的经济起飞之后又产生了一个“粤语歌曲”,连邓丽君都在香港唱起了粤语歌曲。邓丽君是中国台湾艺人,到香港来发展,她要根据香港人喜欢听“粤语歌曲”的审美习惯,也学唱粤语歌曲。邓丽君模仿能力太强了,她唱的粤语歌曲得到了香港人的认可,他们喜欢邓丽君,还喜欢谭咏麟、梅艳芳、刘德华、叶倩文等。“粤语歌曲”掺杂着很多西方的音调元素,和声小调、七声音阶,等等,全部拿来跟广东话结合,结合得天衣无缝,这就成了“粤语歌曲”。在我的心目中,香港音乐对世界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粤语歌曲”,粤语歌曲是一种影响全世界的音乐体裁。懂不懂粤语没关系,爱听爱唱就行。说到底,这就是岭南文化的一个特征!“粤语歌曲”是一种新颖的流行音乐,它不仅柔媚轻软,也有粗犷悲凉,还有高远和哲理,把草根文化的精神发展到极致。这点很值得“岭南钢琴”学习和借鉴。
谢谢张奕明和蔡崇力老师,你们两位的补充都非常重要!(待续)
注 释:
①《苏夏钢琴曲选》,华乐出版社,1999年出版。其中收入了《黎族农村音乐素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