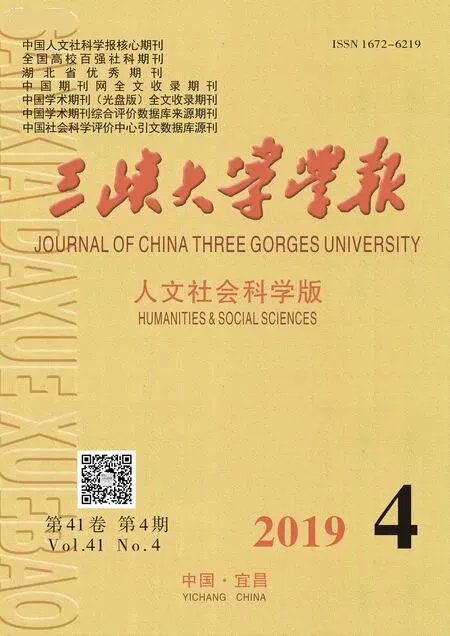《列异传》对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编著的影响
张传东
(鲁东大学 文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25)
《列异传》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第一部志怪小说集,形式上的开创及其在命名、故事材料选择及处理方面的特点都对后世志怪小说集的成书产生了深远影响,加之编著者曹丕在政治上和文坛上的重要地位,使得它更容易受到时人的关注和模仿。“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1]1544。曹丕以特殊的政治身份和邺下文人集团首领的身份编著了一部专谈“怪力乱神”的小说集,自然会抬高志怪小说和志怪小说集的地位,也会对后世志怪小说集的编著起到榜样示范作用。
一、《列异传》命名的影响
“列”字突出了该书的集录性质。《列异传》整体命名明显受到了西汉刘向《列仙传》《列士传》《列女传》等书命名的影响。刘向所谓的“列”含有罗列、搜集的意思,《说郛》元本载《列仙传·叙》曰,刘向“缉上古以来及三代、秦、汉,博采诸家言神仙事者,约载其人,集斯焉”[2]172;《汉书》刘向本传曰刘向“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3]1957,所以“列异传”是动宾短语,动词是“列”,搜集的意思,宾语是偏正结构的“异传”。《列异传》所记皆为鬼神之事,所以从“列”字可以看出该书的小说集性质,也可以看出内容的驳杂性。受这种命名方式影响的小说集主要是《搜神记》《集异记》等,以“搜”“集”来突出志怪小说集的集录性质,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小说集获取作品材料的方式和手段。
“异”字体现了小说集的志怪特征和传奇特征。《释名·释天》曰:“异者,异于常也。”[4]32,凡是“非常”的事、物都可以称为“异”。《隋书·经籍志》曰:“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1]982“异”就是“鬼物奇怪之事”等内容的概称,突出了小说集的志怪特征。“异”字的使用对后世志怪小说集的命名影响很大,一方面以“异”命名的小说集比较多,如佚名的《神异传》、戴祚的《甄异传》、刘敬叔《异苑》等。明代胡应麟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
幼尝戏辑诸小说为《百家异苑》,今录其序云:自汉人驾名东方朔作《神异经》,而魏文《列异传》继之,六朝、唐、宋凡小说以‘异’名者甚众。考《太平御览》《广记》及曾氏、陶氏诸编,有《述异记》《甄异录》《广异记》《旌异记》《古异传》《近异录》……大概近六十家,而李翱《卓异记》、陶谷《清异录》之类弗与焉。[5]364
由此可见人们认为“异”是概括志怪小说集内容的适合之词。另一方面后世小说集编著者多用和“异”意义接近的“神”“怪”等命名,这种名称既能体现志怪小说集搜奇记异的内容特征,又能凸显志怪小说集的传奇主旨,也体现了编著者的审美追求。
传,本是史书为写人物而设,《史通·列传》曰:“传者,列事也。……列事者,录人臣之形状,犹《春秋》之传。”[6]41《列异传》写怪力乱神却称为“传”,可见编著者还是想借重史学的发展以提高志怪小说的品格和地位。这种援史传文体入集名的方法影响到了后世小说集的命名,不仅以“传”命名者很多,如《神仙传》《鬼神列传》,并且以“记”“志”等史书名称命名的小说集数量也非常大。
二、作品材料选择范围的影响
《列异传》在选材上虽然侧重于“鬼物奇怪”,取材面广阔,内容庞杂,但总的看来,该书对作品来源的选择还是有其特点的。
1.偏重于选择历史性异闻
《列异传》选择的很多故事,其主要人物一般是正史中有记载但具体的事件都和正史不同,这些故事正是《列异传》中的“异传”,编著者感兴趣的正是这些志怪故事的异闻性特点。如“冯夫人”条:
汉桓帝冯夫人病亡。灵帝时,有贼盗发冢,七十余年,颜色如故,但小冷。共奸通,至斗争相杀。窦太后家被诛,欲以冯夫人配食。下邳陈公达议,以贵人虽是先所幸,尸体秽污,不宜配至尊。乃以窦太后配食。[7]9
《后汉书》卷六十五《段颎传》曰:“颎为河南太守,有盗发冯贵人冢,坐左转谏议大夫。”[8]2153说明发冢之事是有过的,但是“颜色如故”等尽是传言,“陈公达议”等言更是无稽之谈了。其他,如“韩平夫妇”条,涉及了战国时期宋国最后一位君主宋康王,《史记·宋微子世家》载宋康王“盛血以韦囊,悬而射之,命曰射天。淫于酒、妇人,群臣谏者辄射之。于是诸侯皆曰桀宋”[9]1632,历史说他淫于妇人可是并没有关于强抢人妻的记载。“鲍世骢”条写上党鲍宣救助路人而得报的离奇故事,鲍宣于《汉书》卷七十二有传但未记载此故事,而据李剑国先生《唐前志怪小说辑释》考证,《后汉书·独行传》关于王忳的记载事与此条在结构上十分相似只是主人公由鲍宣变成了王忳[10]162-163,让我们难辨孰非孰是。或许曹丕的时代社会上就流传着两个版本,正是鲍宣故事扑朔迷离“异闻性”色彩吸引了小说集编者的注意;“胡母班”条中的胡母班,在《三国志·袁绍传》中有提及,也并没有关于他见泰山府君的神话记载;“蒋济儿”条的主人公蒋济于《三国志·魏志》有载,其中的蒋济基本是个现实主义者,而《列异传》将此故事安排到他身上就带有某些嘲弄的意味了;“紫气浮关”条中的老子《史记》卷六十三有传,但未言其身被紫气;“鹞异”条主人公魏公子无忌于《史记》有传,但并无护鸠杀鹞的记载;“华歆”条之华歆于《三国志·魏志》有传,也没有华歆遇鬼的记载。可以说自《列异传》就体现出小说和史传的亲密关系,后世的小说集在内容上多记史传有其名而无其载的传闻异辞、荒诞不经之内容。
2.“旧作”和“新闻”兼收
从《列异传》的故事选择看,编著者非常注重“搜旧”,即从前代的图书典籍中刺取旧闻,从传说中纂录古老的故事。如“鹞异”“三王冢”二条皆录自刘向《列士传》,“鹄奔亭”条录自谢承《后汉书》或应劭《风俗通义》,“狸髡”条录自《风俗通义》等。《列异传》中还有大量小说录自民间旧有传说。同时《列异传》也注重“纳新”,即非常关注当时社会上出现的新故事。魏晋时期的文学自觉让人们开始追逐儒家思想体系以外的东西,对被儒学定位为小道的小说等尤为重视,所以有人开始模仿和借鉴其他故事的叙事模式或主题思想进行新故事的创作。如《列异传》的“谈生”条即是融合前代多种叙事因素而创作的新小说,首先,它在结构上利用了《高唐赋》《神女赋》《洛神赋》等赋作人神遇合的模式:小说中女鬼“姿颜服饰天下无双”与赋作之仙女无异;“来就生为夫妇”即同于赋作中神女的自荐枕席;女鬼最终与谈生含恨离别,即同于神女之离别。其次,“谈生”的主题和内容也相对新颖,表现的是我国流行的冥婚习俗。我国冥婚大致有3种形式,即人人冥婚、人鬼冥婚和人神冥婚,该故事为人鬼冥婚,即女子死后其家人择一世间男子与之冥配。这种习俗实际上体现了死者父母和冥婚对象之间的一种金钱利益关系,死者家庭一般地位显赫财货丰足,而冥婚对象则生活拮据。因此小说中的谈生是一介贫困书生,40岁还孑然一身;女子父亲乃朝中重臣,仅一句“表其儿为侍中”即表明了他显赫的政治地位。这种冥婚型的小说在当时是非常新颖的,其结构也对后世同题材的小说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再次,“谈生”小说还植入了大量当时流行的民间巫术以提高艺术效果。如小说中女鬼因为谈生以火照身而化归原型,明显是对传统以火祛鬼巫术的借鉴。古人出于对火的崇拜将火视作神圣之物,《搜神记》《幽明录》等小说集中多有作品表现这种巫术,据民俗学者调查,现今的江苏北部地区还保留着以火祛鬼的习俗;女鬼与谈生婚后“其腰以上,生肉如人”,此细节设置乃借鉴于道教房中术思想,因为道教认为通过采阴补阳或采阳补阴的房中术可以达到体内的阴阳平衡,女鬼的身体变化正体现了这种思想。总之,“谈生”故事身上已经明显具有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从事故事创作的印记。
同时,《列异传》还搜集了一些完全创新的志怪故事,这些小说未见有借鉴前代故事情节或模式的情况,一般和当时的时代背景关系密切,反映的是当时的新人新事。比如当时道教正在兴旺发展,于是出现了反映著名方士、道士的神迹故事。“鲁少千”“寿光侯”“汤圣卿”“营陵道人”等就是这类作品,鲁少千能借仙人符驱杀鬼魅,寿光侯、汤圣卿能劾百鬼众魅,费长房不仅能驱除鬼魅还能缩地脉,营陵道人能让人出入幽冥。这些故事的原作者当是方士或道教徒,其目的也在于自神其教,但是经过文人的转述其审美意味增强了。创新类志怪小说的不断产生是文学自觉、小说自觉的体现,而小说集编著者对这些新小说的关注也是小说自觉的另一种体现。自《列异传》始,“搜旧”和“纳新”就成为编著者获取小说材料的重要方式。
3.志怪题材全面:怪话、鬼话、仙话、传说并录
《列异传》在志怪题材上可以分为精怪故事、鬼故事、神仙方士故事和传说故事四类,这代表着编著者选择故事材料的四大范围。一是精怪故事,主要指以表现精怪作祟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包括“陈宝祠”“怒特祠”“张奋宅”“紫玉”“彭城男子”“张奋宅”“北地傅女”“文纳”“王周南”“野鹅”、“石侯祠”“到伯夷”“张叔高”等条,这些条目中鲤、狸、鼠、梓树、雉、石、玉、金、钱、银、杵、缶都等能化为精怪作祟于人。二是鬼故事,通过鬼来叙写复生、报应等主题,如“公孙达”“鲜于冀”“鹄奔亭”“鲍宣”“胡母班”“华歆”“蒋济儿”“定伯卖鬼”“营陵道人”“史均”“田伯”“谈生”“蔡支”“丁伯昭客”等。三是神仙方士故事,主要包括“鲁少千”“栾侯”“寿光侯”“费长房”“蒋子文”“度索君”“邓卓”“汤圣卿”“王方平”“蔡经”“弦超”等。四是神异性历史传说故事,主要包括“三王冢”“魏公子无忌”“冯夫人”“望夫石”“韩凭夫妇”等。怪话、鬼话、仙话和神异传说等体裁,构成了志怪小说集的主体内容,后世的小说集在题材选择上多不出这几类。
《列异传》在作品取材方面的这些特点,对后世志怪小说集作品材料的选择有直接的影响,可以说其后的所有志怪小说集在选择材料时均遵循了这三大原则。并且《搜神记》《幽明录》以及《神仙传》等志怪小说集均曾从《列异传》中转录故事,这也证明后世小说集编著者对《列异传》取材方式的认可。
三、故事材料处理方式的影响
《列异传》的编著者从图书典籍中抄录故事的时候并非原文照录,而是对其进行了志怪化纯粹处理,即保留原故事中的怪异部分但是省略掉非怪异部分如议论、说理等。《列异传》“鹞异”条[7]12乃抄录自《列士传》“魏公子”故事[11]1589,但是编著者在抄录时省略了很多非故事性的内容。通过表1我们可以看出从《列士传》到《列异传》的故事变化(表中以着重号标出的部分为《列异传》着意省略内容)。

表1 《列士传》与《列异传》之“鹞异”故事内容对比
《列士传》故事的字里行间都在表现魏公子怜爱弱小、不杀无辜的儒家君子品格,说教的成分很重。而《列异传》对原故事做了纯粹化处理,略去了对魏公子品格以及对魏公子进行的各种品评和议论,只保留了故事主干,以突出魏公子能力的独特性和鹞鸟服罪的怪异性。
再如《列异传》的“张叔高”条[12]3936,系抄录自《风俗通义·怪神篇》“世间多有伐木血出以为怪者”条之“张叔高”故事[13]434。两故事内容对比陈列(表2中以着重号标出的部分为《列异传》着意省略的内容)如下。

表2 《风俗通义》与《列异传》之“张叔高”故事内容对比
应劭所讲的“张叔高”故事倾向于表现张叔高正身行事、不惧邪魅的品格,也通过故事弘扬邪不压正的思想,所以故事侧重于描写张叔高除怪的过程,突出他的正义形象,并且文中多有说教性的议论文字(表格中下标下划线的部分),而这些内容恰恰是《列异传》编著者不关心的,因为编著者关心的是怪物的具体情状,最后一句“所谓木石怪夔魍魉乎”也是点明故事中心在于说怪。当然,不排除《列异传》“张叔高”故事被类书征引者做了简省处理,但是《列异传》编著者材料取舍的倾向还是清晰可见的。另外,《列异传》“狸髡”条[7]32乃抄录自《风俗通义·怪神篇》的“郅伯夷”故事[13]427-428,同样对原故事做了故事纯粹化的处理。试以下表呈现两者的变化(表3中以着重号标出部分为《列异传》着意省略的内容)。

表3 《风俗通义》与《列异传》之“狸髡”故事内容对比
《风俗通义》重在表现郅伯夷临危不惧、勇对邪恶的儒家君子品格,所以行文中对郅伯夷多识、多知、多智的才能进行了全面的呈现。而对他除怪的过程着墨颇多,以突出其“孝廉”的凛然不可侵犯之气度。但是《列异传》重在写狸怪“髡人”得道这一怪异现象,因为狸怪得人头发而成精的传说历来盛行,所以对除怪过程只是略作交待。并且两故事的结尾截然不同:一在于升华人物品格,一在于说明故事中狸怪成神的原因,两故事表现的重心不同也就明白无疑了。总体看,《列异传》是根据自身的表达需要对原故事进行了精简处理,志怪特色更加鲜明。
受到时代的影响,早期的志怪故事虽然以叙事为主,但往往会有很强的说理、教化与劝诫的目的,所以班固将小说家归入诸子十家之中。譬如《韩非子》之“说林”和内外“储说”中的小说,韩非子已经明确交代它们是供游说时的资料。刘向的《说苑》《新序》中虽然也存录了不少志怪故事,但主要体现了儒家的哲学思想、政治理想以及伦理观念。至于其它子书如《庄子》《淮南子》《墨子》等生活中的小说,也都是服务于说理和论证。总之,早期的小说并没有独立于子书、史书而存在,而开始主动将志怪小说从子书、史书中剥离出来并帮助原先的故事褪去了说理或说教的意旨。
《列异传》这种重故事、轻说理的材料处理方式对后世志怪小说集的编著影响很大。《列异传》之后的志怪小说集编著者从子书、史书中选择材料时,也是只保留故事本身而摒弃那些议论、说理的语言。譬如干宝编著《搜神记》时就开始有了游心寓目的娱乐追求,因此从《风俗通义》和《论衡》这两部子书中选择故事材料时,都是略其说理而保留故事。所以《列异传》对故事材料进行志怪化纯粹处理的方式对后世小说集编著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四、结语
总体看,《列异传》在命名、取材原则、行文特征等方面的基本做法都为后世志怪小说集编著者所遵循。并且它在选材时既关注旧籍载录又重视民间传说,开辟了志怪小说集编著选材的两种基本手段,此影响尤为深远。由《列异传》开启的志怪小说集编著行为,把志怪故事由分散性、依附性的存在变成了集中性、独立性的存在,对推动小说的独立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