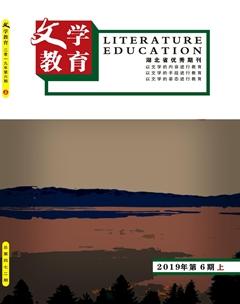一种极强烈的自我创造
黄孝阳的作品为文坛早已所关注,七〇后的作家,写出的文字,与同时代的人不相随,循着个性而行。近日读黄孝阳在《天津文学》第三期,发表的随笔《我和我的文学》,表达自己的文学观。
大多的写作者是泛化写作,如同书写的公文,统一的庸俗化标准,发出一致的口号。丧失个性,也不允许个性的存在。没有精神的支撑,散文和随笔,不过是一堆废弃的文字沙石砾,不值一文钱。洪堡特说:“散文则时时处处陪伴着人,在人的精神活动的所有表现形式中出现。散文与每个思想、每一感觉相维系。在一种语言里,散文利用自身的准确性、明晰性、灵活性、生动性以及和谐悦耳的语言,一方面能够从每个角度出发充分自由地发展起来,另一力面则获得予一种精微的感觉,从而能够在每一个别场合决定自由发展的适当程度。”
写作者不是写自己熟悉的生活,而是选择泡沫的想象。这和俄罗斯作家对苦难的叩问不同,一些写作者逃避,这样可以不担当任何责任,害怕触碰真实的生活。关于心灵的创作,降低为手艺和工匠的行当。
散文和随笔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它们有共同的特性,不需要戴着面具,做矫情的表演。它们是攀援植物,依附精神的主体,赖以生存和发展。
文字的水肿,粗糙,失去古典的诗意美。在没有底线的标准,写作变得随意,趣味低级,心胸狭窄,陷入个人的小情感,没有信仰,在急速发展的时代,表达自己的立场和反抗。巴金在谈起,自己为什么写作中指出:“人为什么需要文学?需要它来扫 除我们心灵中的垃圾,需要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勇气,带来力量。”文学是有使命感和担当的重任,不囿于个人,蛋壳似的狭窄小天地。如果一个作家失去思想的尖锐,他无法剖解患病的时代,更不能做病理分析,做出准确的判断,拿出合理的方案。文学最终要表现对精神生活的感受,不论文字长短,体裁大与小。一个作家的笔下,不限于写生活,吃穿住行和男女爱情,重要的是精神的高度。
有一種极强烈的刺痛感,比刀子割在手上还要疼。低头去看。能看见那里有一个伤口,一个不曾愈合过的伤口,流着脓血。再仔细凝视,这些脓血分明是我这些年所写下的字词段落。
换句话,我所有的写作,也包括相应的文学批评,皆自这个伤口而出。伤口孕育了我,创造了我。
黄孝阳的感受,有自己的独特发现。他的“刺痛感”不是阵痛,也不是药物可以缓解和治癒好的。它是心灵的疼,这种疼的缠绕,不时发出致命的电流。他去寻找疼的原因,究竟是为什么?这些终疑问,在寻找过程中,形成沉重的思考,解开这个谜,才能承救生命。这是艰难的旅程,不是几句牢骚,而是精神修复,所产下的文字。
如果说这个世界是一块钟表,它们即是这块钟表里面不可缺少的一个齿轮。如果说这个世界是一粒被上帝掷下的滚动着的骰子,它们即是这粒骰子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没有富人,哪来的穷人?没有悲伤,哪来的欢喜?没有你,又哪来的我?首先是认识自我,然后是摆脱自我。执念渐消,山河震动。
在古希腊德尔菲神庙的阿波罗神殿中,镌刻着一句人生箴言:“认识你自己。”这句话表达人类对自己、对未来的思考与追求。简单的五个字,却深藏厚重的意义。黄孝阳不断地发出叩问,是对生命的思考,和大声的呐喊。当下的作家得意于小富即乐,小情安逸的生活中。写些隔靴挠痒的文字,制造大量的垃圾作品,贴上花样翻新的标签,很少有作家对生命进行深刻的思索。黄孝阳是一个孤独的行走者,不受时代喧嚣的干扰,独来独往,遵守自己的信仰,绝不接受世俗的污染。
黄孝阳说:“夜里,在房间里坐。是陋室枯坐。世界在窗户外面闪着光。”这句诗意的话,语言张力,而富有弹性。它蕴藏深刻的东西。这不是随手写下的文字,抒发一些矫情,作表演状。一个在黑暗中的人,在一间简陋的屋子里,四面水泥围墙,只有窗外有光亮。要么在黑暗中消失,要么奋力的反抗,去追求对光明的渴望。
当代文学变成“圈子”子里的事情,大多数人热衷于社交、拉关系,很少耐得住寂寞,忍受孤独,更稀少见到对自己心灵的叩问。文字变得琐碎,浮浅如水上的漂浮物,顺流而下,难以发出金子般的光辉。精神的分子,充盈每一个文字中,散发奇异光彩,而不是徒有其名。内容干瘪,丧失生命的汁液。
网络、报刊的空前发达盛况,发表文字的门槛降低。人们错误的将随笔,误认为随心所欲的写作。一个“随”字,让人们失去辨别的能力,把生活中的碎片,唠唠叨叨的记录下来,寇以随笔,却不知随笔的真正意义。随笔是精神的年轮,多维的展现生命的感悟,更其先锋性,试验性,断片性同,担当重大的责任。
黄孝阳《我和我的文学》是心灵的地图,他用精神的比例尺标注。从每一个文字的点位,我们读到各种各样丰富的形象,变化万千,这是作家的踪迹史。
七〇后的作家,进入一种深层的思考和追求,这是难得的。而不是浮浅随大波,写出油光粉面的所谓大作。在北方的春天,我读黄孝阳火焰一般的文字。
高维生,著名散文家,出版散文集、诗集三十余种,主编“大散文”“独立文丛”等书系,现居山东滨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