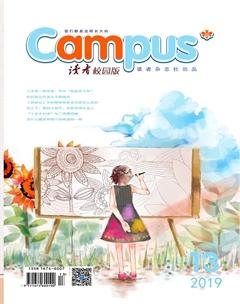我的文字之缘及汉听之旅
彭敏
我的家乡是南方的一个脏兮兮的小镇,小地方的图书资源极度匮乏,小时候我家中的经济状况又相当拮据,不可能经常花钱给我买书,所以我只好到处偷书看。小时候爱不释手的那些书,基本上都是我偷来的。
如果没有这些偷来的书籍,我的整个人生或许将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轨迹。也许我本来该是一个神经大条、严肃古板的理科生,现在却成了舞文弄墨的文学青年。惭愧,我的整个人生都是偷来的,却只能像孔乙己那样为自己辩解:“读书人的事,怎么能算偷呢?”
因为每天都沉浸在书的世界里,所以我常常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得很白痴,智商无限趋于零。比如做菜的时候放过柴油,走路的时候掉进过粪坑,大学7年没有谈过恋爱,我唯一的“女朋友”就是书,我能说出某本谁也没见过的书上一个特别冷僻的注释,却不知道同学经常谈论的三环和四环是什么意思。
我是现实生活中的低能儿,文学世界里的“全能战将”。我创作的古体诗词、新诗和小说在北京大学所有的文学比赛中都拿过第一名,无一遗漏;因为我背了很多诗词,有朋友送给我一个绰号,叫“背诗机”。
长期阅读诗词古籍为我打下了深厚的文字基础,我毕业后到中国作家协会的诗刊杂志社工作。6年的编辑生涯中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校对,这让我对现代汉语中一些易错的字词有了深刻的记忆。于是,当我因一个偶然的机缘来到《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的第四现场,我全部的储备都得以厚积薄发。这些东西在平时的生活中早已是屠龙之技,没有用武之地,却能在这个赛场上绽放光芒。
在答题过程中,我印象特别深的一道题目是:濩落。这个词出自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的“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在诗词当中并不常见,如果不是读了杜甫的这首诗,就很难写出来。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虽然是杜甫的名篇,很多选本也都选过,一般人却很难啃得下来,往往只知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我恰好是个老杜迷,听到这个题目,我心中窃喜,很快就写了出来,而我记得当时这道题的正确率非常低。
餐英,题目给的解释好像是指雅人的高洁。本来这两个字都不难,但是这个从本义引申出来的解释没有提供任何线索指向典故的出处,就变成了一道很难的题。一开始我也毫无头绪,可突然间想到了《离骚》里的“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就试着写了“餐英”,没想到答对了。就是这道题,一下子让我拉开了与其他人的距离,个人排名跃升到首位。
第一现场的小选手为了参加这个比赛,很多都是提前一年或半年背了好几本字典、词典,而我因为是临时被凤凰文化的主编胡涛兄拉过来参赛的,只在比赛那几天的闲暇时间才做了一些针对性的复习和押题。特别有趣的是,有好几个词都被我押中了,比如蒜薹、踣毙、跛牂、躔次、挫衄……
有时候考的字实在是太偏了,很难通过储备来回答,只好根据读音和释义来“造字”。如前文所说,第一现场的小选手基本都经过了长时间的针对性复习,而第四现场的100名成人听写者则基本属于“赤膊上阵”。在经过了诸多难题的轮番轰炸后,大家终于发现仅凭储备肯定是吃不消的,于是纷纷开动脑筋现场造字。常常是主持人念了一段很长的古文,选手基本没听明白说的是什么,就等最后解释那个要考的词是什么意思,然后开始琢磨该用什么形旁和声旁。这样造出来的字如天马行空,往往自己都不认识。特别有意思的是,考了一个“鹙”字,是古书上的一种水鸟。听声辨形,肯定是鸟字旁加某个声旁。在“丘”和“秋”之间,我选择了后者,可是,“鸟”和“秋”谁在左谁在右呢?鹌鹑、鸧鹒、鸬鹚、鹡鸰都是鸟在右,那就把“鸟”放右边吧!谁能想到,答案一出来,“鸟”不在左也不在右,而是在“秋”的下面……鹫、鹜、鹭鸶、鸳鸯都笑了……
当然,也有不少造对了的。比如,考了一个“醠”字,意思是清酒。首先,这个读音比较少见,声旁基本可以锁定为“盎”,既然是酒,那就应当从“酉”,答案出来,果不其然,就是“醠”。
此外,因为是听写,听觉能够提供的信息局限性很大,我们第四现场的选手又不能像第一现场的小选手一样提出自己的疑问,有些字就没听太明白。比如木橛,主持人給出的解释是短木桩,我鬼使神差地把“木”听成了“目”,把“短木桩”听成了“短目装”,就以为这是一种特殊的服装,而两名小选手居然一听就都表示明白了,没提任何问题,只留下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答案一出来,我才恍然大悟。这个词并不难,全场正确率也很高,但我因为想错了方向,所以怎么也写不出来。
参加《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真的是一次令人百感交集的旅程。毫不夸张地说,我平生所学,在方寸之间接受了血与火的考验。一次次,不到14岁的小选手轻而易举地写出了正确答案,我却在一番冥思苦想、绞尽脑汁后仍然写错,这种“前浪死在沙滩上”的无奈感,让人恨不得马上滚回去狂读万卷书再出来见人。不过转念一想,我辈老矣,台上这些青春年少却沉着老成的小选手,不正是我们古老汉语如日初升的守护者吗?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固其宜矣。